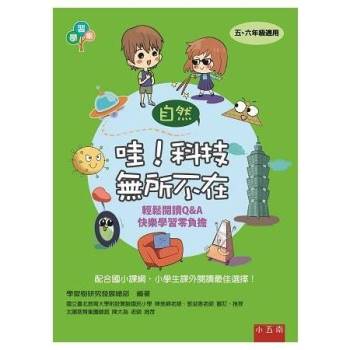知名作家岳南,寫在一代大師之後
鉤沉出離亂年代下人們的悲歡聚散
那是個群星閃耀、充滿啟蒙創造的時代,也是個風雨如晦、個體命運交織著家國恩怨的時代,那個留給後人無窮想像的時代,已成為絕響,一代大師的身影飄零如葉,紛紛遠去,於今留下豐碩的人文果實。
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師,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陶孟和、李濟、董作賓、吳金鼎、梁啟超、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等,他們在離亂年代,萬里流亡,輾轉於途,在本書裡,我們看到了這些大師們為學術思想的自由和進步所付出的汗水與努力,在移動與創造的群體文化規模上,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場景,此後也不會再次出現。
本書也披露了不為外人所知的內幕,作者深入歷史的角落,檢視湮沒日久的文獻,以鮮活的形象再度突顯那段歷史中的人事糾葛、學術爭端與愛恨恩仇。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這一代知識分子之間的恩怨情仇和家國命運,為何如此令人唏噓感嘆?如煙往事,其實沉重不堪。雖然大師日已遠,但是典型仍在夙昔,就讓我們在這個滿世喧囂而人心浮動的當代,一起感懷最後一代大師們的高貴人格,體驗他們的淚笑人生。
本書特色
本書為《之後再無大師》換封重發。
作者簡介
岳南
山東諸城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會理事。自20世紀80年代始,著力對民國抗戰時期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生存狀態、思想脈絡、道德精神與學術成就進行調查研究,有《南渡北歸》、《民國才女:林徽因和她的時代》、《李莊往事》、《陳寅恪與傅斯年》等作品問世,同時著有《風雪定陵》(合撰)、《復活的軍團》、《天賜王國》等考古文學系列作品十部。已有數部作品被譯為日、韓、英、法、德等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被譽為全球最有影響的考古紀實文學作家。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