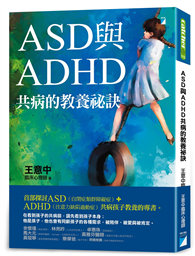我希望這一系列抗爭者的故事,能為新一代人提供某種參考,
每個人都需要從中汲取能量;更重要的是,歷史不僅是數量與規模所決定,理念與個人更是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許知遠
書中的十幾位「抗爭者」,分別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有些人的聲名如雷貫耳,有些則較為藏身幕後;有的人努力對抗時代流轉的巨輪,煥發出新的活力,有的則經過權力的洗禮,轉換生活軌跡;他們不僅是行動者,也是思考者,知道倘若沒有一套新的語言與價值,抗爭可能只會淪為權力爭奪;沒有一個充沛的內在世界,外在的行動便注定難以持久;沒有個人的孤獨堅持,集體行動則容易消散。他們也都有著各自的侷限,常常還在新時代裡不合時宜,甚至成為自己信念的背叛者,但他們都曾在某一個具體的時刻與情境下,成為了漢娜.鄂蘭所說的「黑暗時代中的人」。
在與每一位「抗爭者」的採訪相處過程中,許知遠透過深入觀察,從他們的歷史與歲月裡展現出這些人的個性和熱情。透過筆下文字表達出,這些抗爭者如何以行動改寫了時代、社會、國家、政治,甚至自己。許知遠著既迷於這些抗爭者所置身的歷史現場——激越的情懷、道德的感召、人生的使命,也著迷於每個抗爭者身處在大時代中的脆弱、無奈和渺小。
許知遠像是穿越了不同的時空,進入了這些抗爭者的內心,試圖探索出某種普遍意義的中國人抗爭精神。書中的這些人物與故事既平行前進,又彼此交叉。他們所處的時代與情境不同,但他們在許多時刻裡,幾乎是精神上的同代人。
作者簡介:
許知遠
一九七六年生於北京,為當代中國知名作家、公共知識分子、媒體人,並創立北京著名獨立人文書店「單向街」。許知遠以其對時勢堅定的批判立場、豐富的文化知識,以及個人獨特文風著稱;在二○○八年曾獲亞洲出版協會(SOPA)The Excellence in Opinion Writing獎項,並於二○○九至二○一○年間,至英國劍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現任美國《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主編;並同時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亞洲週刊》等媒體撰寫專欄。
著有《未成熟的國家》、《祖國的陌生人》、《極權的誘惑》、《一個遊盪者的世界》、《偽裝的盛世》等書。
攝影 林怡廷
一九七九年生於台北,政大廣電系畢。曾任香港《陽光時務週刊》台北特派記者,兼任文字及攝影,發表<蘭嶼 核廢之島>、<台北都更影像系列>、<中國病人>等深度圖文報導。<蘭嶼 核廢之島>獲二○一三年亞洲出版業協會環境報導獎,及第十七屆香港人權新聞獎(Human Right Press Awards)。目前任職於台灣媒體。
章節試閱
監獄哲學家 施明德 (節選)
壹.
「許先生,你多大了?」
「三十六歲了。」
「好年輕呀!」
我正準備回說「也不年輕了」,卻意識到面對我的是一位年長我三十五歲的人。況且,對他來說,三十六歲有著無窮意味。一九八九年,當時施明德還躺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的病床上,他對來訪的朋友說,他的人生在三十六歲到三十九歲才算真正活過。
三十六歲那年,當他從綠島歸來時,已在監獄裡待了十五年。從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刻,他如困獸一般被監禁牢中,這對一個人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囚禁只是一種失去空間換來時間的生活狀態」,他在第一次出獄不久後寫道——「『自由人』的空間是廣闊的……卻不得不為名、為利、為世俗雜務奔忙……囚犯的空間雖然是有限的、局促的……卻能擁有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愛的東西。」
在這篇名為〈我的囚犯哲學〉文章中,他歸納出三種觀點;空間與時間的對比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不要求環境適應自己,應該要求自己適應環境」——因為囚犯的環境總是被決定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仍放縱自我,就會頻生煩悶,削弱生機。最後,要拒絕接受絕望意識,「一個囚犯如果任由絕望控制心理,它就會腐蝕其意志,割傷其身軀,最後還會墮落地廉售其操節」,而克服絕望的方式,不是依賴唐吉訶德式的迷狂,而是某種理性的判斷——絕望「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為情勢或條件保持原狀下的結論。但是人為的情勢或條件不會永存不變,一旦它們有了改變,結論便會隨著改變。」
情勢的確有了改變,蔣介石在一九七五年去世,讓原本無期徒刑的施明德得以提前出獄。不過,這篇文章是為另一所監獄的內部刊物所寫,行文中鼓舞的色彩濃重,要給「獄友們」希望。漫長的監獄時光,遠比這三個觀點要豐富及痛苦得多,付出的代價,是非親歷者難以想像的……
他一定難以忘記初次被捕時的脆弱。他發現,從被逮捕到判決前是最脆弱的時候——在連續問訊後,突然把你單獨囚禁——「一開始,囚犯會很高興,終於不用再受訊問」,但幾天後,感覺不同了,「你完全與外界隔絕,沒人訊問,也無法通信、看報紙,完全猜不透他們在打什麼主意;再過幾天……你甚至會產生虛無感,這種感覺比接受訊問更恐怖百倍。」
不過,這只是第一步,即使熬過了這「脆弱的時刻」,審判下來了,接下來的日子則變得更具體,所有你平日熟悉的東西都以另一種面貌出現,最平凡的東西全變成了奢侈。
囚室裡每天能曬到陽光的時間只有三十分鐘;水,更是可怕的問題。在台北的景美,在綠島,我參觀過那些綠色門的囚室,囚室空間的狹窄不必說,讓我最難忘的是它的便池,那種下凹、蹲式的。對囚犯來說,這不僅是便池,而且是所有生活用水的來源——刷牙、洗臉、洗碗筷、洗衣服都得在這裡。日後,這實在是可怕的回憶。
牢裡的食物則是永遠匱乏的。施明德在綠島的時光裡,沒有蔬菜,他和獄友們孵豆芽,他在這過程中發現,「凡是那些彎彎曲曲或又瘦又長的豆芽,都是長在最上層或外緣部位的。那些被困在最內層、負荷最大壓力、又無可逃避的豆芽,卻都長得粗壯結實,活像白武士」。而囚禁在綠島時,他和獄友都太想吃肉了,竟會想烤老鼠來吃。他們要先用饅頭養肥窗外的小老鼠,再設法把老鼠釣進牢房。而燒烤也需要特別的學問,他們用衛生紙與塑膠袋一層層捲起來,這樣燃燒的時間夠長,能把老鼠肉烤熟。
至於被單獨囚禁帶來的無望,同室囚徒為了最卑微的物質而彼此鬥爭的場景,更是不斷上演。監獄中的每個環節,都在試圖摧毀個人的尊嚴與意志。很少有人能在這樣的環境中保有原本的自我。
比起生活上的不適,真正的災難來自被遺棄感。在施明德十五年的監獄生涯快結束前,他的家庭破裂,妻子與女兒離他而去,而且取代他這個丈夫及父親位置的,是他的獄友……不過,求生的意志也可能被激發。他把喪失自由的世界,當成學習的場所,他放棄別的囚犯渴望的「外役」機會,把時間都用來閱讀、思考——歷史、政治、外交、文學,他無一不讀。為了對抗禁錮空間帶來的非現實感,他爭取一切閱讀報紙的機會,瞭解外部的世界,以防止脫節。
內在的反抗不足,他也參與外在的反抗。他是一九七○年那場著名的台東泰源監獄暴動的倖存者。那真是充滿光輝的一刻,一群起義者明知必有一死,他們全部的希望是能喚醒被壓迫的台灣人的意識……
貳.
當少年施明德與他的同學開始這個鬆散的讀書會時,即使預感到某種危險,也必定難以想像會遭遇如此的對待。
他出生在一九四一年的高雄,父親是一位南台灣的名醫,推拿術遠近聞名,他是這個優越家庭的第四個男孩。父親在皇民化的台灣社會上取得了經濟成功,卻是個抗日者。
施明德的出生時間注定了他要親身經歷紛至沓來的歷史事件,台灣命運的矛盾性則在最初就烙印在他心裡。施家在太平洋戰爭的末期,全家從城裡搬到鄉下,但美軍的空襲仍然如影隨行。美國人的飛機要轟炸日本人統治的台灣,交戰的是美日,受害者卻是台灣人。當勝利到來後,台灣重回中國的懷抱,他看到父親被捕,而在他六歲時,曾在高雄火車站前的交叉路口看到成排的中學生被軍隊的機槍掃射——「二二八事件」發生了。
「許先生,你聽過這句台灣話嗎:小孩子有耳無嘴,有尻不放屁」,我們見面不久,他就問我。他的第一遍是以台語說出的,我自然聽不懂,而第二遍的國語所說,我大致明白了。二二八事件後,一個沉默的時代開始了,台灣人深深地活在恐懼中。他們原以為迎來祖國的解放者,遭遇的卻是比日本更恐怖的新統治者。
施明德是在普遍的社會恐懼、以及新政權沒完沒了的「反攻大陸」宣傳中進入少年時代的。多虧他的大哥介紹給他的禁書——中國三○年代的左翼文學、俄國小說,還有青春特有的英雄主義——他瘋狂地崇拜拿破崙、亞歷山大、林肯,還有當時剛崛起的古巴的卡斯楚。施明德克服了這種恐怖。
不僅如此,他還準備把這英雄主義付諸實踐。中學畢業後,他放棄考大學,改進入軍校。高雄火車站前那些中學生中彈的畫面始終縈繞心頭,他要學習軍事知識,在軍隊裡發動兵變,推翻蔣家王朝。
這是個十足孩子氣的想法,它能嚇壞媽媽,讓一個少年逞一時之快,但沒人會把這個想法當真,即使是那些意氣相投的同齡人。當施明德與他的大哥、還有親密的朋友組建這個讀書會,在施家二樓交換對禁書與女孩的看法,煞有介事地談論台灣時局時,他們必定感受到一種戰友式與兄弟式的親密,並在相互鼓舞中克服了恐懼、得到勇氣。
軍校時代的施明德,個子高瘦,與他的大哥施明正的英俊不同,他的狹小眼睛、尖尖下巴,似乎都缺乏男性魅力,與他所仰慕的那些英雄們的氣概不同。軍校畢業後,他被派往與廈門相對的小金門,擔任炮兵觀測官。
休假時,他仍會回到高雄與朋友熱情相聚。他們準備為這定期的聚會起個名字,好更顯正式,或許可以為未來的兵變進行組織上的準備。
但名字還沒起,這個鬆散的小組織就被當作重大台獨案件的「亞細亞聯盟案」而被查獲。這樣的案件在那個恐懼而荒誕的時代層出不窮,這個流亡政權既對所有共產主義組織與思想充滿敵視,又擔心台灣人的獨立情緒會破壞國民黨所代表的大中國的政治合法性;不安全感讓這個政權透過不停地清洗,獲取某種確定感;倘若他們找不到明確的敵人,就創造出一些敵人。
而這個讀書會上的青年人,就成了被創造出的敵人。更諷刺的是,這還是由這個組織內為一個女孩吃醋的兩個成員相互揭發所導致的。施家成了這場災難最大的受害者,兄弟三個牽扯其中,身為四弟的施明德還被視為是這個台獨聯盟的頭目,被判處無期徒刑。
叁.
走進房門,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一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台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審人一字排開、表情各異地站著。施明德正好在圖片中間,與身旁普遍的嚴肅與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雙手插兜,咧嘴笑著,那得意的神情,彷彿自己不是在一場很可能被判處死刑的審判上,而是出席一場朋友間的聚會。照片被放大、貼在一整面玻璃牆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個時代。
這不僅是他此生最重要的時刻,也是台灣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決定性瞬間」之一。這令人意外、漫不經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嚴酷的冬日正在過去,破冰聲正傳來。
在裡間辦公室內的綠牆上,則掛著滿牆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內全是台灣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與事件——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橋頭事件、《美麗島》編輯部,施明德都是這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證人。黑白的光影對比,令它們既真實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確認了對過往的解釋權。
我在台北郊區一處幽靜的半山別墅裡見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著藍色牛仔褲、寬鬆的白襯衫,長髮蓬鬆,鬍鬚修剪得乾淨,整個人望去得體又瀟灑,既不像七十一歲的老人,更看不出二十五年牢獄生涯的痕跡。
他溫暖、客氣、瀟灑,卻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們見面的形式、還是談話內容,都讓我有這樣的強烈印象——在我遇過的人當中,沒有誰比他對自身更富有歷史自覺意識。我們沒有面對面相坐,而是並排坐在兩張側過來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攝影機則擺在不遠處。我同朋友及他的兩個漂亮女兒,則列席在兩旁,這使得我們的談話像是一場會談,是為了鏡頭與聽眾而發表意見。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擔心年齡尚幼的女兒,難以瞭解這個父親多姿多彩的過往,他們父女間過分懸殊的年紀,多少讓他覺得這種講述與記錄的急迫性。
當他開口時,有一種奇特的「個人化的非個人語氣」。他動情地講述自己觀點,卻似乎又代表著某種抽象的歷史敘述,有一種不容質疑的絕對性。
面對我這個來自北京的客人,他自然要從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政治結構說起,似乎要給我補上一小節濃縮的歷史課。施明德的獨特性也因歷史背景而倍顯突出。在他的自述裡,在他的公開談話中,當然也在對我這樣的陌生拜訪者的講述中,他一定會說起,他坐過中華民國四任總統的牢,歷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與李登輝……
「台灣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資歷更深,包括李登輝在內,儘管他年紀更長」。為他這個看法作注釋的,是他在一九六二年的首次入獄。很顯然,他已把五○年前一個躁動青年的遭遇,當作一種成熟意識的反抗。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他似乎確信自己早已形成一種堅強、穩定的內在意志,因此挺過重重難關。我對此多少有些懷疑,他對自己的過往有些太過浪漫化,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駁;倘若他沒有這樣的自我暗示,又怎能熬過那些漫漫長夜?「自大」與「先知」總是如影隨行。
當施明德站在一九八○年的法庭上時,不單他的微笑,甚至連他的自我辯護,都顯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來自另一個時空,根本不知現實為何物。他在法庭上大談對自由、民主、人權的看法,對於台灣未來的思考,解釋自己所創的「暴力邊緣論」;他不僅沒有為所謂「罪行」申辯的意思,甚至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個人命運的憂慮,他談論的是始終是台灣的命運。
在審判的間歇時間裡,他趴在監獄地板上,寫出洋洋灑灑數萬言的「遺囑」。他不過三十九歲,卻感到死期將至,在這篇副標題為「一個奉獻者的最後自白」的政治遺囑中,他回憶自己的一生、他的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以及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判斷。
時隔三十年,這份文本仍散發出一種詭異的魅力。那種高度自我與高度忘我的精神,竟如此奇特地結合在一起。施明德毫不諱言自己正是「一九八○年代台灣最轟動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稱的口氣自問,「這個『最轟動的男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還許諾說「如果我還能活得夠久,我會把自己極端傳奇的一生,包括極精彩的一連串異國戀情,做更詳實的描述。」
但同時,他在分析台灣民主的四大階段與四條路線時,卻又表現出罕見的清晰,在身陷絕境、手邊毫無資料參考的情況下,竟寫得像是法律條文般極富邏輯。而他大膽提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不僅擊中了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統治的核心,而且仍適應於此刻的台灣……
肆.
一九七七年六月,從獄中出來的施明德想必難以想像人生還會贏來這輝煌的一刻。他在監獄中耗盡青春,如今妻離子散,母親去世了,大哥則在恐懼中難以自拔,一切卻要重頭開始。
入監時,一切平常事物都變得珍貴,而重獲自由時,又意味著新的困惑與挑戰。和入監時一樣,它也先從一連串細節開始。
出獄第一晚,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進旅館。施明德在抽水馬桶前不斷嘗試,把坐墊掀起再放下,不知該是蹲在上面,還是坐在上面。他不會用投幣電話,仍到電信局打電話,新型百貨大樓的自動門讓他很緊張,不知怎麼推門進去,第一次坐計程車則忐忑不安,不知該怎麼打開車門……在他被禁錮時,台灣的經濟已經開始起飛,一個忙碌的現代社會正在形成,這也是個混雜、令人費解的新社會。
新事物或許容易掌握,舊有的恐懼卻很難立刻消失。與人談話時,他目光四處張望,在家裡會習慣地搜找竊聽器,到處亂塞東西;他不管到哪兒,背包裡都帶著衛生紙、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圍,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抓進去。
最能表明這生命斷裂感的,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剛出獄時,他走在路上注意的總是高中女生,他的興趣仍停留在入獄前,他是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夜晚去酒店時,他焦慮地坐在小姐們中間,陷入莫名的緊張。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黃粱夢後醒來。
或許最令人難以適應的是社會態度,這個仍未擺脫政治恐懼,又一頭栽進發財夢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會,該怎樣接納這個幾乎毫無生存技能的政治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貨車捆工,多虧另一位出獄政治犯人的幫助,他穿行在高雄與台北之間,是這個島嶼日漸繁榮的螺絲釘。那必定是個難安的時間,有時候,他把內心憤懣發洩到離開他的妻子和獄友身上——舉著橫幅到他們家開設的工廠前抗議。
不過,他恢復得比人們想像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獄五個月後,一同坐過牢的蘇東啟要請他為太太蘇洪月嬌在一九七七年底參加的省議員競選活動助選。蘇洪月嬌在選站中順利當選,也讓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灣政治與他入獄時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猶在,但已經鬆動。蔣經國大力擢升本省人進入權力結構,以安撫人心,而反對力量也開始集結,形成一個鬆散的黨外聯盟。這一年在中壢發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首次表現的民眾抗爭。
只有在這新的抗爭中,施明德才獲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調,根據他的情況,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麼輕,也要面臨再次的無期徒刑。施明德給自己取了化名「許一文」,在台語裡,「許」發音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寫照。
在接下來的兩年多裡,他雖一名不文,卻興致盎然,拚命地戀愛與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補回來。透過蘇洪月嬌的推薦,他成為代表本省人立場的《台灣時報》記者。他在這短暫的記者生涯裡,四處採訪,瞭解政治與社會,廣交朋友,並寫出〈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的著名文章,他在文內首創了後來廣為流傳的「萬年國會」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詞彙能比這一詞更準確地形容出國民黨政治的停滯性。他的努力很快贏得黨外領袖人物黃信介的信任,在一九七八年出任全國黨外中央民意助選團的總幹事,為該年年底新的增額選舉做準備。
施明德的行動能力很快就令人側目。他是個不知疲倦的聯結者,在台灣四處串聯,要把分散在台灣各處的黨外力量連成一股全國性的力量,也試圖與海外民主力量聯結,讓台灣的聲音傳遞出去。這種聯結能幫助弱小的黨外力量消除孤立感與受困感。同時,助選團還試圖把組織意識帶進來,為黨外競選者提供共同的政見、競選標語與歌曲,交換候選人宣傳資料,提供整體資訊給中外記者,以傳達共同的黨外聲音。
他也試圖將新的政治哲學帶入這波新的行動中。批判國民黨的腐敗,要求民主是黨外慣用的競選言詞,他則期望把「人權」引入其中——人權觀念當時因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上台,而在國際政治領域熱烈起來。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貫主張——他之所以反對國民黨政權,是因為它對個人的壓抑。他請人為助選團設計的標誌,是一個握緊的拳頭,下面是「人權」兩字,周圍則是橄欖枝,意味以和平方式爭權人權。
監獄哲學家 施明德 (節選)
壹.
「許先生,你多大了?」
「三十六歲了。」
「好年輕呀!」
我正準備回說「也不年輕了」,卻意識到面對我的是一位年長我三十五歲的人。況且,對他來說,三十六歲有著無窮意味。一九八九年,當時施明德還躺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的病床上,他對來訪的朋友說,他的人生在三十六歲到三十九歲才算真正活過。
三十六歲那年,當他從綠島歸來時,已在監獄裡待了十五年。從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刻,他如困獸一般被監禁牢中,這對一個人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囚禁只是一種...
目錄
序
第一部 台灣
.監獄哲學家—施明德
.堅定的變色龍—許信良
.黨外的聲音—江春男
.野百合與天安門—羅文嘉、馬永成、王丹
.賤民之驕傲—吳叡人
.東方美人與紅露酒—周奕成
第二部 香港
.中環的格瓦拉—梁國雄
.父與子—李柱銘
.遺民與蝗蟲—陳 雲
.愛人同志—陳允中、司徒薇,朱凱迪
第三部 大陸
.在北京讀哈維爾—崔衛平、景凱旋
.受困的黑馬—劉曉波
.我們這一代—許志永、余杰 等
.民主的功夫茶—烏坎人
致謝
序
第一部 台灣
.監獄哲學家—施明德
.堅定的變色龍—許信良
.黨外的聲音—江春男
.野百合與天安門—羅文嘉、馬永成、王丹
.賤民之驕傲—吳叡人
.東方美人與紅露酒—周奕成
第二部 香港
.中環的格瓦拉—梁國雄
.父與子—李柱銘
.遺民與蝗蟲—陳 雲
.愛人同志—陳允中、司徒薇,朱凱迪
第三部 大陸
.在北京讀哈維爾—崔衛平、景凱旋
.受困的黑馬—劉曉波
.我們這一代—許志永、余杰 等
.民主的功夫茶—烏坎人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