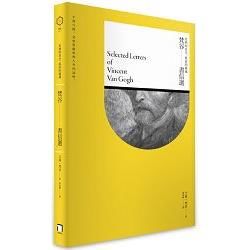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炙熱的星空,孤寂的靈魂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35 |
畫家傳記/文集 |
電子書 |
$ 245 |
繪畫 |
$ 298 |
藝術設計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藝術人物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炙熱的星空,孤寂的靈魂
生前不受歡迎,身後卻受世人喜愛的梵谷,一直要到二十七歲後才開始畫家生涯。然而,短暫人生之末卻也是他的創作巔峰。世人熟知的《向日葵》、《麥田群鴉》等傑作,多半是他在人生最後二年間畫成。
《炙熱的星空,孤寂的靈魂——梵谷書信選》內容多擇自他在人生最後兩年的一八八八年前後;梵谷此時已離開巴黎,遷居法國南部作畫。在這些與胞弟和摯友的通信中,梵谷強烈表達出他對藝術的觀點、創作理念、畫作用色想法,荷蘭「老大師」的啟發,以及他對法國南方地景、光線、顏色、人物的細膩描述和觀察。
作者簡介
文生・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1890)
荷蘭人,後印象派畫家,影響二十世紀藝術甚深,尤其是野獸派與德國表現主義。梵谷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和《麥田群鴉》等作,已躋身全球最廣為人知的藝術作品之列。
譯者簡介
蔡旻峻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藝術管理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出版通路、雜誌企劃、書籍企劃、翻譯,現為專職書籍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