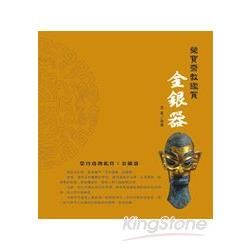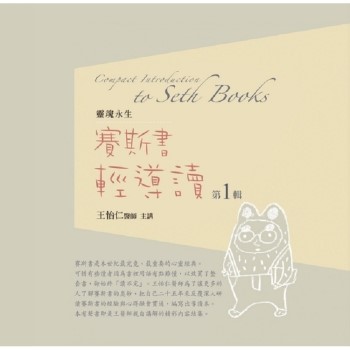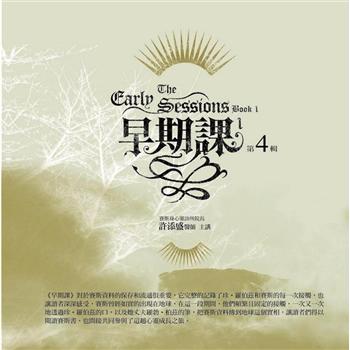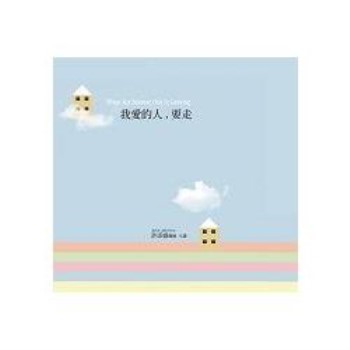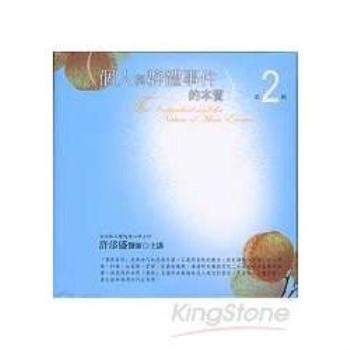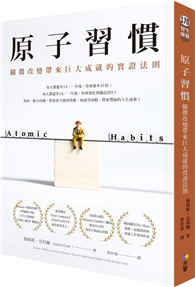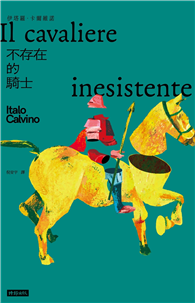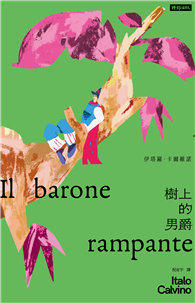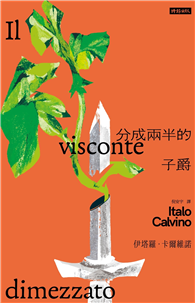黃金和白銀,是金屬中「天生麗質」的貴族。
黃金,擁有天然豔麗的色彩、炫目耀眼的光澤,以及錦緞一般清秀的紋理,,其高雅華美,常使人有不敢逼視之感。
白銀,則以其潔白清亮的色澤,素來象徵著純潔無瑕的高尚情操,為人們所謳歌稱道。
中國古代金銀工藝史是一部絢麗多彩,華光四射的發展史,每一時代無不以其獨特的面貌卓然標舉,各領風騷。
中國金銀器的發展,具有自身的規律和鮮明的特點:首先,中國金銀器追求高超的藝術性,創造了別開生面的藝術形式。其次,是追隨藝術內涵的嬗替,因「時」制宜地推陳出新。其三,金銀器是一門開放的藝術,民族特色與文化交流始終是源頭活水。
一部濃縮的中國金銀器發展史,正是中國金銀匠作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融合各民族傳統金屬工藝精華,同時借鑑異域先進文化的積極因素,逐步摸索創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銀工藝,使審美與實用、造型與裝飾都達到高度和諧統一,並使之成為反映上流社會審美趣旨與文化傾向的歷史。
本書特色
黃金和白銀,是金屬中「天生麗質」的貴族。黃金,擁有天然豔麗的色彩、炫目耀眼的光澤,常使人有不敢逼視之感。白銀,則以其潔白清亮的色澤,素來象徵著純潔無瑕的高尚情操,為人們所謳歌稱道。
中國古代金銀工藝史是一部絢麗多彩,華光四射的發展史,一部濃縮的中國金銀器發展史,正是中國金銀匠作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融合各民族傳統金屬工藝精華,創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銀工藝。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榮寶齋教鑑賞:金銀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38 |
科學科普 |
$ 246 |
收藏 |
$ 246 |
收藏 |
$ 252 |
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目錄
1. 與世界範圍內其他地區金銀器相比,中國古代金銀器具有哪些特點?其價值應如何評價?
2. 商周時期,中原王朝與北方部族對黃金製品的使用存在著不同價值觀,這種差異是如何造成的?
3. 做為商代黃金製品南方系統的三星堆金器的發現,有著怎樣的文化意蘊?
4. 帶鉤在重視衣冠禮儀的古代社會具有重要功用,金銀是如何在帶鉤上展現其天然美麗的色彩的?
5. 金銀容器的萌現堪稱東南地區對中國貴金屬工藝的重大貢獻,這一貢獻是怎樣體現出來的?
6. 為什麼說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高原的金銀器受到了來自斯基泰文化的巨大影響?
7. 金銀最初介入流通領域的形態是怎樣的?在使用上有什麼特點?
8. 兩漢黃金貨幣的規範化有何特點?漢魏以來的黃金貨幣有哪些用途?
9. 為什麼說益壽封禪是漢代金銀器具異軍突起的動因?
10.最能代表漢魏金銀器工藝傑出成就的技術有哪些?
11.魏晉南北朝時期,金銀器的使用在秉承東漢餘緒的基礎上出現了哪些新氣象?
12.鮮卑金銀器的造型、裝飾有何特點?對漢地金銀製品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13.魏晉南北朝時期,薩珊系統的西方金銀器大量湧入中國,這些舶來品有何特點?
14.唐代金銀器展現出的思想觀念和審美情趣,達到了中國金銀器製作的頂峰。唐代金銀器何以蔚為大興?
15.金銀器製造業性質的變遷對唐代金銀器產生了哪些影響?
16.唐代中後期金銀器的區域性風格是如何形成的?怎樣區別?
17.唐代典雅的飲茶時尚與豪飲之風是如何反映在金銀器上的呢?
18.唐代金銀器是如何與煉丹術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19.唐代以貴金屬裝扮的法身法器在規模、種類乃至用法上都有了怎樣的變化?
20.唐代金銀器曾經受到哪些地區金銀工藝的深刻影響?
21.宋代金銀器商品化的前提是什麼?是如何表現的?
22.宋代金銀器在造型與工藝上有何特點?為什麼說宋代金銀器的民族風格最為完美?
23.宋代佛教用具出現了哪些新式風貌?
24.宋代至明代金銀器常見的雞心形飾件,文獻稱之為霞帔墜子,它究竟有什麼用途?
25.遼代金銀器的種類、形制有何特點?
26.西夏、金、大理金銀器有何特點?
27.元代金銀器製造業在商品經濟和手工業發展基礎上,湧現了一批名匠,其代表作有哪些?
28.明代金銀器的突出成就是什麼?表現在以冠帽為主的裝飾品上有何特點?
29.清代融會中國金銀器製作工藝之大成,其具體表現如何?
30.如何鑑別金銀器的真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