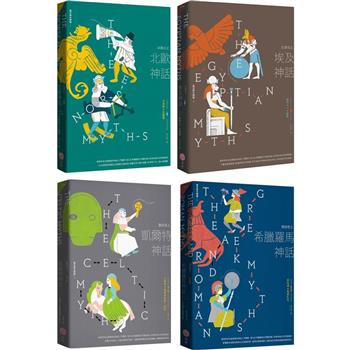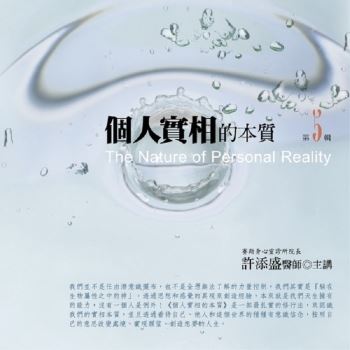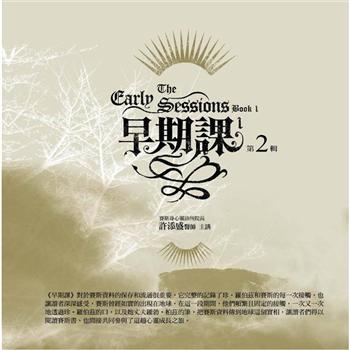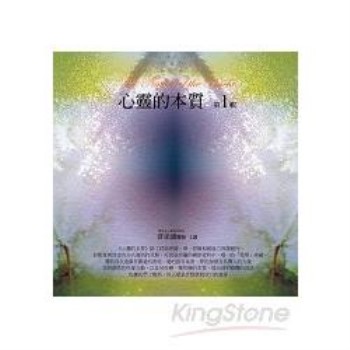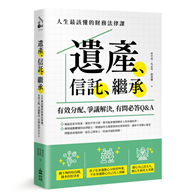第十一回 宰相再易兩重天 南詔平亂六萬兵
………………………
安祿山離京前一日,李隆基又在花萼樓賜宴送行,並令百官第二日將安祿山送出上春門。
此時滿朝文武官員皆被李林甫調理得乖覺恭順,昔日動輒上言的諫官早成了溫順的「立仗馬」,絕不會發聲奏事。凡李隆基的一言一行皆為至理,群臣整齊劃一擁護。如安祿山得如此殊遇,他們皆視為正常,唯聽旨奉承而已。
高力士此時也摸準了李隆基的性子,不敢妄發議論,這日瞧著李隆基的心情甚好,就大著膽子想再進言一回。
李隆基閱罷一道奏書,起身笑眯眯地踱步,轉對侍立一旁的高力士說道:「不空自從入了鴻臚寺,已譯出佛經一百一十部,計一百四十三卷。好呀,不空譯經甚多,堪與玄奘法師媲美,亦為我朝一件盛事了。」
佛學此時廣播天下,若以受眾而論,朝廷奉道學為第一國教,而道教信眾難及佛學信眾十之有一。李隆基起初對佛學不感興趣,像普潤為禪宗首領普寂之師弟,李隆基與普潤交往甚密,卻對禪宗沒有修習;然善無畏於天竺那爛陀寺修習密宗回國,李隆基從此對佛學密宗大有興趣,將此時最盛的佛學禪宗棄置一邊,封善無畏為「教主」;善無畏圓寂後,李隆基又封曾經赴印度和獅子國修習密宗的不空為「國師」,並將其迎入鴻臚寺譯經。不空由此與鳩摩羅什、真諦和玄奘並列,被稱為中國佛學史上的「四大譯師」。佛學密宗之所以傳入中國並得到發展,李隆基功不可沒。密宗教義與佛學其他教派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其將女性作為修學密法不可缺少的伴侶。其宣稱「隨諸眾生種種性欲,令得歡喜」,由此大得李隆基賞識,還親從不空法師受「五部灌頂法」,可見密宗獨得朝廷殊遇。
高力士衷心答道:「太宗皇帝昔日禮遇玄奘法師,今陛下又對不空法師優禮有加,遂使他們成為譯經大家,實為盛世佳話。」
李隆基此時不乏自詡之情,笑道:「朕於開元之初倡言依貞觀故事,高將軍,今日天下殷富安定,此盛景當與貞觀盛世相媲美了吧?」
「以天下人口及財富而論,此時應當優於貞觀年間,此為陛下之功啊。」
李隆基聞言心中得意,僅微笑不語。
高力士此時進言道:「陛下,所謂居安思危,臣近日有一些擔心。如今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
李隆基聞言收起笑容,凝視高力士道:「哦,你是替他人轉言?還是心中自有是思?」
高力士躬身答道:「臣也是一時想起。陛下,自從府兵制廢弛後,京中禁軍及宿衛之兵不足十萬,邊關卻屯集重兵。若某邊將生有異心,然後恃兵生亂,京畿之兵難以一時平叛,臣由是憂心。」
「你以為哪員邊將有異心呢?以各鎮兵力而論,自以安祿山、哥舒翰和高仙芝擁兵最多,他們皆忠心無比,怎麼會有異心呢?」
「陛下,臣非是疑心這些邊將,只是以為如今形成了內弱外強的格局,由此堪憂。」
李隆基笑道:「罷了,高將軍,好好地隨朕在京中享樂吧,你有些杞人憂天了。朕待邊將以滿腔關愛,他們如何會有異心呢?哼,朕為皇帝,只怕有異心之人還一時未生出來。」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目光堅定,說話甚為決絕,也就不敢繼續此話題了。
深秋過後,日子一日比一日寒冷起來,一場寒風席捲而來,氣溫為之陡降,又苦苦撐持數月的李林甫終於熬不下去了。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二日,一直以中書令或右相專掌朝政達十六年之久的李林甫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李林甫一生姬妾盈房,有子女各二十五人,子婿中有十人為三品以上大員。其在平康坊宅第發喪之際,宅中守靈者眾,前來祭拜者絡繹不絕。李隆基贈李林甫為太尉、揚州大都督,給予班劍2、羽褒鼓吹3之器,李林甫之哀榮可謂極矣。
李林甫死後五日,李隆基授楊國忠為右相,並兼知吏部尚書。李隆基起初欲授陳希烈為右相、楊國忠為左相,奈何陳希烈堅辭,楊國忠方能上位。
朝野之人聞聽楊國忠成為右相,皆大為感歎。有官階之人感歎一位蜀中閒漢竟然一躍成為右相,心中雖不屑,畢竟不敢吭聲;至於庶民百姓,將楊國忠能夠上位歸功於其有一個貴妃妹妹,遂又重複「生男不如生女」之感慨了。
楊國忠入李林甫宅中致祭的時候,李林甫的子婿們知道楊國忠如今得聖眷甚隆,遂模樣恭謹,前後侍候。楊國忠看到李府中人頭攢動,心中暗暗想道:「這個老傢伙,生前權傾天下,死後又哀榮無限,實為好命啊。」
楊國忠順口問李林甫靈柩的歸葬之期,李儒回答說因墓地營造尚未完工,估計靈柩還要在宅中供祭一段時日。楊國忠就責怪道:「李公生前病重多日,如墳地營造早該建好,你為李公長子,難辭其咎。」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唐玄宗(4):長恨遺歌(下)的圖書 |
![唐玄宗[4]長恨遺歌(下)](https://img.findprice.com.tw/book/9789865850739.jpg) |
唐玄宗[4]長恨遺歌(下) 作者:趙揚 出版社: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4-07-0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30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7 |
小說/文學 |
$ 194 |
歷史小說 |
$ 194 |
歷史小說 |
$ 198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唐玄宗(4):長恨遺歌(下)
天寶年,對唐玄宗來說是一個不幸的年代。對於大唐帝國而言,也是一個由盛轉衰的關鍵年代。
對李隆基而言,一個從女主手中重復李家天下的人物,卻因安逸於享樂自滿的生活中,繼以任人的失當,以致安史之亂起,將唐帝國的聲勢,一夕由最高處帶往最低處。
最後,必須犧牲自己所鍾愛的楊貴妃,以換取自己的苟活。一個有為的君主,卻落得如此下場,怎不教人唏噓?
【本書特色】
《唐玄宗》一系列小說是將中國史上有名的唐代君主李隆基的一生,以小說的方式重新演繹。希望藉由文學的筆調,讓歷史不再枯躁,不再刻板,能讓一般大眾接收、閱讀。將歷史中真實的人、事,透過輕鬆的筆調,真正的傳播出來,能使將歷史知識傳播出去。
作者簡介:
趙揚
中文系畢業,雖轉戰商海,仍筆耕不輟,已出版《金錢世界》等作品。認為閱讀是一種享受,創作是一門藝術,經常沈溺於文字而不能自拔。尤痴迷古典文學,心醉大唐盛景,窮十數年之功研究唐史。完成並出版歷史小說《唐太宗》、《唐玄宗》。
章節試閱
第十一回 宰相再易兩重天 南詔平亂六萬兵
………………………
安祿山離京前一日,李隆基又在花萼樓賜宴送行,並令百官第二日將安祿山送出上春門。
此時滿朝文武官員皆被李林甫調理得乖覺恭順,昔日動輒上言的諫官早成了溫順的「立仗馬」,絕不會發聲奏事。凡李隆基的一言一行皆為至理,群臣整齊劃一擁護。如安祿山得如此殊遇,他們皆視為正常,唯聽旨奉承而已。
高力士此時也摸準了李隆基的性子,不敢妄發議論,這日瞧著李隆基的心情甚好,就大著膽子想再進言一回。
李隆基閱罷一道奏書,起身笑眯眯地踱步,轉對侍立一旁的高力士說道:...
………………………
安祿山離京前一日,李隆基又在花萼樓賜宴送行,並令百官第二日將安祿山送出上春門。
此時滿朝文武官員皆被李林甫調理得乖覺恭順,昔日動輒上言的諫官早成了溫順的「立仗馬」,絕不會發聲奏事。凡李隆基的一言一行皆為至理,群臣整齊劃一擁護。如安祿山得如此殊遇,他們皆視為正常,唯聽旨奉承而已。
高力士此時也摸準了李隆基的性子,不敢妄發議論,這日瞧著李隆基的心情甚好,就大著膽子想再進言一回。
李隆基閱罷一道奏書,起身笑眯眯地踱步,轉對侍立一旁的高力士說道:...
»看全部
目錄
第九回 楊貴妃再出宮苑 李林甫重使陰招 228
第十回 李林甫病入膏肓 安祿山功至榮寵 257
第十一回 宰相再易兩重天 南詔平亂六萬兵 285
第十二回 國忠嫉恨安祿山 祿山再入華清宮 314
第十三回 安祿山伺機謀反 封常清痛失洛陽 340
第十四回 促戰潰敗失潼關 聞驚倉皇棄長安 369
第十五回 香魂歸葬馬嵬坡 太子北馳靈武城 396
第十六回 太上皇月下憶昔 古棧道霖雨聞鈴 424
第十回 李林甫病入膏肓 安祿山功至榮寵 257
第十一回 宰相再易兩重天 南詔平亂六萬兵 285
第十二回 國忠嫉恨安祿山 祿山再入華清宮 314
第十三回 安祿山伺機謀反 封常清痛失洛陽 340
第十四回 促戰潰敗失潼關 聞驚倉皇棄長安 369
第十五回 香魂歸葬馬嵬坡 太子北馳靈武城 396
第十六回 太上皇月下憶昔 古棧道霖雨聞鈴 424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趙揚
- 出版社: 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4-07-15 ISBN/ISSN:97898658507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0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歷史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