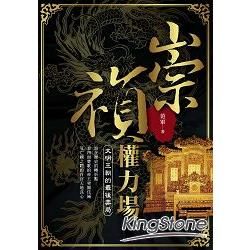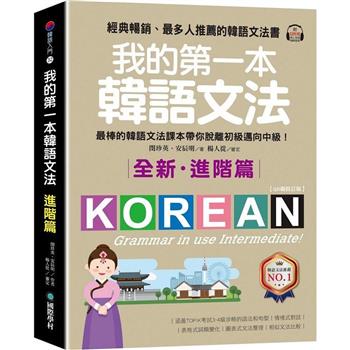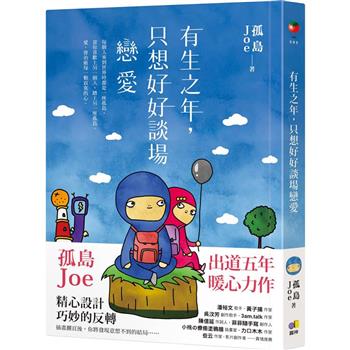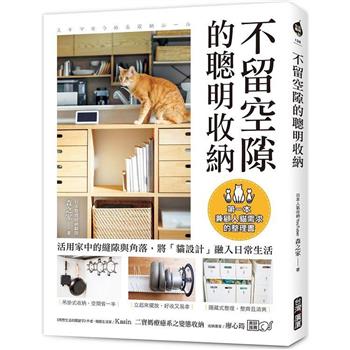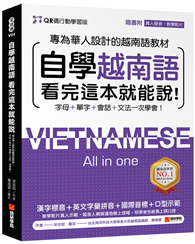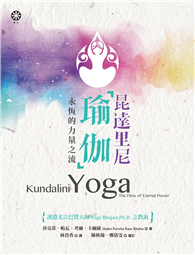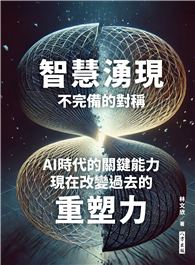第一章 撥亂反正
第一節 天啟七年帝國人與事
一六二七年,這個帝國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這一年是明天啟七年,後金先兵圍錦州,後再攻寧遠。死了很多人。
這一年十三陵開建;而在湖北武當山,玉虛宮一不留神發生了一場毀滅性的大火災,其軸線主要建築均遭火劫。死生之間,唯有灰燼。
這一年,那個在後世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人物馮夢龍刊行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
他在預示什麼呢?
而在此前四十五年,張居正死了。此前四十一年,國本之爭爆發。此前二十四年,妖書案起。此前十二年,梃擊案發。此前七年,紅丸案發。此前四年,魏忠賢掌東廠印。此前兩年,魏忠賢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名臣,毀東林書院。此前一年,浙江巡撫潘汝禎在西湖首創為魏忠賢建生祠,隨即蔚為風氣。
有工部郎中曾國楨建生祠於盧溝橋畔,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建生祠於宣武門外,順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於宣武門內,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墳邊上;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建生祠於孝陵前,河道總督薛茂相建生祠於鳳陽皇陵旁。短短一年中,魏忠賢的生祠遍地開花,一共建造了四十處。
建了祠就是拿來拜的。傳說有入祠不拜者,命立刻就沒了。
這個比較狠。
但是,一六二七年的天還是大明的天。
起碼表面上是這樣。
只不過有一個不安的消息在四處流傳:天啟帝熹宗病了。說是遼東戰事讓他總是心太煩,心太煩,熹宗他老人家又把所有問題都自己來扛,結果扛出病來了。
隨後,一個旨意傳出:天下大事,全由閣臣和廠臣們看著辦,別再煩我。
熹宗累了,這個酷愛當個木匠,在傢俱和家國之間曖昧不堪的皇帝決定給自己放個假。
病假。
這個旨意很是讓大臣們鬆了一口氣,卻讓魏忠賢倒吸了一口冷氣:大家看著辦,我可怎麼辦?因為──
長這麼大了,見過給死人建祠的,沒見過給生人建祠的。不說絕後,也算得上是空前了──只是魏忠賢不知道,空前的東西是不是要埋單的。
長這麼大了,見過給魏忠賢建祠的,沒見過給熹宗建祠的。他是萬歲,我是九千九百歲。是不是挨得太近了?我熱鬧,他孤單。我燃燒了他還是他燃燒了我?
最重要的,熹宗不動聲色地批准我建祠,是榆木腦袋還是大智若愚?他把我捧這麼高,是捧得高摔得重還是……
後熹宗時代,誰知我心?誰慰我心!
魏忠賢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延長熹宗的生命就是延長自己的生命。
挽救熹宗,有條件要挽救,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挽救。於是一個聰明的人在最恰當的時間以最恰當的角度切入了進來。他就是兵部尚書霍維華。他進獻了一個藥。這藥有個好聽的名字叫「仙方靈露飲」。
仙方的做法是:用淘淨的米按程式添水甑中,使鍋內的蒸氣迅速化為水,滴入銀瓶。最後取出滴滿的一瓶「靈露」,其實就是米的精華。
米的精華說到底還是米,魏忠賢太知道「仙方靈露飲」是怎麼回事了。他決定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魏忠賢找到錦衣衛都督田爾耕,說天要變了,宮廷政變也該搞了。但是田爾耕好像不聰明,他並沒有在最恰當的時機以最恰當的角度切入進來。魏忠賢又找兵部尚書崔呈秀談話,崔呈秀顧左右而言他,逼急了,冒出一句「恐外有義兵」,一副不合作、不負責、不舉報的態度。
魏忠賢這才知道什麼叫人心隔肚皮,這才明白那四十座生祠分明是四十座墳墓。的確,熹宗終究不是魏忠賢的明天。這一年的農曆八月二十二日,年僅二十三歲的熹宗朱由校全身浮腫地告別人間,將大明王朝的一大攤爛事、剪不斷理還亂的煩事交給後人處置。
那一刻,魏忠賢心亂如麻。
第二節 很多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國不可一日無君。
熹宗過世的第二天,魏忠賢就在午門外用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語調宣布:「召信王入繼大統!」
信王就是朱由檢。「入繼大統」就是繼承皇位。
這是魏忠賢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當然這個結果也是魏忠賢最不願意宣布的。
但是世易時移,一切都不得不發生。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崇禎權力場:大明王朝的最後弈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8 |
二手中文書 |
$ 383 |
社會人文 |
$ 396 |
歷史人物 |
$ 396 |
歷史人物 |
$ 405 |
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崇禎權力場:大明王朝的最後弈局
崇禎,明朝最後一位皇帝。他在內憂外患的情形下登上皇位。先將魏忠賢閹黨一舉剷除,又積極對後金戰略,然而將守遼重臣袁崇煥下獄處死,卻使邊患後金坐大。致力內政改革,卻又亡於李自成所率的農民部隊。他是一位極欲有為之君,卻成了亡國之君。箇中關鍵,頗耐人尋味。
崇禎王朝是歷史周期的又一節點。
從崇禎元年(1628)開始,在接下來的17年的時間長度裡,崇禎完成了大明帝國最後的收官動作。
崇禎帝朱由檢最初的突圍形象堪稱完美。他在逮治魏忠賢的手段和策略上從容不迫、遊刃有餘,顯示了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老到成熟;而接下來的事實也證明,崇禎是努力想成為一個有為之君的。
但「過猶不及」的悲劇性宿命在他的生命裡頻頻光臨。
在歷史大崩潰的前夜,一個帝王的焦灼、悲憫、怨天尤人、我行我素以及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複雜心態,浮出水面……
作者簡介:
范軍,浙江人,1969年出生。曾為報社記者、雜誌主編、影視公司文學策劃,個人出版有《最三國》、《我的明帝筆記》、《我的清帝筆記》等歷史類圖書。另有長篇小說《你不可突破我的底線》問世。現為《南方都市報》、《百家講壇》雜誌專欄作家。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撥亂反正
第一節 天啟七年帝國人與事
一六二七年,這個帝國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這一年是明天啟七年,後金先兵圍錦州,後再攻寧遠。死了很多人。
這一年十三陵開建;而在湖北武當山,玉虛宮一不留神發生了一場毀滅性的大火災,其軸線主要建築均遭火劫。死生之間,唯有灰燼。
這一年,那個在後世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人物馮夢龍刊行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
他在預示什麼呢?
而在此前四十五年,張居正死了。此前四十一年,國本之爭爆發。此前二十四年,妖書案起。此前十二年,...
第一節 天啟七年帝國人與事
一六二七年,這個帝國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這一年是明天啟七年,後金先兵圍錦州,後再攻寧遠。死了很多人。
這一年十三陵開建;而在湖北武當山,玉虛宮一不留神發生了一場毀滅性的大火災,其軸線主要建築均遭火劫。死生之間,唯有灰燼。
這一年,那個在後世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人物馮夢龍刊行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
他在預示什麼呢?
而在此前四十五年,張居正死了。此前四十一年,國本之爭爆發。此前二十四年,妖書案起。此前十二年,...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撥亂反正
第一節 天啟七年帝國人與事
第二節 很多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第三節 多米諾骨牌
第四節 倒魏運動
第五節 太監還什麼鄉啊
第六節 人人忌談《三朝要典》
第七節 可怕的大名單
第八節 藍圖與現實
第二章 遼東有事
第一節 這就是臨機專斷權?
第二節 兵餉大問題
第三節 過招毛文龍
第四節 帝國的漏洞
第五節 你有罪
第六節 被捕
第七節 祖大壽的選擇
第八節 袁崇煥該死
第三章 反腐!反腐!
第一節 雨一直不下
第二節 可怕的潛制度
第三節 御史崇禎
第四節 全朝皆腐
第五節 ...
第一節 天啟七年帝國人與事
第二節 很多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第三節 多米諾骨牌
第四節 倒魏運動
第五節 太監還什麼鄉啊
第六節 人人忌談《三朝要典》
第七節 可怕的大名單
第八節 藍圖與現實
第二章 遼東有事
第一節 這就是臨機專斷權?
第二節 兵餉大問題
第三節 過招毛文龍
第四節 帝國的漏洞
第五節 你有罪
第六節 被捕
第七節 祖大壽的選擇
第八節 袁崇煥該死
第三章 反腐!反腐!
第一節 雨一直不下
第二節 可怕的潛制度
第三節 御史崇禎
第四節 全朝皆腐
第五節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范軍
- 出版社: 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4-08-13 ISBN/ISSN:978986585082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80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