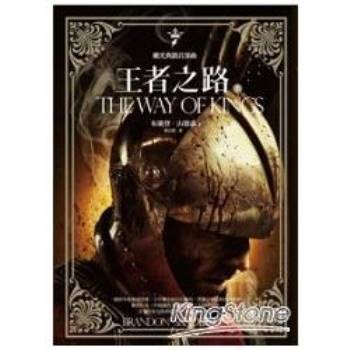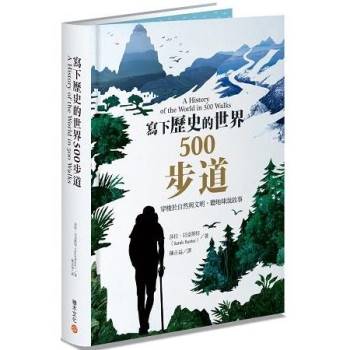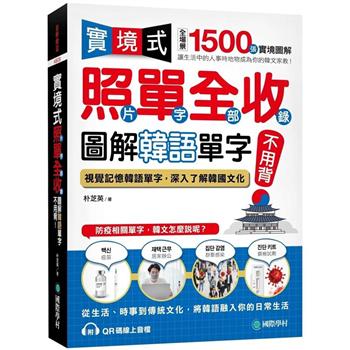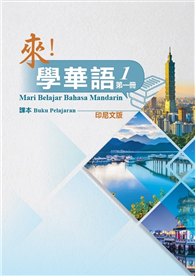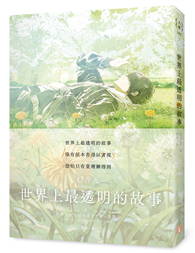親愛的和尚
蘇軾的家被安排在西湖邊的鳳凰山上,這是一處兩層小樓。那時的領導階級的官員住房還沒有面積標準,我們猜想蘇軾的府第應該是不錯的。因為當時的官很少,杭州是大州,有兩個通判,就是兩個副職,一共三個官,其餘的公務員都是沒有品級的小吏,不像現在,一個地方大大小小的一堆官員。因為官少,住房就好安排,面積可能相對大一些。
從蘇軾家憑窗而望,真是無敵風景。向南可以看見錢塘江口,波浪層層,帆船點點;向北看,滿眼西湖的美景。杭州西湖一帶的美麗風光,自宋代以來,在一些文人的筆記裡,有很多精彩的描述。那是一幅生動的圖畫!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是西湖一帶熱鬧非凡。這種熱鬧不像今天「連假」的熱鬧,人擠人,人挨人,不是看景,而是看人。那時的人們很悠閒,也沒有現在那麼多流動人口。杭州的絲綢在當時已非常有名,西湖岸邊有不少很大的絲綢店鋪,各地的絲綢商人會聚於此,各種新奇的車輛在杭州和西湖岸邊的街巷裡慢悠悠地行駛。街巷裡不時有一些流動的商販,賣一些兒童喜歡吃的糖人之類,讓人吃一口,就懷念一輩子。還有一些民間藝人在街頭表演。街巷兩側,除了大的絲綢店,還有一些民間藝術品商店和酒店、飯店,各式小吃店。酒店和飯店都備有一二小漁船,到西湖中打魚,現打現做,現做現賣。二是有一些貴婦人在西湖岸邊的淺水中洗浴。我想,這個記載不會有假。因為,一個地方有山有水就有靈氣,特別是碧波蕩漾的水,那是一個地方的靈魂,是特別讓人迷戀的。三是夜幕降臨,在西湖的深處,不時傳來陣陣悠揚的笛笙聲。這讓西湖又多一分浪漫情調。
杭州美到什麼程度?為什麼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你只有在這裡生活一段,才能真正感受到這裡真的如天堂一般。天造地設的山水,不燥不濕的空氣,不冷不熱的氣候,滋潤著這裡的人們。蘇軾品嘗到了杭州的美麗,也品嘗到了地方官官場生活的滋味。
這是蘇軾一生中的快樂時光,他完全像一個仙人,自在於美女、和尚之間,他熱愛杭州的風光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甚至覺得,故鄉眉山也沒有杭州美麗。他的一首詩這樣寫道: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
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做官怎樣才能竄升,有人說,「無所求,一切捨,當大任」。就是說,只有一心一意,一切都不顧,就想著當官這一件事,才能求得大任。蘇軾既要照顧老婆孩子,與名妓、和尚打交道,又要縱情山水,這怎麼能當大任呢?這是被逼出來的,他本來是一個宰相的材料,不是「走楣運」嗎?那就只好享受這地方官的快樂了。
蘇軾遊歷的足跡不僅遍布杭州附近所有的山,他還遠足上海、嘉興、常州、靖江等地。他喜歡一個人爬山,那讓他感到自由自在,又能喚起他對山水的思考,對人生哲理的思考。
他有時一個人向深山老林進發,不爬到山頂絕不甘休。累了,就找一處廟宇,進去歇息一下,和和尚聊聊天。
蘇軾有好多親愛的和尚朋友。
我們猜想,他喜歡和和尚交朋友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和尚在那個時代算是有文化的人,半個文化人吧。這些和尚從背誦佛經中學習到了很多知識,悟出了許多道理。他與和尚交流不但不困難,而且非常熱烈,不時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直到今天,我們讀到這些他和和尚們的有趣故事時,還經常捧腹大笑。
第二,和尚修行往往選擇靜謐、宜人之處。這些廟宇處在深山老林,常常是風景最絕佳的地方,而這正是蘇軾遊逛的必經之地。
第三,當時佛教盛行,僅杭州地區就有三百六十座寺廟。蘇軾本來就喜歡佛教,他在孩提時代就受佛教的薰染。老家眉山附近有很多佛寺,他經常和弟弟蘇轍一起到寺廟裡玩耍,特別是嘉州,就是現在的樂山,那是他進京的必經之地,那裡依山而雕鑿的世界上最大的佛,總使他產生敬畏之心。
可以說,儒、釋、道三教都對蘇軾產生過重大影響。他的媽媽程氏是一個道教徒,她為兩個兒子聘請張易簡道士作為他們的私塾老師;同時,為了應對科舉考試,他又讀的都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蘇軾和很多和尚的關係都很「要好」。他剛到杭州,就和孤山的惠勤、惠思兩個和尚有交往,寫下了〈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蘇軾和參寥和尚的關係也很密切。他貶官黃州期間,參寥還特地去黃州看他。此外,蘇軾還和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等和尚有往來。
流傳最多的是蘇軾與他的摯友和尚佛印的故事。依我看,這些故事很多都是後來的文人瞎編的,有些也可能是佛印自己編的,藉借蘇軾來揚自己大和尚的名。
讓我們來分享一下這些名人逸事。
佛印雖然是出家人,卻餐餐不避酒肉。這一天,佛印煎了魚下酒,正巧蘇軾登門來訪。佛印急忙把魚藏在大磬(木魚)之下。蘇軾早已聞到魚香,故意說道:「今日來向大師請教,『向陽門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麼?」佛印順口說出下句:「積善人家慶有餘。」蘇軾擊掌大笑:「既然磬(慶)裡有魚(餘),那就積點善,拿來共用吧!」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蘇軾宴會請客,他總是不請自來。有一天晚上,蘇軾邀請黃庭堅去遊西湖,船上備了許多酒菜。遊船離岸,蘇軾笑著對黃庭堅說:「佛印每次聚會都到,今晚我們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詩,玩個痛快,他無論如何也來不了啦。」誰知佛印和尚老早打聽到蘇東坡要與黃庭堅遊湖,預先在他倆沒有上船的時候,躲在了船艙板底下。
明月當空,涼風送爽,荷香滿湖。遊船慢慢地來到西湖三塔,蘇軾拿起酒杯,高興地對黃庭堅說:「今天沒有佛印,我們倒也清淨,先來個行酒令,前兩句要用即景,後兩句要用『哉』字結尾。」黃庭堅說:「好吧!」蘇軾先說:「浮雲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黃庭堅望著滿湖荷花,接著說:「蓮萍撥開,遊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這時候,佛印在船艙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聽黃庭堅說罷,就把船艙板推開,爬了出來,說道:「船板撥開,佛印出來,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蘇軾和黃庭堅看見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個人來,嚇了一大跳。仔細一看,原來是佛印,又聽他念出這樣四句,禁不住哈哈大笑。 蘇軾拉著佛印就座,說道:「你藏得好,對得也妙,今天到底被你吃上了!」於是,三人賞月遊湖,談笑風生。
還有一次,蘇軾、蘇轍、佛印三人結伴同遊。佛印即興出句:「無山得似巫山好。」這個詩句妙在「無」、「巫」的諧音上。蘇轍對:「何葉能如荷葉圓?」蘇軾聽了,對弟弟說「以『何荷』對『無巫』,固然不錯,但改作這樣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與蘇轍聽了,表示贊同,以「水」對「山」,勝在對仗更加工整。
蘇軾還曾對佛印開玩笑說:「你看,『鳥』這個字很有意思吧,寫詩的時候總是『鳥』對『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佛印立即接過話題說:「您不是坐在我對面嗎?我是『僧』,你是『鳥』啊。」實際上,蘇軾認識佛印是在黃州,那已是六、七年以後的事了。佛印住在揚州,什麼時候到過杭州,正史並沒有明確的記載,蘇軾的詩文中也沒有留下記錄。有一個荒唐的故事,說佛印和李定是同父異母,因為李定的媽媽很放蕩,嫁過三次人。這顯然是不帶髒字地罵李定,是瞎編的。
一些文人的筆記裡和民間傳說中,還憑空編造出一個「蘇小妹」來。蘇軾真的沒有這個親妹妹。他倒是有個姐姐叫八娘,嫁給了表哥程才之,因為飽受公婆的虐待,最後慘死在月子中。這讓蘇軾的爸爸很心痛,他公開把程家大罵了一通,與程家斷絕了關係。這件事讓蘇軾的媽媽很為難,這也可能是她早逝的原因之一。
有一件事我至今也沒有弄明白,蘇軾的媽媽怎麼就嫁給了蘇軾的爸爸?門不當,戶不對,這在那個時代是很不容易的。蘇軾的姥姥家可是個大戶,他姥爺當時在京城起碼是個正部級官員,怎麼就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一個目不識丁的老漢的兒子呢?
蘇軾的爺爺蘇序確實是個奇跡,他家五代都是農民,怎麼到了他就能白手起家,掙了那麼多家產呢?蘇軾的家是很有點錢的,他爸爸到處遊學趕考,只會花錢,不會掙錢,他們當年居然能在京城買得起一處房子,這都是他爺爺掙的。歷史造就了一個偉大的蘇軾,這其中恐怕有他爺爺一大半功勞。難道蘇軾的媽媽嫁給蘇軾爸爸的理由就是因為蘇軾的家還比較富足?或許是看上了蘇軾爸爸的才華,認為他是「潛力股」?
蘇軾還有個堂妹,是他二伯父蘇渙的女兒。歷史上很多人猜想蘇軾和他這個堂妹相互愛慕或者有曖昧關係。我想這是可能的。
蘇軾的爺爺蘇序去世的時候,他伯父帶著一家老小從京城回眉山老家丁憂,那時蘇軾大約十一二歲,他的這個堂妹也大約十一二歲。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在當時已經較成熟了,蘇軾納王朝雲為妾的時候,王朝雲才十二歲。一個京城裡長大的女孩,回到眉山鄉下,這讓當時的蘇軾怎麼看都覺得有不一樣的美麗。這個年齡的孩子容易產生「初戀」。
還是詩歌惹得禍。人們從蘇軾的幾首詩裡分析出他與堂妹的戀情。
他的堂妹嫁給了靖江的一個叫柳仲遠的青年,蘇軾在杭州任職時,去過靖江幾回。有一次在他堂妹家一住就是三個月,留下了「厭從年少追新賞,閒對宮花識舊香」的詩句。
人們就認為,他的堂妹就是「宮花」,就是「舊香」。人們翻閱了他記述這次到靖江的很多詩,還納悶,有和他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寫作遊歷的記述,為什麼一次也沒提到他堂妹丈夫的名字呢?
還有一首詩是寫給太守陳襄的:
羞歸應為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
與物寡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
玉臺不見朝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
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
人們怎麼也不明白,這首詩怎麼是寫給太守陳襄的呢?詩中「負花期」,「成陰結子」,「憐我老」,「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怎麼能跟陳太守扯上關係呢?分明是一首愛情詩,分明是寫給他堂妹的:「我這次歸來實感羞愧,因自己誤了花期,耽誤了你的青春,你看你孩子都有這麼大了。可憐我已經老了,你卻還那樣嫵媚動人,一直在空等這遲來的愛。從現在起你我就會年年相見,以後還要在一起像樊遲問孔子怎麼種菜一樣學習種菜。」
到底蘇軾和他的堂妹有沒有私情,這是人家的隱私,別人說三道四,都是瞎猜,瞎操心。看來,不論什麼時候,社會總是有一種窺視他人特別是名人隱私的心理。蘇軾和堂妹情深,不影響他的政治前途,也不影響他此刻輕鬆快樂地為官。轉眼三年的任期屆滿。北宋「京察三年」的制度比較嚴,就是三年任期一到,就要按照「德、能、勤、績」幾個方面對任職官員進行考核。考核後,該提拔的提拔,該留任的留任,該交流的交流,該調離的調離。
這三年,蘇軾混得不錯,與兩任主管的關係都處得不錯,處理政務也比較順手,這讓他得以輕鬆、快樂地去遊山玩水。但是,他的內心深處還在和變法派較勁,他寫了許多反對變法、反對朝廷改革的詩。
蘇軾的詩是不是反詩?同情他的歷代粉絲都說,那怎麼能是反詩呢?而告他狀的人不但認為是反詩,而且反動透頂,以至於後來神宗皇上也半信半疑。詩是藝術,容易讓人產生不同的理解。蘇軾的詩到底有沒有攻擊朝廷?你說他有,他就有;你說他沒有,他就沒有。
在蘇軾的主動要求下,熙寧七年(一○七四年)九月,朝廷任命蘇軾為密州太守。蘇軾的這個要求,完全出於想離他的弟弟蘇轍近一些,此時蘇轍在濟南任職。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蘇東坡官場筆記(上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3 |
社會人文 |
$ 220 |
歷史人物 |
$ 220 |
歷史人物 |
$ 225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蘇東坡官場筆記(上卷)
以文人的性格去面對官場的險惡,造就了蘇東坡與眾不同的人生。
本書可以稱為蘇東坡的公職記錄檔案。他憑藉什麼過人之處,而能平步青雲爬上高位?又如何慘遭牢獄之災?又為何願意擔任沒有一毛錢的虛官?在升降的過程中,蘇東坡有表現出什麼樣的態度?
本書特色
蘇東坡─
一位在官場起起伏伏多年的人,
他的一生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作者簡介:
桂園
一位將歷史變成新聞的文字工作者。
章節試閱
親愛的和尚
蘇軾的家被安排在西湖邊的鳳凰山上,這是一處兩層小樓。那時的領導階級的官員住房還沒有面積標準,我們猜想蘇軾的府第應該是不錯的。因為當時的官很少,杭州是大州,有兩個通判,就是兩個副職,一共三個官,其餘的公務員都是沒有品級的小吏,不像現在,一個地方大大小小的一堆官員。因為官少,住房就好安排,面積可能相對大一些。
從蘇軾家憑窗而望,真是無敵風景。向南可以看見錢塘江口,波浪層層,帆船點點;向北看,滿眼西湖的美景。杭州西湖一帶的美麗風光,自宋代以來,在一些文人的筆記裡,有很多精彩的描述。...
蘇軾的家被安排在西湖邊的鳳凰山上,這是一處兩層小樓。那時的領導階級的官員住房還沒有面積標準,我們猜想蘇軾的府第應該是不錯的。因為當時的官很少,杭州是大州,有兩個通判,就是兩個副職,一共三個官,其餘的公務員都是沒有品級的小吏,不像現在,一個地方大大小小的一堆官員。因為官少,住房就好安排,面積可能相對大一些。
從蘇軾家憑窗而望,真是無敵風景。向南可以看見錢塘江口,波浪層層,帆船點點;向北看,滿眼西湖的美景。杭州西湖一帶的美麗風光,自宋代以來,在一些文人的筆記裡,有很多精彩的描述。...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爺爺是個「淡定哥」
「一夜情」生出的皇上
考進士走了「後門」
在考試卷上瞎編
到基層鍛鍊
包容心是怎樣煉成的
不願做皇上的皇上
錯過了大好機遇
怎樣叫爸爸的無聊紛爭
幕後聽言,綠眉不展
王安石是個比蘇軾高明的「炒作」高手
我不幹了還不行嗎
「搏出位」的大賭注
在宋代K歌
親愛的和尚
黃狗臥花心
「官不修衙」建黃樓
「我拿什麼整死你,我的愛人……」
老大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落水的鳳凰不如雞
貧賤「草民」百事哀,世上沒有後悔藥
東坡種地,雪堂讀書
養生之道和「養國之道」
厚道不厚道
和長江的...
爺爺是個「淡定哥」
「一夜情」生出的皇上
考進士走了「後門」
在考試卷上瞎編
到基層鍛鍊
包容心是怎樣煉成的
不願做皇上的皇上
錯過了大好機遇
怎樣叫爸爸的無聊紛爭
幕後聽言,綠眉不展
王安石是個比蘇軾高明的「炒作」高手
我不幹了還不行嗎
「搏出位」的大賭注
在宋代K歌
親愛的和尚
黃狗臥花心
「官不修衙」建黃樓
「我拿什麼整死你,我的愛人……」
老大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落水的鳳凰不如雞
貧賤「草民」百事哀,世上沒有後悔藥
東坡種地,雪堂讀書
養生之道和「養國之道」
厚道不厚道
和長江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桂園
- 出版社: 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4-11-12 ISBN/ISSN:97898658509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開數:14.8*21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