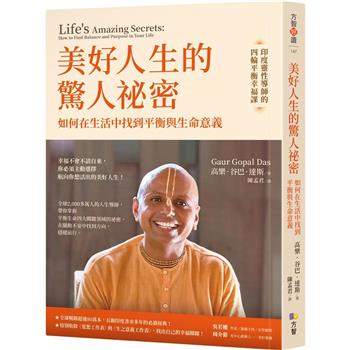施正鋒教授是國內知名的政論家,也是很用心於學術的政治學者。本書收錄他從美國學成返台,這20年來的各項觀察,也是瞭解台彎從威權到民主的每個轉折事件的學者看法。
20年來,台灣變化劇烈,施正鋒教授不只是文字上的關懷,他更投身社會運動與人文議題,他內心的夢,總是期盼著臺灣這塊土地,從暗夜到天光。
施正鋒這本文集,文字短而深邃,直而不曲迴,是一位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之作。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天光的台灣:施正鋒20年短篇文選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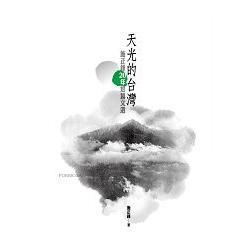 |
天光的台灣:施正鋒20年短篇文選 作者:施正鋒 出版社: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427 |
中文書 |
$ 428 |
政治評論 |
$ 428 |
社會人文 |
$ 428 |
小說/文學 |
$ 428 |
高等教育 |
$ 428 |
Social Sciences |
$ 450 |
台灣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施正鋒
從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赴美取得愛荷華州立大學政治學碩士、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返國後,任教淡江大學、東華大學,曾任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現為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工學系教授。
施正鋒的文筆,不拐彎抹角,有話直說,他在為文分析時,經常流露很濃的愛深責切之心。本書是作者這二十年來短篇文章的精選,大致已涵蓋這二十年來台灣社會每一個轉折的軌跡,是台灣發展變化縮小版的評述紀錄。
目錄
自序/筆耕二十年
一、天光時候:社會角落
001仲夏日的街頭午會
002天光與暗夜
003解嚴二十年
004卑微的犬儒也有感情
005街頭上的陽光
006鐵絲網的雷射光
007社運的落寞
008入夜的凱道
009傳道與說教
010暴力有三種
011黑污的民主白衣
012政客政黨政治
013推倒家園的國家機器怪手
014文林苑的國家暴力
015高雄港都的北中人
二、綠色草根:民進黨歡悵
016政黨的躊躇
017派系恐怖平衡
018黨主席的負荷
019黨綱的包裝行銷
020許信良悵然轉身
021扁式馴服術
022陳水扁向左走向右走
023權力的調整與權宜
024新潮流滔滔二十年
025派系戰國時代
026有體無魂稻草人
027新潮流的滾動
028茶壺裡的風暴
029大老的多愁善感
030黨主席的委曲
031長扁鬥嘴鼓
032大雷聲的小雨點
033小英的綠色危機
034民進黨的糟糠
035十八趴的小英
036鋸箭無法療傷
037三隻小豬的幻覺
038頭人與人頭
三、倉皇身影:扁朝興衰
039阿扁的正反面
040唐飛能飛嗎
041唐飛下台
042陳水扁的戰鬥
043興革先革心
044蔡英文安什麼心
045陳水扁揮長鞭
046長仔不想被看扁
047淚已流盡
048總統與律師
049歷史共業的眾生面孔
050派系山頭的綠色之光
051電火球決定不亮了
052阿扁的家後風暴
053扁朝風蕭蕭
054慘綠時光
四、藍色憂鬱:國民黨起落
055王金平被門戶之見
056人才的擁擠與排擠
057馬英九的練習曲
058馬英九聽政垂簾
059馬上火線
060馬總統迷路
061馬英九與中國的特別關係
062由學者內閣到選舉內閣
063馬英九夜未眠
064馬英九霧裡迷航
065中常委半蹲
五、絃外之音:不是藍綠
066陳唐山的台獨意義
067宋楚瑜的難言之隱
068李登輝與台聯
069泛藍的三角習題
070扁宋隔空抓藥
071政治妥協與立場堅持
072宋楚瑜告官
073旁觀者濁
074政策路線與政黨空間
075兄弟不能一起登山
076宋楚瑜最後一搏
六、圈圈遊戲:提名初選
077買人頭數人頭
078誰搶舞曲的拍子
079綠色水蓮
080口袋黨員與人頭養殖戶
081謝長廷拋繡球
082五都選舉的鴛鴦譜
083民選的人選
084提名機制的政治算盤
085美國式的總統初選
086民調與提名
087政黨初選與黨員登記
088溪水潺潺大河洶洶
089誰能畫出設計圖
七、門裡門外:選舉觀察
090一九九七的地方崛起
091派系抬頭與國會低頭
092選戰與選邊站
093選民配不配
094明天還會天藍嗎
095北高選戰南轅北轍
096不流淚也不投票
097台灣後山與濁水溪以北
098國民黨臉都綠了
099中間選民楚河漢界
100五都選後的綠色江山
101五都空笑夢
102不只一哩路的小英
103踏著沉重腳步的民進黨
104民進黨的大路與窄巷
105蔡英文卸妝
八、近在天涯:巨鄰中國
106帝國瓦解的虛張聲勢
107民進黨的中國結
108江澤民的舊唱盤
109陳水扁大膽喝茶
110兩岸裂縫的陰影
111廢統假戲真做
112海峽的兩岸想像
113馬英九的中國紅包
114民進黨的紅色虛線
115與虎謀皮或羊入虎口
116台灣人心裡的中國
117綠巨人的共識
118台灣人的不安心
119蔡英文不敢打開天窗
120經濟倚賴與政治包養
121穿西裝去跳舞的旅鼠
九、合縱連橫:外交角力
122官僚掣肘的坎坷外交
123外省族群的心靈撫慰
124咱的國家
125紅藍綠的政治調色盤
126台海有事的美日台波瀾
127布胡手忙腳亂
128務實與務虛的入聯
129科索夫獨立之夢
130吃角子老虎的無底洞
131國家安全的微軟
132軍購凱子與投機痞子
133外交休兵或休克
134台灣人的日本記憶
135台灣與美國的曖昧
136回不去的青春夢
137有組織的偽君子
十、風雨之中:憲政選制
138國會選舉制度
139行政與國會的拉鋸
140修憲與制憲
141權力分享與聯合政府
142憲改的想像
143假內行誑真外行
144修憲與反智
145螳螂背後的黃雀
146內閣制與總統制
147選舉制度的外拼與內裝
序
自序
筆耕二十年 施正鋒
思想啟蒙及文字鍛鍊
我從小喜歡塗塗寫寫,老師也蠻容忍的,好像也代表過學校去外面參加比賽。台灣人不會捲舌,無法字正腔圓,不過,動筆努力還是可以超越先天的結構性劣勢。高中聯考作文竟然掛零,低分掠過考上台中一中。回想當時的作文題目,依稀是要我們評論「客廳即工廠」政策,不喜歡歌功頌德,大概得罪了閱卷先生;日後當老師,對於有自己想法的學生,我會嘗試著去理解、甚至於欣賞。
高一的導師彭紫雲教國文(苗栗公館客家人,戰前日本青山學院畢業,二○一○年仙逝),恰好是父親早先二十多年前的先生。忘了是高幾的國文老師,要我們多唸《中央日報》的社論;然而,那些文字充滿教條,終於打斷我讀文科的念頭。誰會知道,現在除了接受稿約,竟然還當上報社的主筆寫社論。其實,中學時,還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地吸引著我,也就是父親不知從哪裡拿來的非國民黨人士所出版的刊物,包括黃順興等人;另外,數學老師黃呈明(彰化線西人)要我們趕快去買《台灣政論》,埋下有為者亦若是的種子,印證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所說的,現代的印刷術快速傳播民族意識,讓那些素未謀面的人可以凝聚成一種具有福禍與共的「民族」(nation),也就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民族運動」(nationalist movement)。
大學沒考上醫科,陰錯陽差進入台大農業經濟學系,誓願把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以及經濟發展讀好,其他的能應付就應付;由於沒有聯考的束縛,因而有很多的時間想東想西,尤其是不時跑到位於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去挖寶。嚮往自由的靈魂,碰上黨外雜誌百花齊放,剛好有另類的思想驅騁空間。參與了「大學論壇社」的外圍,認識了一些「搞怪」的異議分子,包括蘇煥智、劉一德和蘇瑞雲等等;想念那些沒有在政壇的兄弟,不知身在何處。
擁抱鄉土文學,正是黨外雜誌百花齊放之際。當時,只要風聞《自立晚報》「不小心」報導說哪一本被查禁了,立即跑到大學口的報攤去搶購;久而久之,跟老闆娘都有默契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根本不用開口。當然,查禁的單位也懂得不能殺雞取卵的道理,雜誌才可能永續經營,他們才有業績。對我來說,那都是省下自助餐的錢,吃飯不太敢點肉、更不用說魚,因此,結婚前的照片都是瘦巴巴的,彷彿是鄉下來的營養不良小孩,或是腸胃不好。
在這時期,恰好經歷「中」美斷交、中壢事件以及美麗島事件,步調快到無法想像。大學四年住在僑生宿舍,本地生不想住、教官也懶得管。一家烤肉、三家香,不管是《美麗島》或是《八十年代》,香港來的舍友雖然不以為然,卻會不時前來借閱,甚至於激烈辯論;他們的論點不外是只要有富裕經濟以及自由法治就好,為何要多事追求民主及獨立?比較特別的是,位於樓梯口的閱報室訂了幾份香港報紙,儘管是審核過的,尺度明顯比國內報禁解除前的媒體還來得開放;過了半夜,就只有我跟狗,我也屬狗,看來看去是一群狗,不過,還是有一些啟發。近年來,看到他們反彈中國的洗腦教育,倒是後來居上;反觀我們自己人習慣中國國民黨所灌輸的那一套,只能說這是一群「心滿意足的奴隸」。
真正有很強的驅策力動筆,是許信良在《長橋》雜誌寫了一篇文章,他把被巴基斯坦軍事政府吊死的總理布托描寫為殉道者,這跟我在Time、或是Newsweek所獲得的訊息大相逕庭,因此寫了一篇「布托─一個迫害反對黨的政客」(一九七九)來加以反駁。在畢業之前,又寫了「海格外交政策的困惑」、「薩爾瓦多國防軍謀殺了修女」以及「恒河下游的兒女──孟加拉」,刊在《縱橫月刊》和《政治家》。在草木皆兵之際,最大的問題是能投稿的地方不多。
金門當兵回來,白天在翻譯社上班,晚上又到中廣翻譯外電,拚命賺錢,希望能趕快存到第一年的學費出國。這時候,接觸到的國際資訊更多,特別是重大事件的背景分析,令人喜出望外。每天半夜回到家裡,繼續寫稿,偷偷在《生根》以及《台灣年代》等黨外雜誌發表文章,包括「亞美尼亞人的獨立運動」以及「庫德人──世界的孤兒」等等文章。不過,那時候已經開始體會到,必須更上一層樓,透過知識的吸收,以及專業訓練,才能超越自己,否則,只是在「整理」別人的想法;換句話說,除了「知道」東西,更必須有自主「分析」的能力。
白天的工作是翻譯藝術百科全書,除了要認識藝術的專有名詞,最重要的挑戰是有固定的篇幅,除了要求信雅達,還必須一對一,不能多、也不能少;不過,這是很好的訓練,以後碰到有字數的限制,就知道要如何裁剪,不要為難邀稿的朋友,讓對方覺得學者不講道理、文章落落長。另外,在中廣當編譯的磨練,也是難得的經驗;經過福州師傅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特別是口語化的要求,不能過於艱澀,要讓沒有看到文字的人也都能聽得懂。
平面媒體的邂逅
在留學美國七年間,雖然在同鄉的刊物《鄉訊》,以及同學會的《台灣學生》寫了不少東西,卻沒有在台僑的報紙真正寫過東西,只有一篇「咱第三代的前輩黃信介」被《台灣公論報》轉載。除了留學生與同鄉的關注差異,可能還與理工科與社會科學的專業要求不同,總是覺得論理的方式迥然不同,或許因此沒有很強的投稿動機。其實,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依然很少主動向報紙投書、而是應邀寫稿居多,臉皮比較薄吧!在這裡,我們收了兩篇被拒絕刊登的稿子,大概是被認為不夠「鹹」(聳動)。(編按:即『長仔不想被看扁』、『電火球決定不亮了』)
在一九九一年回國任教,次年才開始寫報紙的專論,那是在加入台灣教授協會後,由於隸屬法政組,被安排在《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立早報》以及《自由時報》寫「台教論壇」。台灣人讀社會科學的本來就不多,即便有也以法律居多;即使是政治學博士,基本上未必願意加入台教會,因此,被要求做雜務的機率當然比別人高很多,因而接觸很多一般學者不願意碰的議題。除了使命感以及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不服輸,每次碰到新的課題,就很想做起碼的瞭解,並且問自己:如果是讓你做決策,應該要如何著手分析?
剛開頭的十年,被邀稿的機會其實不多,平均一年不過十篇左右,而且往往是燃眉救急。記得當時小孩還沒有上學、不識字,然而,當我拿著報紙興沖沖的想與他分享,說今天有爸爸的文章,這是「我e名」;久而久之,他還沒看到報紙,遠遠地就會說:「施正鋒」。其實,當時的困境之一是自己的中文生疏許久,往往立即的反應是英文概念或詞彙,常常必須拿出《大陸簡明英漢字典》,由英文單字來查適切的漢字,真是痛苦萬分。當然,現在可以邊寫邊線上搜尋,方便多了。儘管如此,由於耳朵分不出ㄓㄔㄕ與ㄗㄘㄙ的差別,時常必須嘗試錯誤才找得到正確的字,因此,到目前為止,注音輸入還是有些障礙。
在這同時,台獨聯盟出錢辦《台灣評論》,雖然並未公開盟員身分,卻自然而然擔任主筆,算是練筆的好機會。後來,先後擔任文宣部主任以及發言人,不時撰寫聲明稿,而且往往是短時間內必須交差,而黃昭堂主席思慮周延,習慣退回再三修改,相當嚴格,甚於斥責又不是跟人家相罵,不要用那麼強的字眼;還好有預官步校「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的經驗,即使高深莫測,也是敬謹受教。
真正比較像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e writer),是開始接受《聯合報》邀稿之後,以台獨的立場回應中國的政策,或是以本土派的觀點觀察民進黨。一開始,由於台教會在林山田的帶領下發動「退報運動」,因此,只敢接受訪問。後來,李永熾老師鼓勵說,反正神父跟牧師傳道沒有甚麼幫助,不如趁機會打開台派的言論市場,從此放膽寫稿。雙方有共識,文章內容原則不動,而標題可以由編輯決定而花俏一點,只有一次「小鳥依人」被一個女編輯刪掉,因而好一陣子藉故推辭不寫。
當時的輿論界視《聯合報》為保守派的報紙,而《中國時報》則似乎類屬於自由派。通常,《聯合報》遇到重大事件,在傍晚開完編輯會議後,就會立即來電邀稿、甚至於請人畫漫畫配合;如此禮遇,讓藍綠雙方支持者覺得無法理解。相對地,《中國時報》則會做比較長的規劃,譬如大選之際。在二○○五年初,《中國時報》開始邀請我寫「觀念平台」,每兩個禮拜一篇、三個月一個週期,可以說正式成為專欄作家,一直到淪陷為止。這段期間,自由自在寫了不少非政治的議題,算是快意人生。
本土陣營部分,在一九九五年底出現的《台灣民族晚報》,社長施建生熱情提供篇幅、長短不拘,彷彿是有一塊租借地,直到一九九九年夏天為止。兩千年大選期間,接受劭立中的邀請,使用英文在Taiwan News寫了幾篇專欄,嘗試過美式的幽默,順便把不方便明說的看法偷偷釋放出來。在二○○一年幫《台灣日報》寫過幾篇專論,至於《自由時報》,則除非經過安排,很少主動投稿,因為其有特別的政策偏好及政治傾向,也就是教育關懷及反三通,否則,被退稿的機率相當高;另外,由於字數要求越來越短小精悍,頂多只能短打,往往無法暢所欲言。不過,也有一篇長文「大前研一的五大邏輯謬誤、四大錯誤認知、三大用心惡毒」(二○○三)(編按:本書割愛,未收入)破例被接受,連兩個圖都登出來,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主筆的日子
在二○○四年,《話題雜誌》邀我擔任主筆。在二○○七年夏天,蘇進強邀請我擔任《台灣時報》主筆,展開寫社論的生涯,差不多半個月一篇,劉志聰接任總主筆時亦然。沒有想到,當念理工的陳茂雄接手後,更加頻繁,有時將近每週一篇;當時在東華大學擔任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一職,時常在行政會議上接到電話,問說「正鋒兄,今那日甘(敢)有閒寫社論?」往往必須在會議結束後騎腳踏車,衝回原住民族學院的辦公室開機趕稿子;迄今,這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在二○一○年春天,他還邀我每個禮拜寫一篇專論,剛好補「觀念平台」的青黃不接;為了應付週一交稿,週末都在構思,我因此建議他每三個月一輪,免得壓力太大。
前副總統呂秀蓮在二○○九年創辦《玉山周報》,義不容辭擔任主筆,也是時常扮演救火隊的角色,特別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議。從劉志聰、王崑義到葉伯祥,都會來電邀稿,大概每個月寫一篇,甚至於到後期,幾乎每期都有文章,寫到連自己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雖說是周報,其實是比較像縮短週期的政論雜誌,因此,字數允許比較長一點、而且時間也比較充裕,可以做比較深入的討論,這是一般報紙無法享有的奢侈。
在二○一二年初,經過學生的建議,我開始加入臉書(FB)的行列,從此,多了一個分享理念的管道。在復活節前後,爆發「文林苑」事件,我發憤研讀美國的法院判例,把心得PO(上傳)到FB臉書,得到相當的迴響,原來,老百姓也是有想要瞭解公共議題的欲求,就看掌控輿論的菁英是否用心書寫。我後來發現,FB臉書除了有透過社交群來進行傳播的功能,最大的特色是以圖片的辨識為主,因此,必須考慮如何以圖來吸引朋友閱讀文章;不過,找圖的時間可能比寫文章還長,相當傷眼睛。
長輩誇我下筆很快,其實,這是被逼出來的。一開始寫專論,都是台教會的秘書處在排班,有時候,幾個月前就決定了;戰戰兢兢,希望能在政治分析中偷渡一些學理的知識。冷板凳坐久了,慢慢地有上場機會,即使是代打也要保握,想辦法讓自己從B軍變成A軍,有點像是必須先在NHK紅白歌合戰(歌唱大賽)參賽,才有機會在壓軸上演出。一般而言,寫稿的時間約六個小時(聯合報傍晚五時至十一時、台灣時報中午十二時至六時),有時候,對方會情商提早交稿,不過,至少也會有四個小時;偶而有不去不行的婚宴,可以預留版面,九點多趕回家,必須在兩個半小時完稿,這是一種自我挑戰。
其實,不管是一個月、一個禮拜、還是一天前,結果差不多,差別在於文字的斟酌,往往改到最後是四平八穩,缺乏原汁原味。到目前為止,最為好友津津樂道者,是在微醺的狀態下,未加任何修飾就e出去的文章。早期,老婆還會幫我再讀一遍,看是否會過於簡約跳躍;現在,兩人晚上還是忙,一個在書房、一個在客廳用手提電腦,已經沒有家庭警總審查。當然,有時候在第二天的早餐桌上,還是會被批評寫得太深奧、塞的東西太多。
我有自我要求的標準,也就是起碼的正確描述外,必須有切入的分析框架來幫助思考,以求合理的解釋及預測;當然,絕對不能拾人牙慧,更不允許事後諸葛亮,因為,那是對自己專業的不尊重。其實,早期的記者很厲害,除了報導、還擅長內幕解析,譬如朱玲惠、朱浦青以及已過世的樊嘉傑,我瞠乎其後,只能從理論著手,看是否能提供基礎的概念及架構,來達成社會教育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個人的看法如何並不太重要,在乎的是讀者是否能學到思考的方式,在下一回就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卻又能做有系統的分析,沒有必要仰賴菁英的詮釋。
對我自己來說,最滿足的地方是能說服記者或政治人物接受我的觀點;如果看到引發的媒體討論順著我的調子、甚至於用字淺辭大同小異,也可以讓人虛榮地高興一整天。坦白說,政治分析比較簡單,至於進一步的政策建議或是制度設計,因為大家各有盤算,很難立竿見影,必須長時間不斷陳述,才有可能曉以大義、循循善誘。另外,事過境遷,能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也可以自豪當年的訓練是紮實的,以及學以致用的努力是有成果的,作為知識分子,這樣的社會責任就夠了。《讀賣新聞》在二○一二年大選之前要我預先推測,如果不同的人當選總統,將會有何種內外挑戰及走向,這又是新的嘗試。
「預言」與「預測」的區別
我在一九九一年回國到淡江大學,教政治學、公共政策、國際關係等等。當時,學校的招牌是未來學,院長要我代表院去學校開會,負責所謂的「政治未來」。我一直沒有很大的意願,因為我的專長之一是「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老師警告我們不是算命的,不會未卜先知,我一直謹記在心。
當時,由於國際關係或區域研究的學者未能預測蘇聯解體,對於整個削術界的打擊很大,特別是所謂的「克林姆林宮學」(Kremlinology)專家。記得剛到學校沒多久,在校車上,同仁跟我分享一個故事:一位戰略專家上電視分析中東情勢,信誓旦旦美國絕對不會打伊拉克,結果,老布希在第二天就出兵了。
這裡,牽涉到的是學者的專業責任。就科學的過程而言,當一個事件(event)變成公共議題(issue)之後,接下來的工作不外乎正確的描述、合理的解釋以及有效的建議,如果以醫療過程來看,就是問診、病理、藥理(或治療)三大項。當然,如果行有餘力可以做預測(forecast),具體而言,就是根據先前的觀察和歸納,嘗試建構一個將重要變數納入的模型,然後,假設某些變數變動的情況下,會有幾種可能的發展。
我們一般比較熟悉的是氣象預測,經濟學家往往會有相當複雜的計量模型。政治學的預測模型比較難,主要是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瞬息萬變,有效掌握比較困難,特別是個性;當然,口是心非、打死不認,也是常見的反應,更不用說,當事人很可能並不清楚自己行為的意義。儘管如此,比較外交政策還是有些初步的概念架構幫我們分析,尤其是在心理學家的幫助下,理解決策者的特色,包括個性、興趣、理念、訓練,以及角色等等因素。
我們必須指出,預測並不等於預言(prediction),也就是說,我們是科學家、而非算命仙。差別在於後者鐵口直斷,至於問他為甚麼,答案千篇一律是天機不可洩漏;而前者則必須有一個理論支持的分析架構,指出因果分析,然後考察變動的因素,再綜合推測可能的影響。
基本上,科學預測是建立在合理的命題(proposition),也就是在何種條件下,可能會有怎麼樣的發展,而非憑空杜撰的臆測(conjecture)。當然,有經驗的學者不會只是吊書袋,或是光把相關因素列出清單就好,而是要進一步找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potency),以及可能發揮運作的情境條件(contingency)。就這一方面而言,我發現比較外交政策的訓練與經濟學有相通之處。
就先前大家熱烈討論的民進黨人頭黨員,除了制度設計的思考,要如何解釋背後的政治結構因素?在戰略三角的態勢下,邏輯上有多種發展的可能,而最簡單的盤算是兩邊加起來大於第三邊,這是當年美國與中國建交的想法,季辛吉並沒有更複雜的理論。也就是說,為了避免見樹不見林,當然要做合理的解釋。政治結盟是有默契的,政客不會昭告天下、也不會正式簽約。要判斷我的分析是否合理,就看民進黨全國代表大會,只要維持以全民調辦理初選,我推測的短期目標就是正確的,其他,還有中長期目標,敬請檢驗。
政治人物的干擾
人都有立場,以及價值觀,這是避免不了的。然而,我也很珍惜自己的專業信譽,特別是從事政治分析之際,事後一定會再確認,如果有差錯,必須檢討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當然,絕不允許盲人摸象或是後見之明。其實,各行有各行的規矩,儘管要求不同,卻還是有相對的客觀標準。
許多年前,我被某團體要求做政治情勢分析,在政治老前輩之前班門弄斧,最大的挑戰是有不少政治運作是密室進行,只能做合理的假設,再根據可能變動的部分去推論。報告結束,眾人紛紛發問,主要是討論前提假設,或是論理是否合宜。不過,有一位學法律的長輩質疑,很多事情都還沒有發生,怎麼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律師的責任講求證據,目的在於罪行認定的攻防,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頂多是選擇性呈現。這是法律系畢業的職業性反應,卻未必適用在一般的行為分析。
然而,政治學的功能不同,除了要解釋已經發生的行為,還要做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我們的政治觀察透過媒體的報導,會進一步左右輿論,這時候,政治人物考量得失之後,極可能會調整既定的行為。如果政客因此改弦更張,再來沾沾自喜挑戰我們的預測不準確,只能說,那是自欺欺人,因為,我們至少達到嚇阻的效應了。
以外交政策而言,除了採取行動,還有可能決定不為所動(decide not to act)、緩兵之計(no decision),或是猶豫不決(hesitation);問題是,在沒有具體的行為時,很難判斷是哪一種動機,這時候,就看觀察家的經驗及能耐了。拿到國際場域來看,外交本來就是爾虞我詐的,而軍事上也有欺敵戰術,一般的說法是聽其言、觀其行;然而,當對方出兵的時候才猛然大悟,這時,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以希特勒為例,為了全力攻打法國,先跟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等到攻下巴黎,沒有半句廢話,馬上出兵打史達林格勒,史達林啞巴吃黃蓮,只能自認判斷錯誤,可以要求日耳曼人因為食言而肥而道歉嗎?
順便揭露一個密辛。我在二○○四年秋天於《聯合報》寫了一篇「陸委會的整併,蔡英文為甚麼反對?一人決策?制高點決策」(編按:本書改題為『蔡英文安什麼心』),一大早,到淡水就接到電話,質疑為何要在「匪報」修理她?接著是,這些她都還沒有做,憑甚麼做這樣的推測?其實,動機論是很無聊的,因為我的立論很簡單,純粹是從憲政原理的總統職權切入:
蔡英文認為,一人決策是危險的,如果是指總統的話,他/她至少還有民意基礎做後盾,難道,部會首長一人定案就會比較英明?其實,以美國來看,總統好比是腳踏車的中心軸承,而部會有如不可或缺的輻射形支條,也就是說,總統的決策一定要根據相關部會提出的政策規劃,不可能只是由總統府的幕僚來做準備工作。
不過,令她耿耿於懷的是下列政治判斷,彷彿洩露了不可告人的天機:
令人好奇的是,已經當過政務官的蔡英文,究竟只是單純的為舊日部屬爭取高級文官出路的保障,或者是總統府與行政院的仍然步調不一,又或者民進黨內部盍各言爾志,只是為了年底的選舉策略中的中國政策做定調的先聲,也就是新潮流的對中鴿派姿態,為全面接班打基礎呢?
或許是因為法學與政治學的專業訓練差異,彼此對於事後追究犯行、事先的政治情勢估計有不同的重視、或是純然是個人氣度的問題?總之,這是第一次碰到政治人物有這樣不可理喻的反應,可以說是嘆為觀止,因為不管是藍營或是老共,即使立場不同,至少表面上還要客客氣氣地講點道理,更何況是不應罪及妻孥!
政治學的訓練告訴我們,政治行為往往是隱諱的,必須抽絲剝繭、旁敲側擊,絕非人云亦云,更不能當政客的傳聲筒,那是丟臉的事。我們有義務把觀察到的分享給其他人,如果因為戳破政客苦心所包裝的美好形象,惱羞成怒要告誹謗,更是匪夷所思。坦白說,我們的民主迄今還停留在投票主義,選民要負很大的責任。一些人事不關己,一些人則崇拜英雄,四處拜神、找神、甚至於造神,看法不同的就打成異端,宛如中世紀歐洲的獵巫。
感謝與期待
在這二十年當中,總共寫了大約五一○篇篇,我先選了三○○篇左右,之後篩選到一七○篇,最後定稿成一四七篇。首先,我要感謝多年來安排我寫稿的朋友;我也要感謝我的讀者,尤其是打電話來的朋友。當然,更要謝謝翰蘆圖書出版公司的洪詩棠發行人,若非他的鼓勵,沒有想到會出版這本小品文集。最後,特別要感謝家人的寵愛及包容,這些都是犧牲家庭生活而來的。然妻孥也因為我而在工作崗位上、在學校裡受到特別的「待遇」,因此,這一本書應該要獻給你們。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是建立在有獨立思考、自主判斷的選民,真誠期待那天早日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