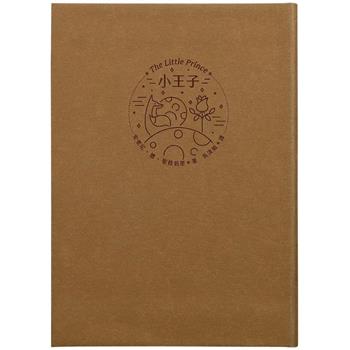導讀
山外是天
這不是本女人寫的書,更好說,女人寫不出這樣的一本書。
什麼樣的書必須由女人寫?什麼,必須由男人寫?應該是個不存在,也不一定值得花心思的議題。然而《日落呼蘭》中,那般的硬與殘,是出自女性作家手筆的事實,確實令人驚訝!是書中情節必須有的霸道、斷殘、粗鄙,讓曹明霞得以練就「男人一身厚實肌肉而擁有爆發力」,並在履踏、揮手的同時,讓大地搖擺、雲層湧動?還是明霞的原本天性在這故事裡得以延伸發展,如同那升了空的紙鳶在山外的高天遨遊,不能回轉?
那些事也不過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之前,歷史學家或許以「近代」在時間軸上標示定位;就地理空間來看,事出地點也只是地球上的一隅,那個高遠寒冷,玉米雜糧拚命生長的地方。然而,那些事件發生之前、期間以及後續的作用與影響,讓人不得輕易小覷,因它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多少人生死與共的悲傷年歲。如同教堂壁上需要精心維護的馬賽克鑲嵌細工,缺了《日落呼蘭》所述及的,既魔幻又真實的那一塊,人類史就只能拼湊得遺憾了。
中國東北抗日戰爭十四年。那是歐洲德國納粹形成,亞洲日本企圖實現東亞共榮大夢的時期;也是勤快老實的洪慶山從十四歲少年直到二十八歲,成了兩個孩子父親的時期;更是在小鋪裡藏賣鴉片煙的金吉花、掉入自滿陷阱的崔百歲、懷抱羅盤身分不明的洪福隆、滿頭蝨子有好脾氣的玉敏堂妹、時不時以煙袋鍋打人的小腳三嬸、和嫂子的嫂子有曖昧關係的崔良田,以及寒冬時以鮮牛糞溫暖赤腳的慶林、慶路,在小興安林麓經驗流離翻轉生死的顛沛時期。
明霞的鐵驪鎮及其周遭的山脈野嶺與呼蘭流域是個巨大而滾燙的火鍋,她的火箸聚焦在殘忍與不公,撈起入口的,是可以吃得明白的碎石、枯枝與餿肉。這是個令人神傷的麻辣鍋。從「民國快叫滿洲」到「熱烈歡迎日本皇軍」,以至「歡迎共黨隊伍」,一系列的翻天覆地在那一大片黑土黃地上,撕心掏肺,痛苦不堪地完成。在那兒,炕上的被襖就要是破爛棉絮;在那兒,鍋台上有成群的蟑螂走過;在那兒,女人頭上的蝨子得要拿煤油嗆,「才會暈頭暈腦從頭髮裡向外爬」;在那兒,「小孩拉屎大人不管,狗會舔」;在那兒,「院裡的雞屎鴨糞被豬牛蹚個滿地」。
西渡而來的殖民主,見雞挑雞,見鴨踩鴨,姦污女人,還罵「支那女人,豬」。這些和「畜牲」交媾了的什麼東西,「一生氣就把三嬸的煙袋桿了撅折了……還踢了慶路一個跟頭」。
從東洋來了一批批開拓團的成員,他們要在望不到邊際的大地上定居繁衍,世世代代。讓「支那百姓流著大和民族的血」,讓中國孩子和日本孩子在學校裡同聲高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而強佔民屋的法子則是中國人自己為他們的殖民主所設想,讓「南綆的二流子、看瓜地的高傻子,還有一些無業遊民,他們都來到了三嬸的當院兒。有直接對著門撒尿的,有坐在院裡摳腳丫的。高傻子……,脫掉了褲子,旁若無人抓起了蝨子。……三嬸盛了一盆冷水,對著那些人潑了過去。一個二流子說,冷水把他激病了,他得上炕養傷。……真的上了三嬸的炕……蓋起了被子。高傻子也學著那個人的樣,光著?(屁股),向炕上爬」。
即便是酷刑也不例外,那孫翻譯不就提供了日本軍官,滿洲山林裡,搶匪對付叛徒,叫「望天」的樹刑?夏天,當河邊柳樹枝幹既堅硬也柔軟,將削尖了的主幹插入受刑者的下體,在樹幹彈向穹蒼的剎那,受刑者也隨之仰臉望天!
山高嶺峻,一個再適合不過了的,塑養半人半獸的魔境。赤匪、土匪、山賊、義勇軍、救國會,一旦上了曠野,入了山徑,不論是快速殺人還是絕處求生,個個幹得乾淨又麻利。抗日者的能耐是,「只要入了山,就像樹葉兒掉進了林子,找不出來」。而日本皇軍「進山剿過多少次,整不淨,滅不絕」,最好是「餓死他們,困死他們。讓他們沒吃沒喝,沒穿沒蓋,最後像那些冬天的樹,活活風乾在林子裡」。
抗日聯軍在林子深處,鑽進荒草偽裝的地窨窩棚休憩,以環山急行迷亂追兵,在馬尾綁樹枝,邊走邊掃除行路痕跡;在雪地上築起擋風雪牆,砍樹枝舖地睡上。「夜晚不滅的火堆把前面的身子烤得焦燙,後背卻是冰涼徹骨」。他們啃嚙樹皮,生米就著雪吞。米沒了,「腳上的馬皮扔火炭兒裡,燒軟了,放在嘴裡嚼」。在如許艱困情境下,人性退位,獸性發揚,所有行為均以生存與活命為唯一指標。
這種「好人進了警察署,不死也要變白骨」的世道,這種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因愚昧、迷信,在粗鄙髒亂的環境裡,以抽大煙為休閒,以嫖妓為娛樂,缺乏教育,有志難伸,受迫遭辱,諂媚當道,搖尾橫行之時,一種悄靜的巨大勢力正不動聲色地趨近人體,滲透肌膚,侵入心髓。「種糧的挨餓,伐木的沒屋,出力流汗的沒有好日子過」的民間控訴,正是這股無形無嗅力量堅實的脊背支柱,是共產黨得勢的開始。
曹明霞對事情的安排一件接一件,目不暇給,是一齣沒有冷場的好戲。有些段落更如同偵探小說的佈置,迂迴、神秘、出其不意。她的文字樸實,不打結、不矯情,更含有攝影機效果,正如「三嬸那隻眇眼,左右一晃,慶山就能把她看過的地方收拾得乾乾淨淨」所顯示。那些不論在什麼語言都難以找到正確表達的擬聲字,明霞卻是隨手一捻,傳神而中聽。
在一個冬天的「太陽像白蘿蔔」、「樹葉如魚鱗」,以及「小姑娘對誰都辣辣」的地方,曹明霞式的家道中落是搭建後的拆毀:是慶山的父親把「房屋的四周由最初的柳條圍欄,換成了整齊高大的木柵板,無論從遠、從近看,都是個正經人家了」,後來三叔「把木柵板又慢慢變回了柳條枝兒,柳條枝兒在冬季裡又變成了燒柴。從前引為家園邊界的木柵板,用逶逶迤迤的小草棵來代替了。」
明霞只在故事最後含蓄地提起國共就要爭天下。其實《日落呼蘭》大可以是一系列東北人民在中國近代生活遭遇的起始。在特有語言、特殊風情的基礎上,以這書的調性與寫法繼續發揮,應該可迴避政治上刻意加予而牽引出來的無謂糾紛。這一期待中的系列故事,只要耐著性子,寫得深、寫得細、寫得招蜂引蝶、寫得蕩氣迴腸,也就接近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們青睞的文學體系之一。
至於貫穿全書的慶山怎麼告訴他那兩個失去日本母親的孩子,山外究竟是不是天?山外的天,可不可以是尋常百姓安身立命的地方?這事,或許留待他的孩子告訴他會清楚些。
顏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