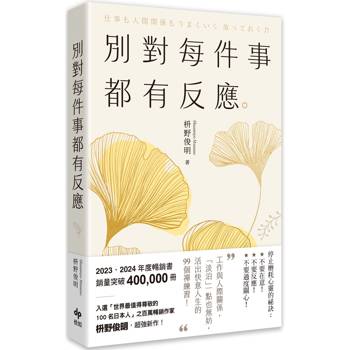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將軍與蓬萊米:陳長慶小說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24 |
小說 |
$ 252 |
小說/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小說 |
$ 288 |
小說 |
$ 288 |
現代小說 |
$ 288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2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將軍與蓬萊米:陳長慶小說集
戒嚴軍管時期,金門長年駐守著數萬大軍,金防部直屬的四大營區中,更有數十顆星星在閃爍,他們美其名叫「將軍」。即便多數是身經百戰、戰功彪炳、學養俱佳的將領,但亦有少數不學無術,僅懂得逢迎拍馬求官之道的軍中敗類。同一時期,金門特約茶室少說亦有百餘位從事性工作的侍應生為三軍將士服務,她們自願承受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苦難,冒著砲火的危險來到金門這座小島討生活。當時,金門地區實施戰地政務實驗,期間不少鄉親因不知戒嚴軍管的利害關係而一時失察,或說錯話,或寫錯字,或誤觸法網,而被移送軍法究辦。本書四篇小說均以該時期為背景,並以各個角度切入,由故事的主人翁帶領讀者走入軍管時期的金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