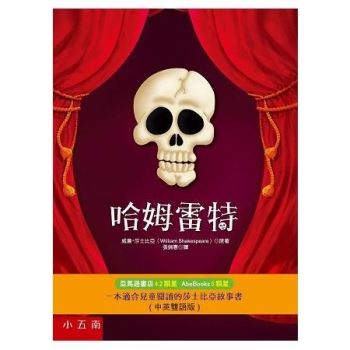重巒疊嶂、溝壑縱橫、綿延七百餘里的雪峰山,中日兩國數十萬軍隊在此展開了中日大規模會戰的最後一戰——湘西會戰!
雪峰山會戰中,有一支獨特的抗日民眾武裝──他們是以瑤民獵戶為主的「鳥銃隊」,被日軍稱為「嗅槍隊」──他們於山路打伏擊、夜襲新寧縣城、馳援武岡、為中美空軍指引轟炸目標……就是這些由獵戶、舊日山匪、地方士紳、教書先生、女學生、雇工、老兵油子等組成的隊伍,令在幾十年後「戰地重遊」的日軍旅團長感喟,難怪當年自己敗得那麼慘,轉而不能不讚歎,山民,了不起!
本書特色
本書生動地刻劃了抗日武裝山民的保家衛國之情,而中日高級將領的對決、戰局變化莫測的轉換、終至最後的勝利,精采絕倫,不容錯過。
作者簡介
林家品
中國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壇湘軍「七小虎」之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野魂》、《熱雪》、《從紅衛兵到跨國黑幫》、《蠱惑之年》、《生番女兵》、《老街的生命》、《兵販子》、《花橋》、《蔡和森》等,共計八百多萬字。作品《熱雪》獲第三屆中國煤礦文學烏金獎長篇小說第一名,《老街的生命》獲國際亞洲太平洋戰爭文學獎第一名、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提名,亦被改編拍攝成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