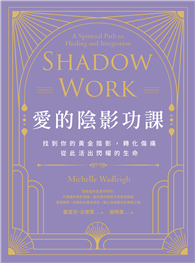標題:重慶鄉間的狗及其它
一
夜裡,狗對著過路的板車發瘋地亂叫;
白天,又對著臭氣熏天的糞坑狂吠;
道士只要在做法事,狗便吼個不停;
連傳教士的小狗保羅也「汪汪」得乾脆。
豬肉是宴席上非常高級的菜?
學究論書
菜農論蔬
漁人論魚
屠夫論豬1
夫子不論魔法――子不語?
馬在草地上打滾――驢打滾?
我們禁不住笑了。
標題:小 學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1
學習就是高聲朗讀,
就是不析義、不綜合、不數學。
而學堂亦是「在黑夜中穿上華貴的衣服。」2
那老師用戒尺打他11歲的頭
他就哭著回家,讓妻(童養媳)3
一邊安慰他,一邊用黑色膏藥塗他的傷口。
後來,他患了水腫病
易於激動的他拒吃藥、大哭鬧,好吃西瓜
之、乎、者、也,奈如何
三年後,他命赴黃泉,留下一個寡婦。
注釋
1.語出《三字經》。
2. 其語義如成語「錦衣夜行」。亦可見司馬遷《史記》卷七,中華書局,1982,第315頁中項羽所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在沈德潛所著《古詩源》(中華書局,1977,第216頁),我讀到:「夜衣錦繡,誰別真偽。」
3. 「童養媳」,又稱「待年媳」、「養媳」。「童養媳」的名稱起源於宋代,元、明、清時,童養媳從帝王家普及到社會,一般人家往往花少許錢從貧民家買來女嬰或幼女,等到養大後,作為自己的兒媳,如此一來,也便節省了許多聘禮。童養媳在清代時候已經甚為流行和普遍。在中國社會,童養媳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女大男小,當然,這也並非是一個絕對現象。不過這裡「讓妻(童養媳)/一邊安慰他,一邊用黑色膏藥塗他的傷口」,正是這種女大男小的現象。另外,由於童養媳多是孤女或貧寒人家的孩子,在婆家往往受到虐待,如果遇到惡婆,虐待尤甚。童養媳成了受苦的代名詞。有一首土家族民歌〈十八歲的姑娘三歲郎〉,反映的即是這種現實:
十八歲的姑娘三歲郎,
不要陪嫁只要糖,
站起沒有桌子高,
睡起沒有板凳長。
板凳長喲!
十八歲的姑娘三歲郎,
天天要奴抱上床,
睡到三更要吃奶,
奴當妻子又當娘。
又當娘喲!
十八歲的姑娘三歲郎,
夜夜要奴抱上床,
睡在床上屙泡屎,
打濕奴家花衣裳。
花衣裳喲!
十八歲的姑娘三歲郎,
夜晚要奴哄上床,
不是奴家公婆在,
郎當孩子奴當娘。
奴當娘喲!
十八歲的姑娘三歲郎,
奴家夜夜守空房,
童養媳婦命最苦,
命苦像喝黃蓮湯。
黃蓮湯喲!
十八歲的姑娘三歲郎,
叫聲阿爹喊聲娘,
砸破封建舊世界,
同樣媳婦永不當。
永不當喲!
順便說一下,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位童養媳的形象光芒四射、彪炳千秋,她就是關漢卿筆下著名的竇娥。《竇娥冤》第一折,關漢卿這樣寫道:「老身蔡婆婆,……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個孩兒,年長八歲,……這裡一個竇秀才,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我數次索取,那竇秀才只說貧難,沒有還我。他有一個女兒今年七歲,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個媳婦,就准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於是乎,年幼的竇娥,即因父債,入了蔡婆婆家做了童養媳。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史記:晚清至民國──柏樺敘事詩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31 |
華文現代詩 |
$ 290 |
中國歷史 |
$ 290 |
中國歷史 |
$ 297 |
華文現代詩 |
$ 297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30 |
詩 |
$ 33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史記:晚清至民國──柏樺敘事詩史
繼《史記:一九五○~一九七○》後,詩人柏樺又一部敘事詩史,
獨創以注釋解說表徵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詩」,
並從書報取材,展示了中國晚清至民國這一時期的生活觀和現實處境。
本書以晚清民國書報等材料作為創作題材,從構思、布局、選材及運作與前書《史記:1950-1976》並無二致,這正應了一句古訓「世間萬物皆出一理也。」
詩共140首,企圖從歷史的片段與細節,企望照亮那個時代「黑暗的森林」,重現歷史真實的面貌。
本書特色:
詩人柏樺取材自書報,獨創以注釋解說表徵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詩」
作者簡介:
柏樺
1956年1月生於重慶,現為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中文系教授。柏樺是公認的中國當代最優秀的抒情詩人之一,其詩作受到海內外廣泛的推崇和讚譽。著作有詩集:《表達》(1988 ,灕江出版社)、《望氣的人》(1999,臺灣唐山出版社)、《水繪仙侶──1642-1651:冒辟疆與董小宛》(2008,東方出版社)、《史記:1950-1976》(2013,秀威出版社);回憶錄:《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200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等。
章節試閱
標題:重慶鄉間的狗及其它
一
夜裡,狗對著過路的板車發瘋地亂叫;
白天,又對著臭氣熏天的糞坑狂吠;
道士只要在做法事,狗便吼個不停;
連傳教士的小狗保羅也「汪汪」得乾脆。
豬肉是宴席上非常高級的菜?
學究論書
菜農論蔬
漁人論魚
屠夫論豬1
夫子不論魔法――子不語?
馬在草地上打滾――驢打滾?
我們禁不住笑了。
標題:小 學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1
學習就是高聲朗讀,
就是不析義、不綜合、不數學。
而學堂亦是「在黑夜中穿上華貴的衣服。」2
那老師用戒尺打他11歲的頭
他就哭著回家,讓妻(...
一
夜裡,狗對著過路的板車發瘋地亂叫;
白天,又對著臭氣熏天的糞坑狂吠;
道士只要在做法事,狗便吼個不停;
連傳教士的小狗保羅也「汪汪」得乾脆。
豬肉是宴席上非常高級的菜?
學究論書
菜農論蔬
漁人論魚
屠夫論豬1
夫子不論魔法――子不語?
馬在草地上打滾――驢打滾?
我們禁不住笑了。
標題:小 學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1
學習就是高聲朗讀,
就是不析義、不綜合、不數學。
而學堂亦是「在黑夜中穿上華貴的衣服。」2
那老師用戒尺打他11歲的頭
他就哭著回家,讓妻(...
»看全部
作者序
小序
早在寫作《史記:1950-1976》的中途――注意:此「中途」並非比附但丁那家喻戶曉的名句「當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我就萌生了要寫晚清和民國的「史記」。接下來,順理成章地,寫完《史記:1950-1976》,便又埋頭於浩瀚的晚清民國的書報等材料,但我並非「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而是企望照亮(其實也照亮了,至少許多部分被照亮了)那「黑暗的森林」(即:在昏暗中沉睡不醒的晚清民國書籍、報紙和材料)。
《史記:晚清至民國》從構思、布局、選材及運作與前書《史記:1950-1976》並無二致,這正應了一句...
早在寫作《史記:1950-1976》的中途――注意:此「中途」並非比附但丁那家喻戶曉的名句「當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我就萌生了要寫晚清和民國的「史記」。接下來,順理成章地,寫完《史記:1950-1976》,便又埋頭於浩瀚的晚清民國的書報等材料,但我並非「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而是企望照亮(其實也照亮了,至少許多部分被照亮了)那「黑暗的森林」(即:在昏暗中沉睡不醒的晚清民國書籍、報紙和材料)。
《史記:晚清至民國》從構思、布局、選材及運作與前書《史記:1950-1976》並無二致,這正應了一句...
»看全部
目錄
小 序
卷一 晚清筆記
重慶鄉間的狗及其它
小 學
地 痞
榜 樣
母與子
回鄉偶書
問 道
成都反洋暴亂
一位軍機處要員的日程表
知禮的車夫
舉 止
節儉二事
燈 下
驚 蟄
恭維對方貶低自己的對話模式
神 樹
面部毛髮問題
辮 子
剪辮傳說及處方
怪 事
苦力的收支
在山西
在四川
不相及
說 膽
儒教說
與辜鴻銘對話
清廷財神赫德及其團隊
我愛你,中國
伯 駕
丁韙良的痛苦
夜上海
海上四大金剛之林黛玉獨佔五貢
小 趣
秋石:小便備忘錄
抄倉山舊主《酒話...
卷一 晚清筆記
重慶鄉間的狗及其它
小 學
地 痞
榜 樣
母與子
回鄉偶書
問 道
成都反洋暴亂
一位軍機處要員的日程表
知禮的車夫
舉 止
節儉二事
燈 下
驚 蟄
恭維對方貶低自己的對話模式
神 樹
面部毛髮問題
辮 子
剪辮傳說及處方
怪 事
苦力的收支
在山西
在四川
不相及
說 膽
儒教說
與辜鴻銘對話
清廷財神赫德及其團隊
我愛你,中國
伯 駕
丁韙良的痛苦
夜上海
海上四大金剛之林黛玉獨佔五貢
小 趣
秋石:小便備忘錄
抄倉山舊主《酒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柏樺
- 出版社: 釀出版 出版日期:2013-07-03 ISBN/ISSN:978986587157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4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