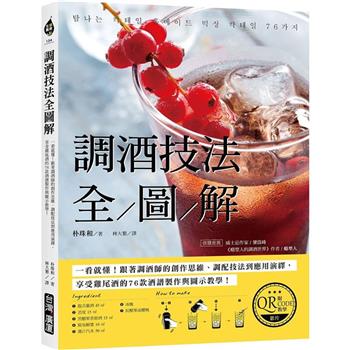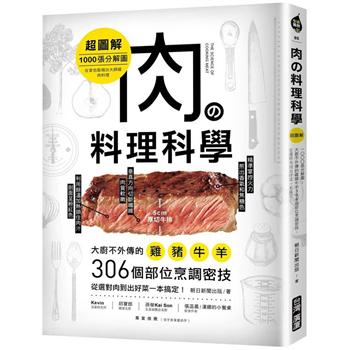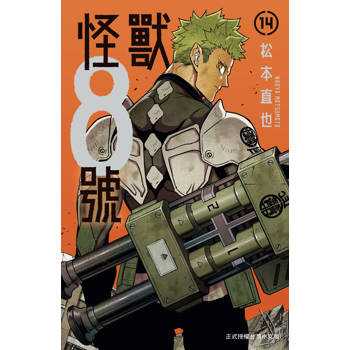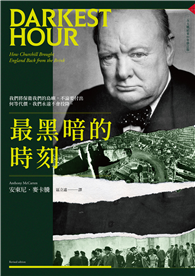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我與父親的戰爭:反右、文革時期心靈成長小說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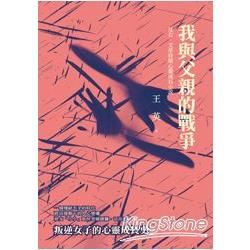 |
我與父親的戰爭:反右、文革時期心靈成長小說 作者:王英 出版社:釀出版 出版日期:2014-02-2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20頁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86 |
小說/文學 |
電子書 |
$ 350 |
華文創作 |
$ 395 |
中文書 |
$ 440 |
現代散文 |
$ 450 |
小說 |
$ 450 |
現代小說 |
$ 450 |
文學作品 |
$ 450 |
中文現代文學 |
電子書 |
$ 500 |
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我與父親的戰爭:反右、文革時期心靈成長小說
臉上帶著粉紅色胎記的「小小」,自出生就被父親嫌棄,認定小小是他命中註定的剋星。同時父親把在「反右」和「文革」中所遭遇的怨恨和憤怒宣洩到小小母親身上,無休止的家庭暴力,使得母親毅然帶著小小逃離了這個家,過著備受歧視和寄人籬下的生活,從此小小在一個幾乎與男性世界隔離的狀態下生活。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她不參與任何形式的武鬥。改革開放後,哪怕有機會進身仕途,卻甘願放棄入黨入團等機會,而選擇了文學。以一種內在的意志,尋找那個她認為真正屬於父親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