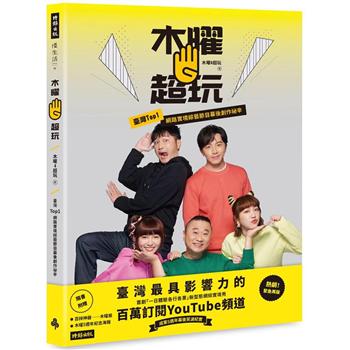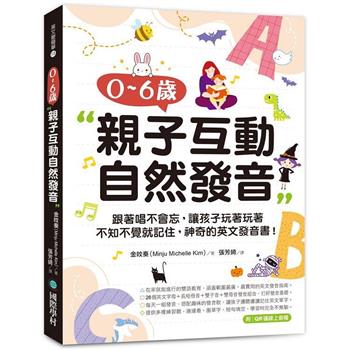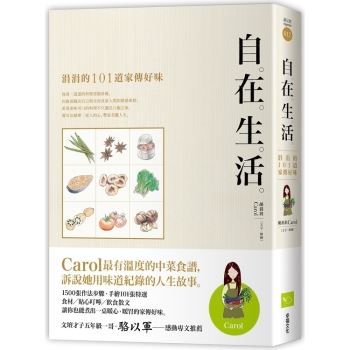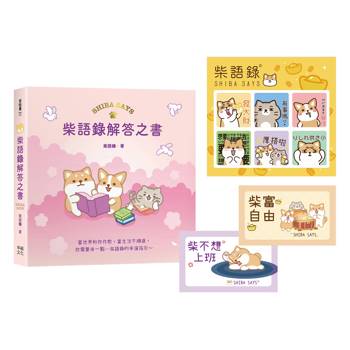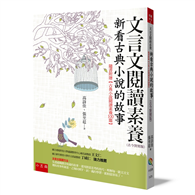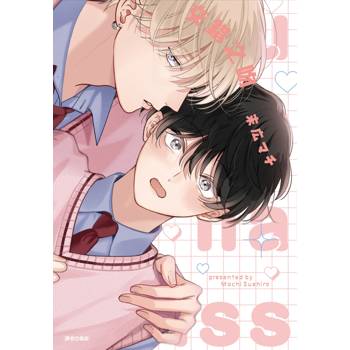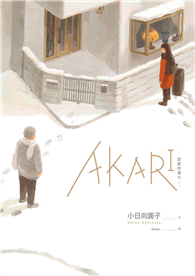亞馬遜五顆星滿分評價,各大國際書評一致好評!
《紐約客》專欄作者的真情告白,一段重拾父親身影的記憶之旅!
對於家族情感最深層的思索與追尋,獻給所有讀者的催淚詩篇!
《紐約客》專欄作者的真情告白,一段重拾父親身影的記憶之旅!
對於家族情感最深層的思索與追尋,獻給所有讀者的催淚詩篇!
帶著傷痛難癒的心靈,乘載著你未曾離開過的靈魂,踏上風景與回憶穿插,重拾夢想和探索內心的跨國旅程。
人們總是盡其所能地迴避面對「死亡」,都期盼活在樂觀的朝陽下,不讓悲傷與哀慟進入自己視線所及的人生中。面對親人的逝去,痛或許會被時間淡化,但也有可能在時間的醞釀加成下,讓自己作繭自縛無法逃脫。
即將邁入十一歲的維多莉亞,她身為男同志的父親因為飽受HIV疾病摧殘之苦,選擇踏上自殺一途。原本以為至親離去的傷悲,長大後就會隨著時間撫平,但每當想起父親在八歲時說要帶她去看看世界卻未能實現的夢想時,又感受到無以名狀的痛苦,並設想如果當時兩人能夠成行,一切會有什麼不一樣,因此懷抱著父親的靈魂而前往彼此當年約定的目的地。
「維多利亞的道別」是描寫一位女兒解開逝去父親身上的謎團、探尋自己的心歷路程。這是一本赤裸裸的回憶錄,裡面描寫著女主角前往斯德哥爾摩、柬埔寨、巴黎等地方去尋找她那難以接近、又充滿魅力的父親踪跡,並慰藉父親的在天之靈。對女主角來說,她的父親永遠就是一個四十四歲的男人,而他們的父女關係會永遠存在,她所能做的事就是向父親的過去道別。
各界書評&推薦
精神科醫師&暢銷作家 鄧惠文
Tizzy Bac主唱 惠婷 ──動人推薦
亞馬遜五顆星滿分評價,各大國際書評一致好評!
《紐約客》專欄作者的真情告白,一段重拾父親身影的記憶之旅!
對於家族情感最深層的思索與追尋,獻給所有讀者的催淚詩篇!
文字絲絲入扣,將一位女兒對父親最親密且愛恨糾葛的告白赤裸呈現。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作者以優雅細膩的字句、漸進式的深入,勾勒出一位年輕女性自我探索的心歷路程。
—《出版人週報》(Publishers Weekly)
在這本回憶錄裡,維多莉亞一邊揭露對父親的回憶,一邊描述自己在世界各地旅行的點點滴滴。她所形容的父親是一個看似冷靜表面下,獨自飽受於病魔及心魔折磨的男人。內容苦樂交織,但都能帶給讀者許多感動。直率的文字為父親送上最後的告別。
—《書單》(Booklist)
所有傷痛欲絕的情感.會無止盡地牽動著彼此的生命,卻對你我沒有任何助益。若能轉化為緬懷的力量,如同透過放大鏡般,讓所消逝的摯愛其生命體驗,透過另一種方式呈現,世人就能感受到他曾存在過的悸動。
—龐克搖滾詩人 派蒂‧史密斯(Petti 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