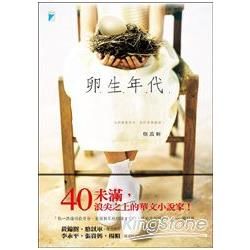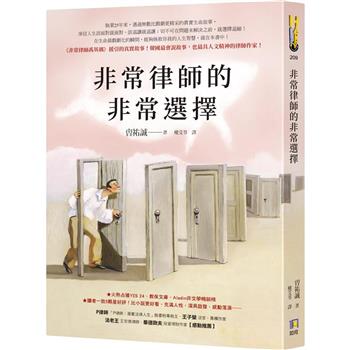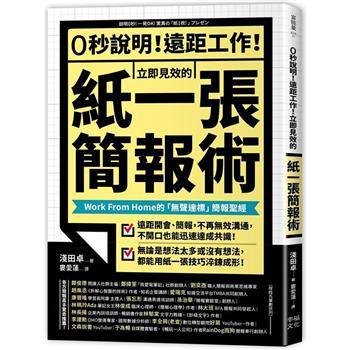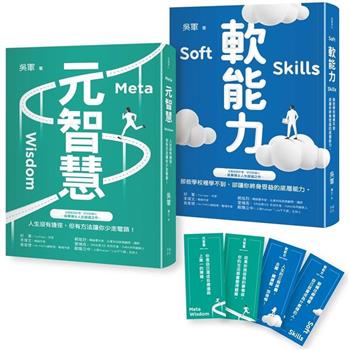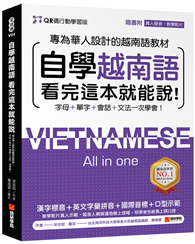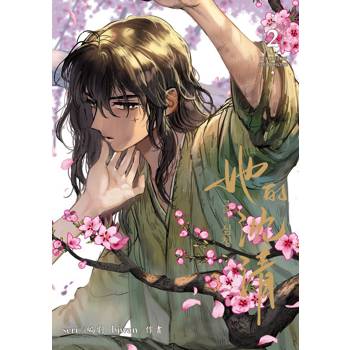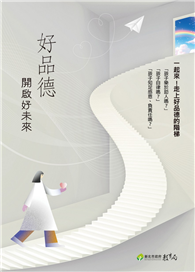推薦序一
鴨嘴獸的呢喃--序龔萬輝小說集《卵生年代》◎黃錦樹
在寫作人不多、但文學之火不熄的馬華文壇,一九七六年出生的龔萬輝,無疑是四十歲以下的寫作者中最受期待的之一。雖然他的作品並不多(馬華本土迄今也沒有多產的傳統),在他最初的兩本書(一本小說一本散文)似乎也帶著相當明顯的駱以軍的風格痕跡--雖則相較於駱的華麗淫猥,萬輝的文風顯得淺白甜膩得多;沒有那麼重的著色,沒有那私人馬戲團式的家庭劇場,也沒有那麼狂野的想像。但在時空的處理、母題、隱喻的偏好等方面,還是斑斑可考的。也即是說,在寫作之路上,(縱使是局部的)駱腔已然成了萬輝明顯的負擔,昔日啟發他寫作靈感的導師已是他必須克服的對象了。他應該有能力走出來的,這新集子裡的部分作品即是見證。
這小說集共分三輯,各三篇,長短不一。寫作與發表都在近幾年內(有六篇是這兩年內的)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十幾歲的少年,尤其是前面兩輯的作品。九篇中有兩篇我在前年參與海鷗文學獎評選時就讀到了,很奇怪的有日本都市青春小說的感覺(尤其是那篇原題〈鏡子〉的〈折光〉),情感與欲望的糾結,觸鬚般的文字感受--連主人公的名字都像。
但最令人好奇的還是書名,雖然集子裡有篇小說題為〈卵生〉,還是令人費解。作者的〈後記〉並沒有清楚的解釋。我用時下流行的通訊方式問了,他的答覆(經當事人同意不嫌冗長)徵引在這裡,以被轉述的形式幫他自己說明:
生物學上有個理論,演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說,當魚演化成爬蟲,當身上的某些器官退化消失,那就是一條不能退後的路。鯨永遠不會再長出鰓,人類不會再長出尾巴。我覺得有趣的是,生物演化的過程也是一種時間的隱喻,沒有退後的餘地,充滿錯失的不歸之路。
如果把人類的演化過程濃縮成人的一生的話,十幾歲的青春期大概就是卵生動物的階段吧,姑且稱為「卵生年代」。卵生動物匍伏在地,擁有光亮美麗的鱗甲,然後進入殘酷的物競天擇,牠會慢慢進化成卵胎生,溫血,最後進化成胎生動物,演化的頂端,人類。
我想,在這段不斷嘗試、不斷錯失,以及開始意識到性,又驚恐成長的階段,是極其迷人又迷惘的。我的這輯小說多寫少年,其實也是一種回望,或者是對無可迴避的「最終還是要演化成人」的現實的一種抵抗。
因為寫的是成長,時間已逝的過往,所以把這本小書題為「卵生年代」。--11/11/2012臉書通話紀錄
依這樣的說法,這本小說應是部成長小說,告別未成年,但又對它戀戀不已。但這說法和小說的〈後記〉是有衝突的。
嚴格的說,「卵生年代」的說法只適於小說前二輯的六篇,也即是袁哲生〈寂寞的遊戲〉、駱以軍《遣悲懷》第二書裡改寫過的「祕密洞」遊戲的那種童年、少年敘事,自在的探索未明的世界,一直到性的邊界、這樣那樣的傷害。而〈後記〉發出的強烈的傷悼之音是典型的哀樂中年的感慨--老去的父母的亡故--終究會遇到的,當你活過了一個年齡,除非你選擇提前結束此生(如袁哲生等)。一如多年來受邱妙津之死困擾的賴香吟最近在《其後》裡清楚表明的。不論是朱天心的《漫遊者》,還是駱以軍的《遠方》,都是闖進生命裡的故事。雖然集子裡只有一篇〈遠方的巨塔〉(這本書三篇最好的作品之一),但悼逝的強音蓋過了相較之下比較文學化的「卵生」論。或許因為這樣,它壓抑掉我前面那段引文,那段自白。
相較於〈遠方的巨塔〉,〈後記〉是雙倍的哀悼:小說裡還活著的那個父親,在〈後記〉裡也猝然死去了。第三輯除了第二篇以外勞為主人公的〈一趟旅程〉(她十九歲),另兩篇的主人公,一篇年近而立,一篇則頗有疑問。〈後記〉中的「這幾年」更有力的把時間從前引文中彷彿帶殼的「卵生」拉到當下:無可挽回的胎生、靈長類,故事本身強烈的呼應著〈遠方的巨塔〉,賦予它一個自傳背景,敲響了「事實的金石聲」(張愛玲語)。庶幾讓駱以軍的讀者不致誤以為這又是對《遣悲懷》開篇、結尾著名的〈運屍人〉--一個兒子坐捷運送母親的遺體到台北城另一端的醫院器捐(那來自一則真實的新聞報導)--的擬作。出生於半島南方小鎮的人,在大馬政府那種國家再有錢也不投資醫療的奇怪政策下,大病只好往首都吉隆坡送(或其他鄉鎮貴族等級收費的私人醫院),沒醫活運屍返鄉對一般人來說又是一大筆負擔。我自己最近也聽說了一個幾乎相同的運屍返鄉的真實故事(甚至比龔的小說還真實,因為〈後記〉告訴我們,真實情況與小說有異)。雖然作者無意經營成問題小說,但故事本身就已是個準問題小說了。
然而這篇小說在策略上有一處頗令人困惑:為什麼把敘事者的年齡設定在十五歲(「十五歲了,即使不說,他也知道很多了」)?這樣的設定或許有利於安放性啟蒙(把玩旅館裡取得的保險套、對「觀光」的期待,作為轉喻,那佔了不少篇幅),以及省略大量繁瑣的與醫院交涉的細節,可是那主人公對母親的亡逝也未免冷漠得太不近人情了。那少年對母親沒有回憶。這在技術上可能是個問題。我們不知道他母親死時幾歲。因為小說沒有提供特定的細節,我們只能依一般狀況去推算。一般來說,十五歲的孩子的母親,年齡並不會太大(除非是老年得子,但那需要提供特定細節)也不會太年輕(除非未成年就生孩子,那也要細節說明或暗示),三十五到五十五之間是合理的推估。換言之,應該是個相當年輕的母親。如果是那樣,小說中的父子的反應就更顯得不近人情了。如果年紀大,久病,死亡是一種解脫,平靜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中年崩逝,除非關係惡劣,是很難不發出「天問」的。
也許是個外加的視點讓小說世界整體變得淡漠。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參照〈後記〉(別忘了那也是敘事),可以看到本事(fabula)和情節(plot)之間的距離。小說主人公的年歲大概是作者的一半,逝者的真實年齡應該都過六十了(除非他是長子),作者本人看待至親之死會比少年平靜得多。而那少年,像是個從小就離家的孩子。作者在調整孩子的年齡時,是不是忘了也要調校那對父母的年齡,以致讓他們看起來不致過於蒼老?處在這本事與情節之間的時差,或許也正是作者念茲在茲的卵生與胎生的差別。但由於喪親是作者強加給那少年的,難怪他無動於衷。卵生年代大抵是幸福時光,時有發現的期待與興奮。縱使那過程中有微小的傷害。
標誌著作品走向成年的第三輯的故事,無一例外的傳達出身在首都吉隆坡強烈的異鄉之感。
該輯另一篇佳作〈無限寂靜的時光〉,都市下層中產階級的男主人公,生活原本該朝向擁有妻子、孩子、房子的幸福的方向。但敘事卻在途中逆轉:無緣的孩子、沉睡的妻子、崩毀的房子,甚至整座城市也好似被蛀空了似的。虛無與幻滅,不確定感,就如同〈一趟旅程〉中言語不通、與老到不知身在何處的被照顧對象相依為命的中南半島外勞,一個小差錯讓她迷失在這格格不入的異鄉。這些題材都是這十多年大馬經濟成長後帶來的一些新的現實:中產階級崛起,國家大量引進外勞外傭,最粗重最辛苦的工作幾乎全由外勞代勞,「麻煩」的老人交給外傭--這和二十多年來的台灣幾乎一樣。儘管作者說他只對日常細節有興趣,然而當生活的結構已發生了鉅變,個體無法再沉湎於個人的內在世界(包括那年少時光),縱使不甘願,那現實還是強悍的闖進敘事裡了。
這很可能是大馬本土作者能大大發揮的領域,尤其在吉隆坡,大馬的歷史往往就在大街上日常的上演。遊行抗爭、通膨、交通打結、環境污染、城市犯罪……。
此刻的寂寞不再是遊戲,而是實存本身,那往往是「無限寂靜的時光」。
作者沒直白的告訴我們的是,「卵生年代」是屬於遙遠的南方故鄉的。然而那故鄉,早已是他鄉了。題目執著於卵生論,或許是種鴨嘴獸似的自傷。牠們原即是地球上最孤獨的物種。《維基百科》:「這是第五種單孔目哺乳動物——單孔目是唯一的產卵哺乳動物,並不是藉由分娩而是下蛋的方式產出下一代。由發現相關物種的化石紀錄知道,牠是其屬(ornithorhynchus)唯一的活代表。」
2012/11/18埔里
推薦序二
抵達之謎∕駱以軍
我想像著這個畫面:二十六、七歲吧(或其中某幾位更年輕)的錦樹、啟章、哲生、國峻、邱妙津、賴香吟,或是黃啟泰、成英姝……這些人,圍坐著一張U形桌,時光的細碎塌毀或因懷念感傷的防腐(或懷舊照片化的療癒),使在那般狀態的我們輕鬆一點,友愛一點,認命一點,又那麼憂悒或非把自己的鐘錶內部機械翻出來重組成一個「不存在的物種」不可……
我想像著在我們(年輕的我們)圍坐一圈的中央,坐著一位更年輕的小說家。我們或許迷惑;或許被某些像蜻蜓點水留下的終於淡去的波紋,或以為仍然持續在揮翅的白鳥,被這些神祕的波赫士詭戲激起童心;或更專注些側頭思索年輕時只因直覺而撬開,後又遺忘,走開的「一整間的玻璃器皿店」。我們裡頭可能比較不那麼害羞的(譬如我),會興味地問:「欸他是誰啊?」
卵生少年。安卓珍尼。寂寞的遊戲。度外。烏暗暝。鬼的狂歡。霧中風景……
很奇異的心情。像卵殼中不會孵化成為成人的,蜷縮成一團、張口閉眼的少年。像複眼所精微描出的一個在演化中是截斷孤立於歷史進程之外的,多餘出來的「微物之神」,像疾病一般的,讓人想尖叫的感覺突蕾與觸鬚(某部分其實或有一支遺傳源頭是川端為摹本的「新感覺派」)。更孤立,更將某種「詞的河流」中原本只是閃瞬即逝的某張《銀翼殺手》那樣的曝閃底片,將之延展,如造夢術,將之像拿微形鑷子用放大鏡而在一極精微宇宙中,栩栩如生搭建的,那像雪景球裡的、易碎的、一個粗手粗腳即全景塌毀的,「箱裡的造景」。
練習消失。一個什麼都故障、失重的密室。什麼都沒發生的,少年暫宿的旅館。葬狗。畫夢。殘光碎影的小學校園和一隻野貓的對峙。父子載過亡母屍體駕破車在陌生之城裡迷路,阿基里斯追龜論那樣的倒走並微分(因之有一種怪誕的喜劇性)。這位母親殤亡於這座拒絕之城的依偎和陪伴(這篇的怪異感,讓我想到童偉格的「死者們的家族旅行」)。
萬輝的這組短篇,我一路讀得從背脊、後頸到耳根起雞皮疙瘩、乃至讀到〈遠方的巨塔〉,終於淚流滿面。我知道在小說技藝本身,或是放置於馬華(旅台)的小說語言的「現代主義實驗並實踐」,有其不斷換焦、不斷累聚的身世(身分)重影,在那些失語少年穿越死蔭之谷的這些過於潔淨白光,過於植物性將自己的性啟蒙、自己的父、自己的母、自己的妻、自己的城、自己的逝水年華……全「駱駝穿針孔」地流淌過那白河夜船般的換日線,它們有其在小說物種演化,在龐大紛雜的雜語(或「南方」)的記憶體攜帶壓力(或和這種壓力恰巧逆反的「消失」的詫異)。萬輝的這組「卵生」隱喻、過於喧囂的孤獨,將暴亂的哭泣與耳語定格成一個內向、自封、破碎(且湯汁迸流)之前的神經質單薄……必有其閱讀維度和景框必須再疊焦再覆蓋的,那沉靜與柔和後面被封印的恐怖暴力。它們並不是我懷念的那個小說世代,在台灣某一懸浮截面的年輕黃金小說家們之「再一次」。一顆掉落在時間差之外的,孤本的行星。
當我這樣自傷懷念地,出現了像電影《啟動原始碼》那不斷復返、強迫症式被送回那列全部人已被爆炸、死去,不存在的「八分鐘」,那因為不再被放進時間流,而終於理解它只是一個上下括弧間的封閉「靜置劇場(純真博物館?)」的擺設、裝置,或CSI式的找出第一次瀏覽疏忽的,錯漏的,細節與細節,線索與其背後之隱喻,或遺憾當時未曾說出的話,未曾堅持的美德與正當,未曾珍惜的那一切發出熠熠光輝的美麗人兒或事物……事實上,所謂「在一輛疾駛中的列車的,滅絕前的八分鐘」,二十多歲時的,黃錦樹曾命名為「內向世代」的,那一個恰巧像撞球某一切角斜擦清脆撞開的,絨布桌檯上的短篇小說群景觀(或所謂「霧中風景」),我們或有各自背後差異更大的身世設定(與亂數),但在某一個時期,如夢境殘影或始終未受精的孤卵,也許是這幾個人腦中被永遠存檔(非常幸運)的,因為當時被封印了,即使遺忘初衷,仍被微物之神騰出無比清晰現場的「八分鐘」。有一種感慨、虛無情懷是,在小說探索、漂流(或對西方二十世紀龐大小說週期表的摹寫和反思,挪藉以「觀看」,反省華人完全不同記憶印痕的離散命運,巴別塔的各自的歷史激流亂石灘),其實,至少我,回不去,或徹底失去了那個時期,那樣如精微模型撬開一微觀、易碎、少年純潔感性的對短篇小說的器質性,神經質的精密控制了。這在「再一次」,「再二次」,第五次,第六次的「重返」、「重建」、「重描圖」、「重修補鑲綴那馬賽克式的卵形小彩圓石」……這樣的小說技藝之執念,它們已形成龔萬輝自我獨一無二的風格宇宙了。它不是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歧路花園」;它或應可視為對華文其他物種而言是「未來學」的馬華小說的其中一支演化論可能--不論它可能撬開這卵生少年的蛛巢小徑,或林中路,或匯聚進他強大前輩們的抵達之謎。
祝福萬輝這本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