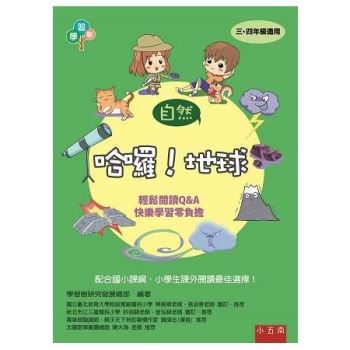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 出版隔年,旋即獲得普利茲小說獎!
★ 與童妮.莫里森《寵兒》、唐.德里羅《白噪音》、約翰.厄普戴克《兔子四部曲》等名家作品一同入圍《紐約時報》「二十五年來最好的一部美國小說」。
★ 與《追風箏的孩子》、《哈利波特》、《少年Pi的奇幻漂流》同列英國《衛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書」!
一九八○年出版,如今在美銷售已逾兩百萬本,並有18種語言翻譯。
當世上有真正的天才出現,你可以據此跡象辨認:
所有的笨蛋,都結成了聯盟與他為敵!
美國文壇最重大的遺珠!
問世後即瘋狂暢銷,並榮獲普利茲小說獎!
☆與《追風箏的孩子》《魔戒》《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同列英國衛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書」!
☆華克.波西(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影迷》作者)撰序推薦!
☆《笨蛋聯盟》與童妮.摩里森《寵兒》,唐.德里羅《白噪音》,
約翰.厄普戴克《兔子四部曲》等名家作品同入選為《紐約時報》
「二十五年來最好的美國小說」!
宇文正(作家,《聯合報》副刊主編),南方朔(知名評論家),郝譽翔(作家,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高翊峰(小說家,FHM總編輯),馮品佳(交大外文系特聘教授),黃崇凱(小說家),賴軍維(宜蘭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按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一致熱烈推薦!★
「我老是找不到工作,顯然我欠缺了當今僱主所尋求的某種變態特質。」
他深信自己是救世主,但他也是個自視甚高的憤青。他學歷傲人,卻長期失業,是個宅男,甚至是個媽寶!只要不順心,他就打嗝脹氣。他的女友深信他最大的問題在於逃避性愛,屢屢來信相勸,總惹得他勃然大怒。
在他令人發噱的外在之下,卻對世界懷抱極其純粹的理想,甚至時不時想來場社會改革。而對他百般忍讓的母親,在認識了新男友之後,一天比一天厭倦這個極端脫離現實的兒子,決定來一次大行動,徹底翻轉她與兒子的人生……
《笨蛋聯盟》是約翰.甘迺迪.涂爾的代表作,也是美國文壇唯一一部在作者過世後才獲得普立茲獎的小說。涂爾生前寫作此書可謂嘔心瀝血,卻始終乏人問津,終抑鬱而逝;之後,其母為此書四處奔走,尋覓知音,終在十一年後獲出版社青睞,出版後,它跌破眾人眼鏡瘋狂暢銷,並獲得普立茲小說大獎。涂爾以插科打諢的反諷手法,透過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角色,折射出現代社會的種種不公不義,與個人理想的失落。在他筆下,我們看到現代人的喧譁激情、笑罵悲喜;看到他人的身影,似也見到自我存在的無奈。
作者簡介:
約翰.甘迺迪.涂爾(John Kennedy Toole, 1937-1969)
約翰.甘迺迪.涂爾出生於紐奧良一個中產家庭,自小即是母親賽爾瑪生命的中心,也是她眼中的天才。一九五八年大學畢業後,涂爾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獎學金,攻讀英語文學碩士。他於一九六一年入伍,兩年後,因官階昇遷而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才開始《笨蛋聯盟》的撰寫。
一九六四年初,他將完成的書稿寄至賽門&舒斯特出版社。由於稿件屬於不請自來之類,自然被打入冷宮。幸好出版社資深編輯的一位助理在無意中拾起這份稿件,讀後頗為激賞,立刻便推薦給自己老闆,亦即編輯──羅伯.葛特里布。葛特里布相當喜歡《笨蛋聯盟》,只是認為此書有個重大問題,亦即缺乏意旨。涂爾因此遵照指示,作過幾次修改,但葛特里布總認為不盡理想。
此後涂爾的精神狀況似乎便開始惡化,而一向愛恨糾葛的母子關係也每況愈下。幾次遭出版社拒絕之後,涂爾與母親為之反目,並自此出現了憂鬱症與偏執狂的癥狀,性格大變。一九六九年一月,涂爾和母親天翻地覆大吵一場,之後便離家出走,音訊全無。兩個月後,一輛白色的雪佛蘭轎車在密西西比州比洛希城外一條小路旁被人發現。駕駛座上衣著整齊、神態安祥的涂爾已經自殺身亡。
一九七四年,涂爾父親離世,他的母親賽爾瑪將稿子寄往八家出版社,全都遭到拒絕。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得到機會,親身出現在名作家華克.波西的辦公室內,硬將書稿塞給了他,並大出意外受到欣賞,於是又轉給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但由於涂爾死時未留遺書,牽扯出眾多親戚爭奪繼承權,賽爾瑪督促律師祭出一切法律武器,才迫使夫家的親戚放棄繼承。
一九八○年,《笨蛋聯盟》終於問世,好評如潮,平裝本與電影版權也相繼售出,銷量迅速竄升。其廣受全國歡迎的程度,不但大出十五年前葛特里布之所料,連原本以為此書或許只具地區性市場潛力的波西也跌破眼鏡。隔年,此書獲頒普利茲小說獎,使涂爾成為史上唯一在身後獲此殊榮的作家。
譯者簡介:
莫與爭
東海國貿系、淡江美研所、Johns Hopkins 社研所。臺北生長,現居美國。
賜教信箱:yuchengmo@yahoo.com。
章節試閱
一頂綠色的獵帽,擠在有如肉氣球的一個頭顱上端。綠色耳罩裡鼓著一雙大耳和久欠修剪的頭髮,和耳中長出的纖細鬃毛,像同時指著兩個方向的轉彎號誌。厚而噘的嘴唇突露在濃密的黑八字鬍下,嘴角下垂,皺出幾重充滿了鄙夷不屑與薯片碎屑的細褶。帽子綠色前沿下的陰影中,是伊內修.J.萊里目空一切藍黃相間的眼睛,正蔑視著其他等候在D.H.侯姆斯百貨公司時鐘下的人,研究著這群人衣著品味低劣的徵狀。伊內修注意到,其中幾套衣服嶄新昂貴的程度,簡直就是對品味與端莊的冒犯。任何新而貴的東西,都只能反映出擁有人欠缺神學與幾何學的修養,連其靈魂也能讓人起疑。
伊內修自己卻穿得舒適而合理。獵帽可以防範傷風。寬大的粗呢長褲既耐用又能允許極其自由的行動。褲褶與角落裡藏著一窩窩溫暖陳滯的空氣,令伊內修通體舒泰。花格的絨布襯衫可以取代夾克,暴露在耳罩與衣領間的萊里皮膚則有圍巾護守。不論以任何一種玄奧的神學與幾何學來看,這套衣裝都能合乎標準,而且還暗示出豐富的生命內涵。
以大象一般沉重笨拙的方式,將重心從一側臀部移向另一側時,伊內修在粗呢與絨布底下傳送出一批漣漪起伏、紛紛拍碎在鈕釦與縫邊上的肉浪。這樣換好姿勢之後,他將等候母親所耗費的大段時間做了一番思忖。他基本上是想到了他開始感到的不適。他覺得整個人彷彿都要從那雙腫脹的麂皮沙漠靴裡爆裂出來,而似乎為了證實這事,伊內修還將他高人一等的眼睛投在他的腳上。腳看起來是腫了。他準備向他母親提出這雙鼓脹的靴子作為證據,請她看看她對旁人是如何不知體恤。抬起頭來,他看到太陽已開始在運河街底的密西西比河上沉落。侯姆斯的時鐘說是將近五點。他已開始琢磨著幾個字斟句酌的控訴,要讓他母親為之懺悔,或至少為之困惑。他常得給她點顏色,讓她知道分寸。
她開那部普利茅斯老車帶他來到城中心。她上診所去看關節炎毛病的時候,伊內修就到維爾雷恩店裡給他的小喇叭買了幾份樂譜,給他的魯特琴買了根新弦。然後他逛進了皇家街的廉價遊樂場,去看看裝了什麼新遊戲沒有。他在失望中發現那迷你棒球遊戲機不見了。也許只是送去修理。上回他玩的時候,打擊者動不了,這廉價遊樂場的人雖然恬不知恥,暗示棒球機器是被他自己踢壞的,但爭論半天,管理人總算退還了他的五分鎳幣。
一心掛念著那部迷你棒球機命運如何的伊內修,正神遊在運河街與身邊人群的具體現實之外,也就沒注意到D.H.侯姆斯一根大柱後面那兩隻朝他貪婪注視的眼睛,閃著希望與慾望的悲哀眼睛。
那機器可不可能在紐奧良修?大概吧。不過,也可能得把它送到密爾瓦基或芝加哥,或在伊內修心中總與高效率修理廠與永遠冒著煙的工廠連在一起的哪個城市。伊內修希望那棒球機在運送途中能遭人小心搬放,不讓它那些小球員破損或支解在粗暴的鐵路員工手中,那些一心一意要以托運者的索賠讓鐵路破產,而總有一天會鬧起罷工把個伊利諾中央鐵路公司﹝註:伊利諾中央鐵路(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又名美中幹線(Main Line of Mid -America),主要連接芝加哥與紐奧良兩地,1972年與海灣、莫比爾與俄亥俄鐵路(Gulf, Mobile and Ohio Railroad)合併重組為伊利諾中央海灣鐵路(Illinois Central Gulf Railroad)公司。﹞搞垮的鐵路員工。
正當伊內修思考著小棒球機為人類所帶來的歡樂時,那兩隻悲哀飢渴的眼睛穿過人群向他靠近,像魚雷對準一艘毛茸茸的大油輪。那警察拽住了伊內修的一袋樂譜。
「你有身分證明嗎,先生?」警察用一種盼望伊內修沒有合法身分的聲音說。
「什麼?」伊內修往下看著藍帽上的徽章。「你是誰啊?」
「給我看看你的駕駛執照。」
「我不開車。能不能請你走開?我在等我母親。」
「垂在你袋子外面的是什麼東西?」
「你想會是什麼,笨蛋?是我魯特琴用的弦。」
「什麼琴?」警察稍退半步。「你是本地人?」
「這個城是文明世界裡聲名狼藉的罪惡首都,卻來騷擾我,這是警察局的本分工作嗎?」伊內修對著商店門前人群的上空咆哮。「這個城出名就出在它的滿城賭徒、妓女、暴露狂、反基督徒、酒鬼、男同性戀、癮君子、患戀物癖的、成天手淫的、賣春宮的、騙子、蕩婦、亂丟垃圾的,和女同性戀,都被貪官污吏保護得太安穩了。你要有點時間,我可以試著跟你討論犯罪問題,但可別弄錯對象,來找我的麻煩。」
警察抓住伊內修的臂膀,帽子上就被樂譜敲了一記。垂吊的弦線正抽在他耳朵上。
「喂,」那警察說。
「找打!」伊內修喊道,他注意到一群顧客起了興趣,開始聚攏成圈。
D.H.侯姆斯店裡,萊里太太正將她母性的胸部壓在糕點部那一玻璃櫃的椰蓉酥上。她用一根因為常年洗刷兒子巨大泛黃的內褲而粗糙不堪的手指,敲在玻璃櫃上,吸引售貨小姐的注意。
「噢,依湼絲小姐,」萊里太太以那種在紐澤西以南只有紐奧良(墨西哥灣旁的霍博肯)聽得到的口音﹝註:這就是紐奧良第九區(Ninth Ward)、愛爾蘭渠道(Irish Channel ──「渠道」此名的來源,一說因為此區是愛爾蘭移民源源來 到的渠道,一說因為此區街道每逢下雨便成渠道)、中城區(Mid- City)等地愛爾蘭、德國後裔居民與紐約、紐澤西某些地區口音相 似的「崖特方言」(Yat dialect)。方言中慣用的問候語,不是一般常用的「你好嗎?」(How are you?),而是「你在哪?」(Where are you at?),發音則如「Where y'at?」。「崖特」一名,即由此而來。﹞說。「在這裡,寶貝。」
「嘿,最近怎樣?」依湼絲小姐問。「好不好,親愛的?」
「不大好,」萊里太太據實回答。
「天可憐見。」依湼絲小姐隔著玻璃櫃傾身過來,忘了她的蛋糕。「我也不大好。是我的腳。」
「老天,我還巴不得有你的運氣呢。我是手肘生了關節炎。」
「噢,怎麼會!」依湼絲小姐帶著如假包換的同情說。「我可憐的老爸爸也有那毛病。我們都讓他在滾燙的熱浴缸裡躺著。」
「我兒子成天泡在我們家浴缸裡。我現在連自己的浴室都很難進了。」
「我以為他結了婚,寶貝。」
「伊內修?哎嗨嗨,」萊里太太悲傷地說。「親愛的,可不可以給我兩打那個什錦點心?」
「但我以為你跟我說過他結婚了,」依湼絲小姐邊說邊將糕點裝進一個盒子。
「他呀,連對象都還沒有。原來那個小女朋友也飛了。」
「呃,他還有的是時間。」
「也許吧,」萊里太太淡漠地說。「哪,可不可以再給我半打葡萄酒蛋糕?家裡一沒有糕餅,伊內修就要發脾氣。」
「你兒子喜歡糕餅,嗯?」
「噢,老天,我這手肘可疼死人了,」萊里太太回答。
百貨公司門前聚集的人群當中,只見那頂獵帽,那個人圈的綠色圓心正在狂跳。
「我要去跟市長投訴,」伊內修喊道。
「別找人家孩子麻煩,」人群裡有個聲音說。
「去抓波本街跳脫衣舞的,」一名老頭附和。「人家可是好孩子。人家在等他媽。」
「謝謝,」伊內修傲慢地說。「希望大家能為這種駭人聽聞的事作個見證。」
「你跟我來,」警察以逐漸消減的自信對伊內修說。人群開始出現一點暴民的味道。附近也看不到任何交通巡警。「我們到局裡去。」
「一個好孩子居然連在D.H.侯姆斯旁邊等他媽媽都不行,」又是那老頭。「我告訴你們,這城以前可不是這樣的。都是共產黨。」
「你說我是共產黨?」警察邊躲著魯特琴弦的鞭笞,邊問那老頭。「小心我帶你一起走。眼睛最好睜亮點,看看你是叫誰共產黨。」
「你抓不了我,」老頭喊了。「我是紐奧良休閒娛樂部贊助的『金色年代俱樂部』會員。」
「別找老人家麻煩,你這個惡警察,」一個婦人尖聲叫道。「他大概都做爺爺了。」
「我是,」老頭說。「我有六個外孫,全跟著修女上學。可聰明了。」
伊內修從人群頂上望見他母親慢慢踱出百貨公司大廳,手裡像拎著一盒盒水泥似地提著糕點部的產品。
「媽,」他叫。「你來得剛好。我被逮捕了。」
排開人群的萊里太太說:「伊內修!怎麼回事?你幹了什麼?喂,你別跟我孩子動手動腳。」
「我沒碰他,太太,」警察說。「這人是你兒子?」
萊里太太一把扯下伊內修手中那根咻咻有聲的魯特琴弦。
「我當然是她孩子,」伊內修說。「你看不出她有多疼我?」
「她愛自己兒子,」老頭說。
「你想對我可憐的孩子怎樣?」萊里太太問那警察。伊內修用一隻巨掌拍撫著他母親染成紅褐的頭髮。「這個城裡各種貨色的人滿街亂跑,你們倒有工夫跟可憐小孩過不去。等自己媽媽他們也要抓。」
「這顯然是個該讓『公民自由聯盟』﹝註:「公民自由聯盟」全名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簡稱 ACLU),創於1920年,是專為爭取民權的自由派民間組織。﹞來管的案子,」伊內修邊用手掌揉擠他母親下垂的肩膀,邊做出了觀察。「我們得聯絡摩娜.敏可夫,我那失去的戀人。這種事她熟。」
「都是共產黨,」老頭插嘴道。
「他多大年紀了?」警察問萊里太太。
「我今年三十,」伊內修口氣高傲。
「你有工作嗎?」
「伊內修得在家裡幫我,」萊里太太說。她原先的勇氣已經減了一些,手中捲繞著魯特琴弦與蛋糕盒上的繩子。「我患了嚴重的關節炎。」
「有時我會撣撣灰塵,」伊內修告訴警察。「此外,目前我正在寫一個長篇論文,批判我們這個世紀。文字勞動讓我頭昏腦脹的時候,就偶爾去做點乳酪蘸醬。」
「伊內修做的乳酪蘸醬可好吃了。」
「那他真乖,」老頭說。「人家男孩多半都成天野在外頭。」
「你能不能閉上嘴?」警察對老頭說。
「伊內修,」萊里太太用顫抖的聲音問,「你幹了什麼,兒子?」
「其實,媽,我覺得這都是他起的頭。」萊里用他那袋樂譜指著老頭。「我只不過是站在這裡,一邊等你,一邊祈禱醫生能給你點好消息。」
「把那老頭帶走,」萊里太太對警察說。「都是他在搗亂。真可悲,有像他這樣的人走在街上。」
「警察都是共產黨,」老頭說。
「我不是叫你閉嘴了嗎?」警察憤怒地說。
「我每天晚上都要跪下感謝上帝,感謝我們受到的保護。」萊里太太告訴群眾。「沒有警察的話,我們早都沒命了。我們都會倒在床上,脖子給人從耳朵割到耳朵。」
「一點不錯,老妹,」人群裡有個女人回答。
「為警察部隊唸唸玫瑰經,」萊里太太開始對群眾講演。伊內修狂暴地撫摸著她的肩膀,在她耳邊低聲鼓勵。「你會為一個共產黨唸玫瑰經嗎?」
「不!」幾個聲音熱烈地響起。有人推了老頭一把。
「我沒騙你,太太,」老頭喊道。「他想抓你孩子。像在俄國一樣。他們全是共產黨。」
「來,」警察對著老頭說。他粗暴地揪起老頭上裝的後領。
「我的天哪!」伊內修說,一邊看著蒼白瘦小的警察企圖控制那老頭。「你們煩死人了。」
「救命啊!」老頭向群眾哀求。「這是強行接收。這是違反憲法!」
「他瘋了,伊內修,」萊里太太說。「我們趕緊走吧,寶貝。」她轉身對著群眾。「跑啊,各位。說不準他會把我們大家都宰了。我看哪,他才是共產黨。」
「你也用不著演得太過頭,媽,」他們排開四散的人群快步沿著運河街走去的時候,伊內修說。他回頭看見老頭和那羽量級的警察正在百貨公司的鐘下扭成一團。「你能不能慢點?我感覺心臟有點雜音。」
「噢,閉嘴。你以為我感覺如何?我這把年紀實在不該這麼跑的。」
「我想,心臟對任何年紀恐怕都很重要。」
「你心臟沒有毛病。」
「我們再不慢點,就要出毛病了。」往前滾動的時候,伊內修的粗呢褲子在他巨大的臀部四周掀起波浪。「你拿了我的魯特琴弦?」
萊里太太拉著他轉過街角走上波本街,他們開始步向法國區。
「那個警察為什麼會找上你,兒子?」
「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但他恐怕馬上就要追過來了,等他把那個老法西斯制伏之後。」
「你覺得會?」萊里太太緊張地問。
「我猜是會。他一副鐵了心非要抓我不行的樣子。他一定是有什麼配額之類的。我不敢相信他會那麼輕易就把我放過。」
「那多可怕呀!你會上報的,伊內修。多丟人吶!你在等我的時候一定是幹了什麼,伊內修。我對你清楚得很,兒子。」
「別人不說,我在那裡可沒管半點閒事。」伊內修喘著。「拜託。我們得歇一會。我覺得要內出血了。」
「好吧。」萊里太太看看她兒子愈來愈紅的臉,知道他光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會很樂意當場癱倒在她跟前。他以前就幹過這種事。上回她強拉他在禮拜天陪她去做彌撒,他在去教堂的途中就癱過兩次,在聽關於怠惰的講道時又癱了一次,還搖搖晃晃滾出了那排座位,鬧出一場令人臉紅的騷亂。「我們進去坐坐。」
她用一個蛋糕盒將他推進了「歡樂良宵」酒吧的門。他們在滿溢著波本威士忌與菸屁股氣味的黑暗裡,爬上了兩張高腳凳。萊里太太在吧檯上排列她那些蛋糕盒的時候,伊內修張敞著他寬闊的鼻翼說:「老天,媽,一股臭味,我肚子裡開始翻騰了。」
「你想回到街上?你想讓警察抓進去?」
伊內修沒有答腔。他大聲聞嗅,做起怪臉。一直在觀察這兩人的酒保從陰影底下用揶揄的口吻問道,「要些什麼?」
「我要杯咖啡,」伊內修大聲大氣地說。「菊苣咖啡﹝將菊苣(chicory,亦即endive,學名cichorium)根部烘烤磨碎與咖啡豆相混所製的咖啡。紐奧良法國區的百年老店Café du Monde即以其chicory coffee加牛奶的café au lait名聞遐邇。﹞加熱牛奶。」
「只有即溶咖啡,」酒保說。
「我沒辦法喝那種,」伊內修對他母親說。「太低級了。」
「呃,叫杯啤酒吧,伊內修。喝不死你的。」
「我有可能脹氣。」
「我要瓶『迪克西45』,」萊里太太對酒保說。
「這位先生呢?」酒保用一種深沉做作的聲音問。「喜歡喝什麼?」
「也給他一瓶『迪克西45』。」
「我有可能不喝,」伊內修在酒保去開啤酒的時候說。
「我們不能在這裡白坐,伊內修。」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能。這裡的客人就只有我們。有我們在,他們該高興還來不及。」
「他們這裡晚上有跳脫衣舞的,呵?」萊里太太用肩膀推推兒子。
「我猜是有,」伊內修冷冷地說。他看起來十分痛苦。「我們本來可以到別家去的。我怕的是,弄了半天警察還會馬上來這裡檢查。」他鼻子呼嚕有聲,清了清喉嚨。「謝天謝地有我的鬍子濾掉一點臭味。我的嗅覺器官已經送出了求救信號。」
經過一段似乎相當長的時間,陰影下的某處不斷傳來玻璃杯叮叮噹噹和冰櫃門乒乒乓乓的聲響,酒保終於再度出現,將啤酒放在他們面前,有點想將伊內修的啤酒打翻在他大腿上的意思。萊里一家所受到的,正是「歡樂良宵」最差的服務,專為不受歡迎的顧客所提供的待遇。
「你們該不會有冰的『堅果博士』﹝堅果博士(Dr. Nut)是紐奧良 World Bottling Company 於1920年代推出的杏仁汽水,行銷一直不能廣及全國,現已消失。﹞吧,有嗎?」伊內修問。
「沒有。」
「我兒子愛喝『堅果博士』,」萊里太太解釋。「我得整箱整箱的買。有時候他坐下來一口氣就是兩三瓶『堅果博士』。」
「我相信這位並不特別感興趣,」伊內修說。
「要不要把帽子脫了?」酒保問。
「不,不脫!」伊內修雷聲隆隆。「這裡冷颼颼的。」
「悉聽尊便,」酒保說完就飄進了吧檯另一端的陰影之中。
「真是!」
「別氣了,」他母親說。
伊內修撩起靠他母親那側的耳罩。
「哪,我把這個翻起來,你就不用大聲嚷嚷了。你那個手肘或是什麼部位,醫生是怎麼說的?」
「說是需要按摩。」
「你最好別指望叫我按摩。你知道我摸到別人會有什麼感覺。」
「他叫我儘量少待在冷的地方。」
「我要能開車的話,應該可以多幫著你點,我想。」
「嗷,沒有關係,親愛的。」
「其實,就算是坐在車裡,我也受不了。當然最糟的就是坐在『灰狗觀景長途巴士』的上層。那麼高。你記不記得我坐那車去巴頓魯治的那次?我吐了好幾回。司機還得把巴士停在沼澤當中什麼地方,讓我下車走兩圈。其他乘客都有點生氣。他們的腸胃大概都是鐵打的,能坐那種可怕的機器。離開紐奧良也讓我相當恐懼。一出城市的地界,就進入了黑暗的核心、真正的荒原。」
「我記得,伊內修,」萊里太太心不在焉地說,一邊大口喝啤酒。「你到家時病得一塌糊塗。」
「我那時已經好多了。最糟的是我剛到巴頓魯治的時候。想到自己手上是張雙程車票,還得坐這巴士回去。」
「你告訴過我,寶貝。」
「回紐奧良的計程車花了我四十塊,但至少我在計程車上沒暈得那麼厲害,雖然也起過幾次作嘔的感覺。我叫那司機開得特別慢。他算是倒了楣。州警兩次把他攔下,都是因為車速不到公路的最低速限。他們第三次叫他停下的時候,把他客車司機的執照也沒收了。你曉得,其實他們一路在用雷達監視我們。」
萊里太太的注意力擺盪在她兒子與啤酒之間。這個故事她已經聽了三年。
「當然,」伊內修錯把他母親恍惚的表情當成了興致,繼續說道,「我這輩子離開紐奧良也就只有那麼一次。我想也許是缺少了一個方向感的中心,才會讓我那麼難受。在巴士裡全速前進,就像是被拋進了無底深淵。我們離開沼澤地區進入巴頓魯治附近那一帶起伏的丘陵時,我還開始擔心會有什麼鄉巴佬農民朝巴士丟炸彈呢﹝此處似乎隱喻1961年母親節,一輛滿載「自由行者」(Freedom Riders)民權運動人員的灰狗巴士,在阿拉巴馬州安尼斯頓(Anniston, Alabama)城外遭到「三K黨」汽油彈攻擊的事件。當時巴士起火之後,攻擊者原欲堵住車門,企圖燒死全車民權工作者。幸好發生爆炸,暴徒方鳥獸而散。﹞。他們喜歡攻擊汽車,因為那是進步的象徵,我猜。」
「呃,我很高興你沒接下那個工作,」萊里太太把猜當成了她的提示,不假思索地說。
「我沒辦法接下那個工作。我一見到『中世紀文化學系』的主任,兩手就開始長滿了小白疹子。他那個人根本沒有靈魂。還提到我不打領帶,對我的短夾克冷嘲熱諷。這樣一個淺陋的人居然敢如此厚顏無恥,我是啞口無言了。我真正依戀的物質享受沒有幾個,那件短夾克就是其中之一,要是找到了偷它的那個瘋子,我一定把他告到底。」
萊里太太眼裡再度出現了那件可怕的、咖啡污漬斑斑點點的、她一直暗中希望連同伊內修最愛的其他幾件衣物一併捐給「美國義勇軍」﹝美國義勇軍(Volunteers of America)是成立於1896年的宗教性慈善組織。﹞的短夾克。
一頂綠色的獵帽,擠在有如肉氣球的一個頭顱上端。綠色耳罩裡鼓著一雙大耳和久欠修剪的頭髮,和耳中長出的纖細鬃毛,像同時指著兩個方向的轉彎號誌。厚而噘的嘴唇突露在濃密的黑八字鬍下,嘴角下垂,皺出幾重充滿了鄙夷不屑與薯片碎屑的細褶。帽子綠色前沿下的陰影中,是伊內修.J.萊里目空一切藍黃相間的眼睛,正蔑視著其他等候在D.H.侯姆斯百貨公司時鐘下的人,研究著這群人衣著品味低劣的徵狀。伊內修注意到,其中幾套衣服嶄新昂貴的程度,簡直就是對品味與端莊的冒犯。任何新而貴的東西,都只能反映出擁有人欠缺神學與幾何學的修養,...
作者序
喧囂而瘋狂的征途
華克.波西
介紹這本我在第三度重讀時竟比首次過目還要震撼的小說,最好的方法,或許就是談談我和它最初的接觸。一九七六年,我在羅耀拉執教時,開始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電話。她的提議相當荒謬。不是她寫了兩章小說,想進我的班;而是她過世的兒子在六○年代早期寫過整本小說,大部頭的小說,想請我讀讀。為什麼要讀?我問她。因為這是部絕佳的小說,她答。
我多年以來,已經練就一身功夫,專能將不想幹的事推個乾淨。而如果世上還有我不想幹的事,這就絕對是了:要應付一個已故小說家的母親不說,最可怕的是得去讀她口稱絕佳的稿件,並且我還發現,那是個嚴重塗污幾至無法閱讀的複寫本。
但這位女士很能鍥而不捨,幾經周折她已現身在我辦公室中,向我遞來一份厚重的稿件。推脫是不可能了,只剩下一個希望,也就是我暫且讀它幾頁,而這幾頁不忍卒讀的程度,便足以讓我在問心無愧中即時打住。我通常都能如此。其實光讀第一段多半也就夠了。怕只怕這本稿件可能還不夠壞,或可能剛剛夠好,教我不得不往下讀。
這回我是讀下去了。還再讀下去。先是暗覺不妙,它沒壞到能讓人撒手的地步,接著感到一絲興趣的激刺,繼而漸趨亢奮,最後是難以置信:怎可能會有如此之妙。在此我得忍住誘惑,將當初那些令我張口咧嘴、放聲大笑、搖頭讚嘆的東西賣個關子。還是由讀者自己去發現的好。
總之,書裡有個伊內修.萊里,在我所知的文學裡找不到任何前身:邋遢透頂,身兼瘋狂的奧勒佛.哈台、肥胖的堂.吉訶德,與頑固的多瑪斯.阿奎那,正在對整個現代進行殊死的反抗,穿著絨布睡衣,躺在紐奧良市君士坦丁堡街一間屋後的臥室裡,趁著排山倒海襲來的脹氣與打嗝之間空檔,將成打的「大酋長」拍紙簿填滿了激烈的批判。
他母親認為他該去上班。他也做過一連串不同的事。每個職位雖都迅速惡化成瘋狂的探險與十足的災難,但也正如堂.吉訶德的經歷,各有其獨特的荒誕邏輯。
他來自布朗士區的女友摩娜.敏可夫,認為他需要性愛。摩娜與伊內修之間的事,大不同於我經驗所及的任何典型愛情故事。
涂爾小說中另一個同樣巧妙的地方,是他筆下的紐奧良特色,它的後街小巷、它的偏僻鄰里、它的奇特口語、它共享特殊文化背景的白人,加上一位黑人。涂爾在這黑人身上達到了幾不可能的境界,將他寫成一個足智多謀極富喜劇性的角色,卻不帶一點「賴司特廝」式白人抹上黑臉唱滑稽戲的調調。
但涂爾最成功的地方,還在於伊內修.萊里本人,在於這個知識分子與理論家,這個無所事事懶作好吃的人。他龐大的自我膨脹,和他對現代種種的放縱無度,乃至包括佛洛伊德、同性戀者、異性戀者、新教徒在內一切人等所作的厲聲譏誚與隻手挑戰,頗能使讀者望之卻步。不妨想像一個開始抽起大麻的阿奎那,搬到了紐奧良,從那裡展開瘋狂的征途,穿過重重沼澤,殺向巴頓魯治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而在腸胃大出問題,不得不坐在男教職員廁所裡的時候,被人偷去了他的短夾克。他的幽門瓣膜不時會對現代世界之缺乏「正確的幾何學與神學」產生反應,自動關閉。
我不太敢用喜劇一詞──雖然它確是齣喜劇──因為其中暗示的只是一本引人發噱的書,而這部小說卻遠不止此。說它是個龐巨喧囂、大如福斯塔夫的鬧劇還比較合適。說它是「commedia」更貼切點。
而它也悲哀。我們始終不太確定這悲哀到底從何而來,是藏在伊內修巨大氣態的憤怒與那些瘋狂冒險核心當中的悲劇,還是伴隨著本書的悲劇。
本書的悲劇就是作者的悲劇,是三十一歲的他在一九六九年的自殺。另一個悲劇,是我們橫遭剝奪的整批作品。
約翰.甘迺迪.涂爾今天不能安然在世繼續寫作,是個天大的遺憾。但他不能,而我們除了竭盡全力至少要將這部巨大嘈雜的悲喜劇呈獻給廣大讀者之外,也別無可求了。
喧囂而瘋狂的征途
華克.波西
介紹這本我在第三度重讀時竟比首次過目還要震撼的小說,最好的方法,或許就是談談我和它最初的接觸。一九七六年,我在羅耀拉執教時,開始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電話。她的提議相當荒謬。不是她寫了兩章小說,想進我的班;而是她過世的兒子在六○年代早期寫過整本小說,大部頭的小說,想請我讀讀。為什麼要讀?我問她。因為這是部絕佳的小說,她答。
我多年以來,已經練就一身功夫,專能將不想幹的事推個乾淨。而如果世上還有我不想幹的事,這就絕對是了:要應付一個已故小說家的母親不說,最可怕的是得去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