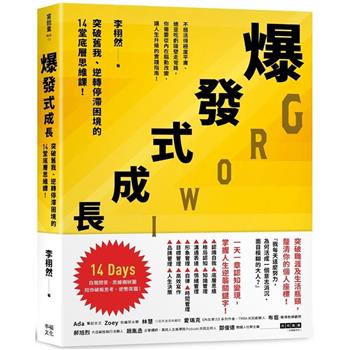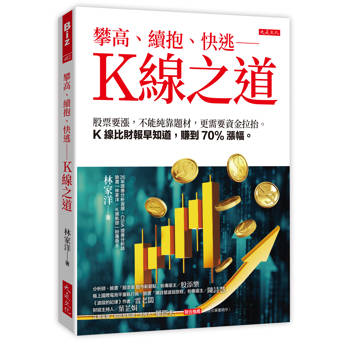我只是想要有個人來愛,
哪怕她沒有手沒有腳,全身佈滿鱗片……
史上唯一兩度獲頒法國「龔固爾文學大獎」的傳奇作家!
《雨傘默默》作者轉捩代表作,
失落四十年的原始結尾首次出版!
◎已搬上大銀幕,由法國電影「凱撒獎」得主、《悲慘世界》男星尚.卡爾梅主演!
我三十七歲,我一個人住。
我養了一條蟒蛇。
我喚牠「大親親」,因為當我倆在床上時,牠總是緊緊纏繞著我。從來沒有人像牠這樣親密地擁抱我。牠完全依賴我,我是牠的一切,離開我牠就活不了。
可是此刻,我面臨了人生最困難的抉擇。大親親得吃肉,然而眼前這隻衝著我手心嗅聞的小白老鼠,是如此純潔柔弱,我實在不忍心把牠送入那漲滿欲望的大口!
生活,該如何繼續下去?
《大親親》是羅曼.加里以化名撰寫的第一本書,當時他已是國際知名的文壇大師,卻刻意隱身幕後,甚至順從編輯的建議而大幅修改結尾。此書推出後佳評如潮,然而作家本人始終盼望著有一天,「原始的結尾」能夠如實出版。終於在四十年後,繁體中文版首次完整收錄了此篇夢幻結尾,也讓讀者們得以更貼近這位傳奇作家不朽的靈魂。
本書特色
★史上唯一兩度獲頒法國「龔固爾文學大獎」的傳奇作家!
★《雨傘默默》作者轉捩代表作,失落四十年的原始結尾首次出版!
★已搬上大銀幕,由法國電影「凱撒獎」得主、《悲慘世界》男星尚.卡爾梅主演!
★羅曼.加里創作過程中最波折的一本作品,讓他來回重寫了二十次!
★法國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四顆半星盛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