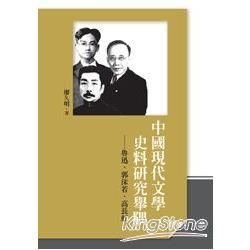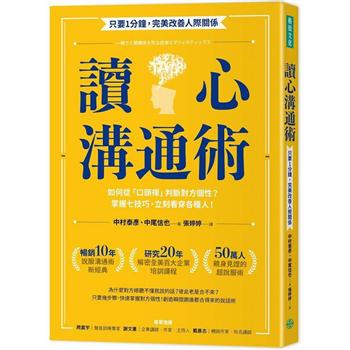魯迅的《朝花夕拾》、《野草》「開創了現代散文的兩個創作潮流與傳統,即『閒話風』的散文與『獨語體』的散文」 ,這種說法出現在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由於該教材被廣泛使用,所以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21世紀仍然有人將它寫進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中:「《野草》和《朝花夕拾》以『獨語體』和『閒談體』兩種體式,超越了五四時期啟蒙式的散文,開創了現代漢語散文的兩大創作潮流,對現代漢語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將魯迅這兩部作品與高長虹相關作品比較一下便會發現,該說法值得商榷。
一、魯迅《野草》與高長虹《幻想與做夢》比較
首先比較一下內容和風格。人們對魯迅的《野草》已經非常熟悉,故筆者僅簡單介紹一下人們對它的評價而不介紹其具體內容:「『獨語』是以藝術的精心創造為其存在前提的,它要求徹底擺脫傳統的寫實的摹寫,最大限度地發揮創造者的藝術想像力,借助於聯想、象徵、變形……,以及神話、傳說、傳統意象……,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藝術世界。於是,在《野草》裏,魯迅的筆下,湧出了夢的朦朧、沉重與奇詭,鬼魂的陰森與神秘;奇幻的場景,荒誕的情節;不可確定的模糊意念,難以理喻的反常感覺;瑰麗、冷豔的色彩,奇突的想像,濃郁的詩情……。」
現在逐一介紹高長虹的《幻想與做夢》。《從地獄到天堂》描寫了一個夢境:「在長久的孤獨的奮鬥之後,我終於失敗了」,在「向沒有人跡的地方逃走」過程中,遇到了「銜著毒針的怒駡,放著冷箭的嘲笑,迸著暴雷的驚喊」,最後「倒在一塊略為平滑的岩石上睡了,甜美地睡著──一直到我醒來的時候」。 《兩種武器》通過與朋友的對話,表達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我本來便決定十年之內要造兩種武器:理想的大炮和一支手槍,如大炮造不成時,我便用手槍毀滅了我這個沒能力的廢物。」 《親愛的》用詩一般的語言記錄了一個美麗的夢:在丁香樹下看見了夢寐以求的意中人──「她的顏色,像蛋黃那樣的黃,又像萍草那樣的綠,卻又像水銀那樣的白」,「我還沒有趕得及辨清楚那是樹影搖動的時候,我已看見你伏在我的懷中。我們一句話都沒有說,但是,一切宇宙間所能夠有的甜蜜的話,都在我們倆的心兒裏來往地迸流著。」 《我是很幸福的》為「我」在「一個女子的心裏攪起一些波浪」而感到「幸福」:「她的心的確是在很熬燙地懊惱著,她在想著關於我的過去的錯誤的認識。一個男子,能引起女子對於他的注意,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奇跡,尤其在孤獨的傲慢的我。」 《美人和英雄》寫了一個夢,夢見「我」和小學同學在服侍一個「面目可憎」的主人和一個「漂亮」的女子時,女子突然倒在地上,「變成一條蚰蜒」,最後「只剩下一灘水的痕跡」。於是,「我」與同學立即一起捉拿這主人,卻讓他跑掉了。 《得到她的消息之後》寫得到她的消息之後,「連夢都不能夠幫助我了」:「我」竟然夢見「她被做了妓女」,「又像變成一個囚犯」。 《母雞的壯史》寫「我」已沒有興趣研究人類的歷史,故轉而研究動物的歷史。文章讚美母雞,認為由於母雞比公雞的境遇更慘,所以,「雞的革命運動,時常是由他們中的女性所發起的」。 《我的死的幾種推測》寫了「我」推測的十種死法。 《生命在什麼地方》寫「我」曾在家庭、朋友處尋找「生命」,結果卻是「女子,人類,都給我以同樣的拒絕」。最後,作者終於在偶然中找到了「生命」:在一塊很小的石頭下,「一隻快死的小蟲」,仍然在頑強地鳴叫著。 《婦女的三部曲》寫婦女的命運:結婚前人見人愛,結婚後滿足於自己嫁給了一個好男人,死後被烏鴉所追逐。 《一個沒要緊的問題》寫「我」與「一個鄉村的少婦」生活的情景,文中的少婦是一個沒有主見的女人。 《我和鬼的問答》通過與鬼的問答,寫「我」願做乞丐──因「乞丐是最節儉的掠奪者」、願愛妓女──因妓女「永遠不能夠得到愛情」,願與鬼作朋友──鬼卻哭著跑開了。 《一封長信》寫自己在閱讀三個月前所寫長信時已經無法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安慰》寫小孩阿寶在外面受了欺侮,本希望回家後從媽媽那兒得到安慰,沒想到媽媽也正希望從阿寶這兒得到安慰。 《迷離》寫夢中「我」與一個醜陋、矮小的女子擁抱,卻被屋外的腳步聲驚開。 《噩夢》寫「我」原以為「闖進了未來的黃金時代」,結果卻是一個「惡夢」:「我在夢中,比醒時,看見了更真實的世界。/在我的夢中,一切都是惡,都是醜,都是虛偽。」
通過以上介紹可以發現,《幻想與做夢》和《野草》確實存在不少相同的地方:它們都描寫了大量夢境、場景都非常奇幻、情節都非常荒誕、想像都非常奇突、詩情都非常濃郁……正因為如此,魯迅與高長虹初次見面時都非常佩服對方的類似作品:「我初次同魯迅見面的時候,我正在老《狂飆》週刊上發表《幻想與做夢》,他在《語絲》上發表他的《野草》。他說:『《幻想與做夢》光明多了!』但我以為《野草》是深刻。」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舉隅-魯迅、郭沫若、高長虹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2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60 |
中文書 |
$ 361 |
華文文學研究 |
$ 369 |
文學史 |
$ 36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舉隅-魯迅、郭沫若、高長虹
總之,寫文學史確實應該抓大放小,否則便是一種「『博覽旁搜』,以量取勝」。不過,寫文學史應該先研究再篩選,而不應該先篩選再研究,只有在對所有對象進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才能知道哪些該抓、哪些該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為不瞭解而放棄那些本該抓住的內容,卻讓那些本該放棄的內容濫竽其間。並且,結構主義告訴我們,「現實的本質並不單獨地存在於某種時空之中,而總是表現於此物與它物間的關係之中。」就是為了研究重要作家和重大現象,也應該將其與相關作家和現象聯繫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家的重要性和重大現象的意義所在。這一切,都離不開史料工作。
——廖久明
作者簡介:
廖久明(1966-):文學博士,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樂山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工作。
章節試閱
魯迅的《朝花夕拾》、《野草》「開創了現代散文的兩個創作潮流與傳統,即『閒話風』的散文與『獨語體』的散文」 ,這種說法出現在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由於該教材被廣泛使用,所以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21世紀仍然有人將它寫進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中:「《野草》和《朝花夕拾》以『獨語體』和『閒談體』兩種體式,超越了五四時期啟蒙式的散文,開創了現代漢語散文的兩大創作潮流,對現代漢語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將魯迅這兩部作品與高長虹相關作品比較一下便會發現,該說法值得商...
»看全部
作者序
就中國現代作家而言,《魯迅全集》至少應該是最全的全集之一。但是,出於寫作《一群被驚醒的人──狂飆社研究》的需要,筆者在通讀《莽原》週刊和半月刊時竟然發現有近20則廣告未收入2005年版《魯迅全集》(不包括12則《正誤》)。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收錄了部分廣告、劉運峰編輯的《魯迅全集補遺》收錄了30則廣告的情況下,竟然在魯迅主編的、著名而常見的《莽原》上發現這麼多魯迅佚文,筆者不能不感到驚訝。筆者由此想到,由於魯迅一生辦了不少刊物,在魯迅主辦的其他刊物上應該還能發現魯迅佚文。由此可知,哪怕是「尚可...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廖久明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2-10-22 ISBN/ISSN:978986591508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