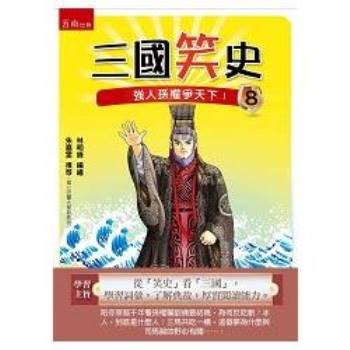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我參加過抗日、國共內戰、韓戰三場戰役。
戰亂時沒被打死,
饑荒時沒被餓死,
一系列政治運動沒被整死。」
本書為書法家林鵬先生回憶革命戰爭時代的人和事。
藉回憶故人從歷當年戰爭的實況,並憶及在文革時曾被劃為右派分子之經過和省思。
本書特色
作者回憶過去參加革命戰爭時的種種經過,雖然在文革時劃為右派分子,卻不放棄自己更加努力的閱讀書籍,最後成為一位知名的書法家。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社會人物 |
$ 405 |
毛澤東及中國近/當代人物 |
$ 405 |
社會人文 |
$ 405 |
歷史 |
電子書 |
$ 450 |
人物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鵬
字翮鳳,號蒙齋、夏屋山等。1928年2月生,河北易縣人。1941年參加工作,1958年轉業至山西。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山西分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創作評審委員會委員。出版著作有《丹崖書論》、《蒙齋讀書記》、《林鵬書法》、《蒙齋印話》及長篇歷史小說《咸陽宮》等。
目錄
序
不能宣傳的抗日英雄-回憶樊金堂
白髮青山兩無言
回憶陳亞夫
英雄失路張學義
馬義之的文昭關
南管頭人
尋訪御射碑記
竇大夫祠觀感
傅山與交山義軍
紫塞雁門
感受陽謀
龍居回憶
常平回憶
童蒙憶零
我所經歷的戰爭
戰壕裡的民謠
荷花的品格
艱難與獨特-回憶王螢
回憶李玉滋
紀念王朝瑞
憶梁寒冰-閒話儒法鬥爭史
記袁毓明-東花園雜記之一
那一年,那一天
我的罪孽(原名:苦菜窪)
康八里章
孤萍浪記
李斯的性格
序幕的尾聲:方其夢也
蒙齋印話
新絳筆贊
金包公傳說
《丹楓閣記》真跡發現始末
涿州行
附錄一 三打紅山包
附錄二 愉快的勞動
序
序
一
林鵬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長者。
打定主意要寫個痛快的文章,一起首竟是這麼一個平庸的句子,不知將來林先生看了會怎樣,此刻我就先覺得彆扭,不是怠慢了林先生,就是怠慢了我自己。
改吧,似乎也不好改。因為林先生確實是我敬重的一位長者。
問題出在,我不是一個能很規矩地敬重某個自己敬重的人的人,他呢,也不是個能很規矩地端著架子等著叫敬重他的人來敬重的長者。
越說越糊塗了,還是說兩件事吧。
林先生是個書法家,這沒說的,毛病出在他以為他靠靈性成了書法家,只要他一指點,再愚鈍的人也能成了書法家。一次在他家裡,前幾年了,現在不會了,他說:石山吶,你只要照我的法子練上兩個星期,就成了書法家了。找兩幅自己喜歡的書法家寫的字,字數不要多,一首七言絕句,一首五言絕句,照著寫,寫熟了,到了哪兒都是這兩幅,別的不管他怎麼求,就是個不寫。時間一長,架子也有了,名氣也有了,不是書法家是什麼?
我心裡直笑,這是教沒文化的官僚的辦法,韓某人怎麼會來這一套。說出的話卻是,林先生吶,這麼一來是成了書法家,且是出自林門,只是你的弟子那麼多,我現在才列於門牆,將來見了你那些弟子,我該叫什麼,叫師兄還是叫師叔?―我還是好好當我的三流作家吧。
林先生一聽,哈哈大笑。此話遂撂過不提。
再一件事,也與寫字有關。他知道我平日是寫字的。一次聊天過後,要走了,問我,要紙嗎?隨手指指地板上堆的宣紙摞子,有一人高,全是別人送的。我說要。他說,你自個拿吧。
將上面的幾令翻了一下,抽出一令我覺得好的,扛起便走。
從老先生家這麼拿東西,只有林先生家敢。我知道,他是真心給,不是客套,他也知道我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不會扭捏。要是別處,先不說會不會這麼說,就是說了,要和不要我是會掂量一下的。一掂量準壞事,―我是個窮到連紙也買不起的人嗎?
下次見了林先生,說起練字,我說,林先生的紙真好,寫起來的感覺就是不一樣。他驚喜地說,是嗎?別人送我的都是好紙。我說,我家裡也有好紙,只是一用好紙寫,總也寫不好。用林先生的紙就不同了,白來的,寫壞了不心疼,心態放鬆,筆下也就有了靈氣。林先生聽了,哈哈大笑,說:「那你以後就隨便拿吧。」
以後他再不提拿紙的事。可我知道,只要我開口要,他還是會給的。
敢隨意說話,敢隨意行事,這就是我敬重林先生的表現。
允許我隨意說話,允許我隨意行事,這就是林先生品德學問之外,更讓我敬重的地方。
雖未能列於門牆,林先生還是把我當弟子看待的。只是我這人在尊師面前,總也沒個正經的時候,比如共同外出赴宴,要上台階了,我會過去攙扶一下,給了別人,這樣的事,做就做了,絕不會說什麼的,我不,一邊攙扶一邊總要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每當此事,林先生總是推開我,去去去。我呢,也只是在這樣的地方表現一下,待到了餐桌上,就只顧自己大快朵頤,絕不會說什麼「有酒食,先生饌」了。
有了這樣的亦師亦友的關係,當領了林先生之命,要為他新近編成的散文集寫序的時候,就會知道,我會怎樣的盡心,要寫成一篇怎樣痛快淋漓的文章了。
還得說是怎樣領命的―與林先生有關的事,沒有一件不是既見情誼又見個性的。
上個月吧,去了林府,剛落座,老先生說他的散文集編起來了,隨即說:「序,你寫吧。這是你鼓動我編的。一萬字,不能少!」
我心裡苦笑,有這麼讓人寫序的嗎,定下了字數不少於一萬。我從沒有寫過這麼長的序。可是―當時就沒有可是,只有現實--就坐在林先生面前,就聽到了林先生的話,能說的話只有一個字,行。
二三十年的交往,林先生從來沒讓我做過力不能及的事,凡是他讓我做的事,我也從沒有撥過林先生的魂兒。真用得上那個俗之又俗的流行語: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其時我正在寫一部書,唯一的軟話是,寬限幾天行不行。
林先生說,也不能太遲。
這不,我的事一撂過手,就緊著看起林先生的散文集子。他老人家做事,從來是大手大腳,像這樣的書稿,要是我,列印上一冊也就行了,他竟用四號字,印了不知多少本,且裝訂得跟真書一樣。看這樣的書稿,簡直是一種享受,不像是在看書,倒像是在批公文似的。
不光看了這本書,還看了先前送我的《丹崖書論》、《平旦札》,連他的書法集也翻了出來。
看林先生的書,一是痛快,越看越痛快,一是敬重,越看越敬重。
二
敬重的根基是佩服。
佩服的根基之一是經歷。
一個中學生考上北大清華,也佩服,佩服的只是單薄的聰明,一個赴緬甸作戰的遠征軍老兵,你只要見了,就只有佩服,不是別的,是豐厚而苦難的經歷。
林先生是有大經歷的人。不知道他的經歷,很難理解他這個人。
要捋清他的經歷,非得編個年表不可。還真的編了,抄錄下來太長,且簡略述之。
林鵬,原名張德臣,後改林鵬,字翮風。河北易縣人,生於一九二八年農曆正月廿八。一九四一年入晉察冀邊區革命中學讀書。一九四三年任區幹部。一九四五年以正連級入伍,任晉察冀一分區團、師政治部通訊幹事。一九五二年赴朝參戰,任六十五軍戰地記者、報社主編。一九五八年轉業到山西,歷任山西省人事局秘書,省革委會業務組幹部組副組長,省輕工廳科技處處長。
光看這些,不過是個有著革命經歷的老幹部。這樣的人多的去了,若要佩服,去了榮軍敬老院,進了門就得一步三磕頭,直到爬著出來。
再看下面這些。
改革開放以來,聲名大震,曾任山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創作評審委員會委員。為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山西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太原師範學院名譽教授。出版著作有《崖書論》、《蒙齋讀書記》、《平旦札》、《林鵬書法》、《蒙齋印話》,長篇歷史小說《咸陽宮》。還有即將出版的這本--《過往雲煙》。
還不行。大陸省區(含直轄市)書協主席,一屆就三十個還掛零,加上曾任,比我家的祖宗牌位還要多。就是出了那麼多書,也沒有什麼可稱道的,我周圍的文人朋友,哪個不是十幾部二十部?
說到底,經歷不是一個又一個的層級(官職),也不是一冊又一冊攤開的書本,這些都是直線的,平面的。經歷是一個豐厚的存在,是巍峨的山巒,更是山巒上升騰起的雲嵐。不是仰首可視的豐碑,也不是抬腿可進的殿堂,就是那麼一個歷盡滄桑,又渾身正氣的人。
真正的經歷,不是多少了不起的偉績,要的是曲折,乃至挫折,入死出生的驚懼。
這才是林先生經歷中最為可貴的,也是讓我由衷佩服的。不必詳述了,有位朋友正在寫他的傳記,相信看過的人,會同意我的這個看法。這裡連簡略述之的必要都不必。林先生有首名為《回鄉》的詩,既見經歷,見性情,也見才華。詩曰:
書劍飄零四十年,歸來依舊老山川。
項上得腦今猶在,肚裡初心已茫然。
丹心碧血成底事,白髮青山兩無言。
小子狂簡歸來晚,尚有餘力綴殘篇。
對了,無意中寫出了經歷的真諦,就是,只有昇華為性情的經歷,熔鑄進才氣的經歷,才是讓人敬重的經歷。
還有一首詩,也頗見性情,不妨也抄在這裡:
吊兒郎當小八路,自由散漫一書生。
命中註定三不死,胡寫亂畫老來風。
這裡的三不死,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經歷過三個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沒有被打死,困難時期沒有被餓死,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沒有被整死。」(《丹崖書論》第二三五頁)
這經歷,用他的話,還有一種更為簡潔的表達:挨整三十年,讀書三十年。
看了這些經歷,瞭解了他的性情,他的才氣,就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人,這樣的人有多高的志向,積三十年之功,能做出怎樣的業績了。
前面說「挨整三十年,讀書三十年」,還應當加上「著述三十年,精進三十年」。
精進一詞不好理解,我的本意是,有人有著述而無精進,比如在下,有人有精進而無著述,比如時下不少高談闊論,而一下筆便露怯的學者。林先生則反是:會讀書,善思考,呈才使性,多方建樹,筆走龍蛇,碩果累累。最能說明這精進成果的,該是經過三十年的磨礪,終於成為一代名書法家、名作家、名學者。
這是人生的大成功,也是挨整的大成功。
挨整與成功之間的關係,當他自己還氣猶填胸之際,倒是他的老首長,北京某部劉紹先政委先他一步,看了出來。九十年代初,一次去北京,去看望老首長,劉政委說:「林鵬,你應該感謝你挨得那些整。你要是不挨整,你能讀了書,能寫出長篇小說,能寫學術隨筆,能寫一筆好字嗎……跟你一發子的多了,誰能像你。」
既已寫了林先生的經歷,且將以之作為下面談論他的散文的依憑,不妨在這裡,也將他的書藝與學問作一概述,這樣,後面說起他的散文,就更實在了。
他是當今的草書大家。料不到的是,其起步竟是篆刻。學篆刻,是為了學會篆字讀《說文》。為什麼讀《說文》。是為了學習古典文學。這個路子,是他轉業到山西後,因工作之便,結識了從教育部下放到山西的右派分子,語言學家孫功炎。孫先生給他說的:「把《說文》攻下來,直接就攻讀十三經、先秦諸子……把眾經諸子攻下來,你再看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文集),就像大白話一樣。」(《蒙齋印話》)
於是便下了十幾年的功夫,由篆刻而篆字,由《說文》而先秦經典。
這是起始,也可說是最初的功夫。接下來就分作兩途,一是書藝的發展,一是學問的發展。
書藝的發展,有一個篆書而草書的過程,仲介則是明清之際的山西草書大家傅山先生。是理之必然,也是性之必然。有了篆書的底子,再進入草書,這是一些研究林氏書法的人,不大注意的。從最規整的,到最草率的,其成功的奧秘或許在這裡吧?
學問的發展,則是由眾經諸子,到專注一經一子,一經者,《禮記》也,一子者《呂氏春秋》也。
書藝與學問相糾結的,則是傅山研究,《丹崖書論》。
學問與寫作相糾結的,則是長篇歷史小說《咸陽宮》。
直到二十世紀終結,他還不知道,他還有另一樣大本事,這便是盡情盡性而又元氣沛然的散文寫作。
想到他初到部隊,是通訊幹事,後來做到軍報的主編,擅長的是通訊寫作,我的腦子裡,登時就閃過一個意象:一條蛟龍,幾十年騰雲駕霧,興風作浪,到了耄耋之年,一回頭,又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一切都是機緣的巧合,一切都是命運的撥弄。一句話,一切都是才情的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