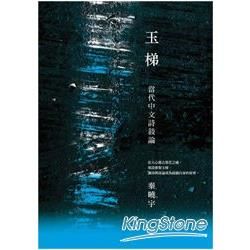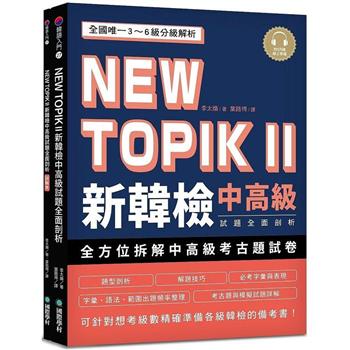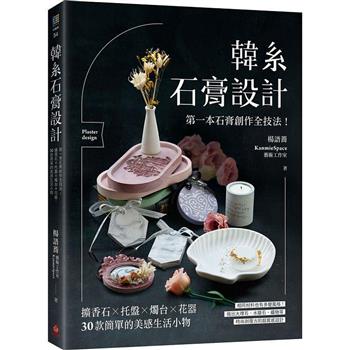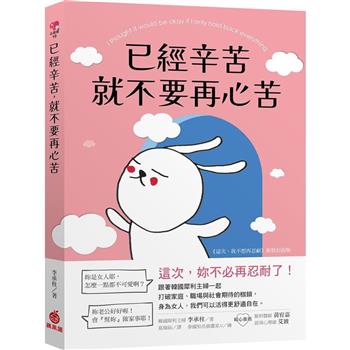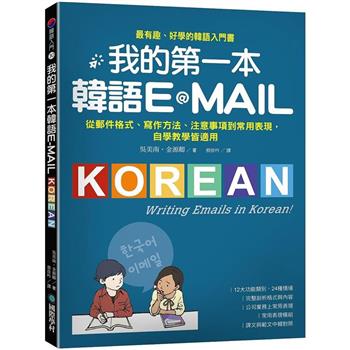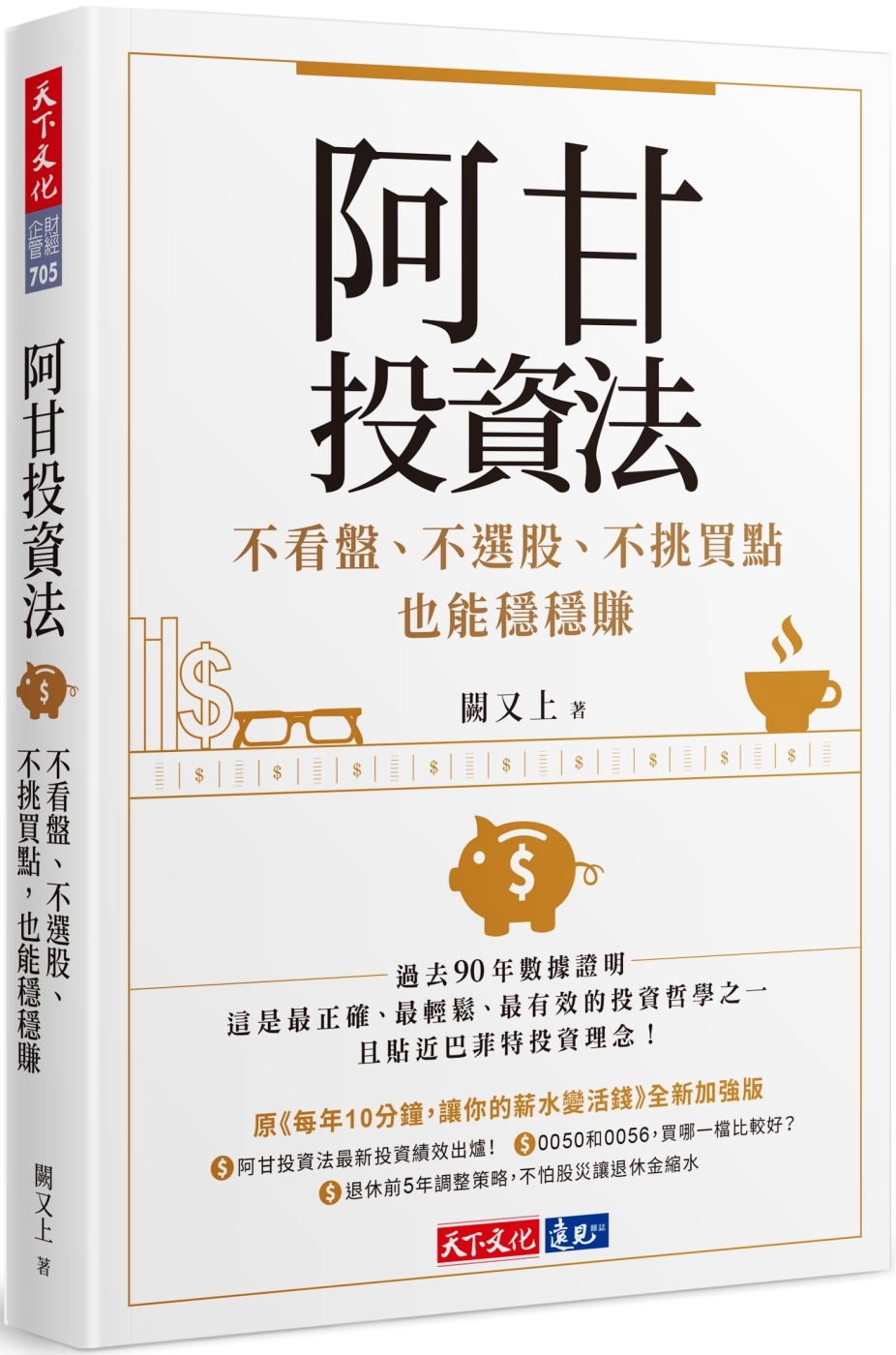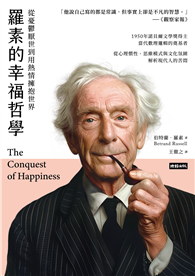推薦序
玉梯上的眺望∕楊煉
我不想給秦曉宇套上「某某代」的稱呼。一個特立獨行者,不會類同於批量生產的一代人。相反,他的思想,得滋養每一代。我們的初次見面,鉚定於林立的啤酒瓶和一本《七零詩話》。後者更鮮明有趣得多。因為「詩人」太多了,而敢把自己定位為詩歌批評家的人很少,拿出第一本論著,就直接冠以古稱「詩話」的人,我此前從沒見過。我的神經,被「詩話」一詞觸動,因為那遠不止一個古意盎然的標題,甚至不只是中國「傳統的」詩論形式。它有意思,是因為特定的形式能包含特定的思想。我面前這個人,肯定仔細思考過「怎麼寫」,而不僅僅把一些想法塞進散漫的文字了事。這個感覺,完全被閱讀《七零詩話》所印證。
一如古典詩話,這本書也由大量片斷拼貼而成:詩人趣聞、詩作擷英、古典佳話、舶來思緒、他人之諷議、一己之心得,以至貌似離題的隨想漫筆等等,材料從紀實到思辨到想像,性質絕然不同,卻又統一於書寫的文學風格。正是我強調過的獨特「散文」風格,一種僅存於中文裡的傳統(見拙文《散文斷想》)。「七零」既是他出生的年代,更是一個回溯的角度,讓他檢視「當代中文詩」招牌下的雜交奇觀。我們懷有它們全部,卻又不同於其中任何一個。由是,我們的原創性,也是一種不得不。我說過,「當代中文詩」的特徵,在其觀念性和實驗性,因為,它沒法因襲任何現成觀念,也只能用每一行詩實驗存在的可能。我們的尷尬和機遇都在這裡。從《七零詩話》起,秦曉宇的一系列精彩文章,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極大注意。
對我(我的詩!)來說,更堪稱期待已久、終逢知己!他的蒙古大漠生長背景,他理工科學歷包含的求「真」執念,他廣博的古典學識和化古鑠今的能力,他對西方詩學的深入和對自身創造性的自覺,在在成為一種標誌:當代中文詩,終於有可能突破過去零積累、甚至負積累的窘境,進入正積累的階段了。我很高興,這變化不曾減少思想深度,相反,得之於在深度中的會合。
序
這六篇文章涉及的所有詩學問題,大體可以分為文化詩學、形式詩學、漢字的符號詩學這樣三個相互關聯、相互包含的層次。文化詩學將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立場預設為前提,其核心是一種探求意義與價值的解釋學,為此它不僅在知識學的層面上展開,更是在思想層面上展開的;就文化詩學而言,東西方可以充分共享,於相互吸收、深度對話中實現互釋、互證與互識,進而達至跨文化的創構。形式詩學反對一切粗糙、粗陋、粗浮、粗俗的寫作,同時亦有別於形式主義。
正如某位批評家所說,形式主義者不重視形式到了任由其脫離內容的地步;而形式詩學不僅關注形式本身,而且重視形式說服力、形式必要性、「形式之責任性」(羅蘭.巴特語),也就是從形式到內容的過程。對於形式詩學,東西方可以相互借鑑,但只能部分共享,譬如中國詩人完全可以寫十四行詩,而一位英國詩人卻沒法寫一首七律,因為七律的形式已然不是一個純形式問題,它牽涉到漢字性這一中文詩學的「獨得之秘」。漢字是漢語及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中國文學真正的特殊性說到底就是漢字性問題,每個傑出的中國詩人,都會在寫作深處觸及這個問題。對於漢字的符號詩學,以及如何將其運用於批評實踐,我希望我做了一點有益的開拓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