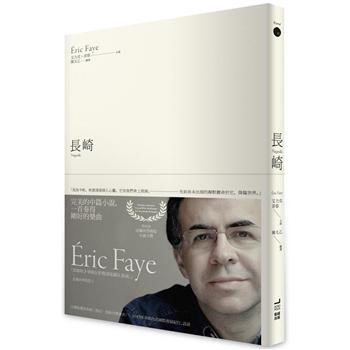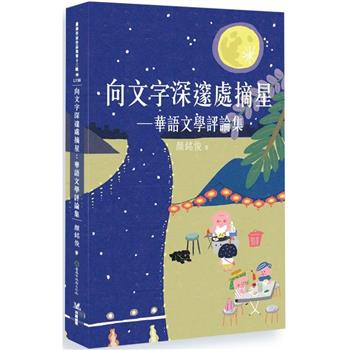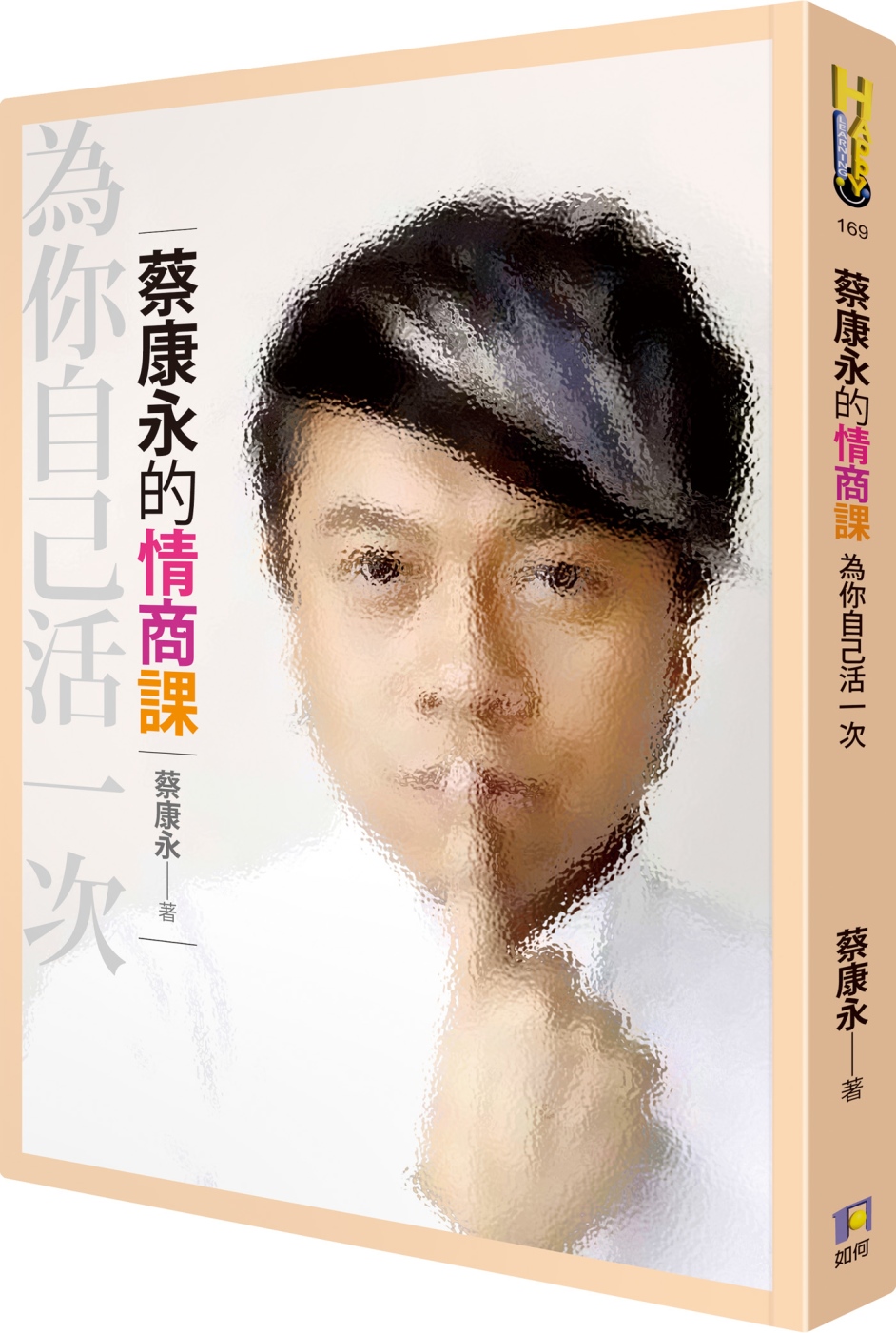序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是對20 世紀80年代以降,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下篇「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範型』」,是對20世紀60年代至今,先鋒詩歌發展史上的幾位標誌性、代表性的詩人的研究,並試圖在論述時以個案帶出史的線索。筆者希望做到專業性和可讀性,學理性和時效性並舉,勾勒和闡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的概貌,為此後對先鋒詩歌做進一步的歷史和美學評價,提供相對可靠的起點或某一角度的參照。
本書取名為「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代表著我對先鋒詩歌的價值的基本認識,同時也是此書的基本論旨。我以為,對先鋒詩歌而言,詩歌外在的型模「成規」,還不是決定性的,決定性的是那種「表達現代人對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語言」,即先鋒詩歌的意味和表達其意味的話語方式,是同步發生、彼此選擇、彼此發現、彼此照亮的。這決定了優秀的先鋒詩歌,不僅是特殊的修辭技藝,也是詩人試圖揭示和命名生存、歷史、生命、文化中的噬心困境,所產生的「精神重力」。而且,這種「精神重力」體現在先鋒詩歌中,也並非類聚化的「代言人」式表達,而是來自於詩人個體生命體驗所浸潤的「個人詞源」。在現代社會,先鋒詩歌要為捍衛個人心靈感受的價值而申辯,詩人雖然要處理個人經驗中的公共性,但更專注於公共經驗中個人的特殊性。詩人尋求個人化的語言,個人化的書寫、命名能力,常常將公共化的語詞變為個人「發明」般的新詞,像是汲於「個人詞源」的深井。
我以為,同時堅持這兩個維度,將有助於我們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如何衡估「詩與真」的關係問題。在此,「精神重力」和「個人詞源」,是在對話關係中展開的兩個相互激發、相互平衡、相互吸引──簡言之,是「相互贈予」的因素。對先鋒詩而言,缺乏「個人詞源」的「精神重力」,時常會淪為空泛的見證式表態;而沒有「精神重力」在其中的「個人詞源」,則常常淪為微不足道的私語化「遣興」。正是成功的個人心靈詞源,贈予精神重力以藝術的尊嚴;而精神重力,則贈予個人心靈詞源以具體歷史生存語境中的分量。
詩學文本介入當下寫作語境的活力和有效性,是我寫作此書的動力。在寫作這些詩人專論和理論探討文字時,我會不斷回想起中國先鋒詩歌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今所走過的激動人心的道路。同時,我也清晰地感到,從價值確認,詮釋模式,運思向度,到措辭特性上,自己的批評方法也正在經歷著一個較大的轉變。下面,我想集中對書中所實踐的批評意識做一些必要的說明,因為它不僅是詩歌批評方法轉型的問題,還事關如何打破當下詩歌創作的「幽閉」狀態,重置詩的具體歷史及文化位置,以及對中國先鋒詩歌歷史承載力和形式激發力的綜合性理解。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詩歌批評家或是單一地貼近社會學和文化闡釋,或是專注於文體形式研究,或是印象式地表達自己的審美感受。這些批評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顯的缺陷──它們人為地將先鋒詩的意義闡釋和形式研究割裂,硬性地使之「各自為陣」了。上面談到,先鋒詩是「表達現代人對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語言」,這決定了其「功能」與「本體」是同步呈現的。緣此,我們應該樹立「舞蹈與舞者不能分開」(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語)的意識,積極尋求真正有效地「兼治」或「打通」二者的方式,避免「分而治之」帶來的缺失。如果說,前些年採取「分治」是為了使詩歌批評更走向「內部」,有一定專業推進力的話,那麼今天依然如此,則就有明顯的保守性了。
詩歌於社會、歷史、文化、性別、階級等大有關係,其文體修辭形式也是詩歌之為詩歌的本體依據。在有效的批評中,它們均不可或缺。我們不能顧此失彼或非此即彼,而應有能力將之扭結一體做出綜合批評。說到底,真正有活力的詩歌批評,探討的應是綜合性的事關具體歷史語境下先鋒詩「寫作」諸方面的問題。而要對「寫作」這個關聯域廣闊的概念進行綜合考察,則需要樹立「形式就是恰當地達到了目的的內容」,即本體與功能不再硬性割裂的、求實的理念。因為,「那些外部關係本身即為文本所有,包含在文本內部。內部和外部的區分,正如大多數這類二項對立一樣,結果都被證明是人為的,是騙人的。」圍繞綜合性的當下詩歌「寫作」問題,筆者明顯感到上述詩歌批評,將本體與意義做「二分法」的處理,或依賴於某種單一的批評「範式」進行批評寫作,是乏力的,至少是不順手或不夠用的。如何將詩歌的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有效地打通,就成為需要我們考慮的重要問題。
本書作者試圖從單一化的批評模式中跳出,探尋一種姑且稱之為「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方式。本書的「上篇」,採取了較為明顯的「知識僭越」或曰跨界的策略,逾出專門化的「學科知識體制」,開啟歷史哲學視野,乃至社會學視野,將歷史話語、社會學話語、哲學話語,融通到詩學話語中,為先鋒詩的意識背景做出深層次的透視,以求把詩歌清晰地顯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有這個意識背景鋪墊,本書「下篇」的詩人論,同樣打破以往詩歌批評內在的制度性侷限,在對詩人個體審美話語的分析中,自覺地引入歷史話語分析的維度。實踐一種以話語的歷史生成為重心,同步開啟歷史文化闡釋和文體修辭闡釋的新的綜合批評模式。
使詩論話語能對社會歷史和修辭學的雙重視野作出回應,把對詩歌的文體意識、修辭特性的細讀辨析,同步融滲到歷史話語的建構中,這就是我的想法。因此,面對中國先鋒詩歌,筆者不僅僅觀照其形式本體,還將之作為一種勇毅的文化實踐、文化奮爭,來考察其特定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比如在論述當代先鋒詩歷史上不同階段的標誌性詩人,特別是郭世英、張鶴慈、北島、西川、于堅、翟永明、海子時,筆者就自覺地將其納入較為開闊和縱深的社會歷史和詩學的對話關係中,體現了微觀研究中的宏觀視野。從對其詩歌話語的修辭學、文體形式的分析中發現「症候」,將之引入某種社會文化視野,透視出詩的困境和可能性,揭示出其歷史的、文化的壓力。
我為自己設計的批評路線和目標,是要回答如下問題:詩歌說了什麼?怎樣說的?由誰說?對誰說?在什麼時間和歷史語境下說?納入何種意義系統中說?這就既離不開對詩歌揭示的具體歷史語境的分析,同樣也離不開對個人話語的修辭學分析。因為,詩歌不僅表達了詩人的情感經驗,而表達這種情感經驗的修辭路徑本身,也是他的歷史的情感經驗的重要構成部分;換言之,不只是他的情感經驗運用了某種修辭,同時也是這種修辭才「建構」了他的歷史情感經驗。詩歌批評的歷史化、社會化內涵,其實是內在於語言修辭方式裡的。因為在很多時候,不只是詩人的意識和修辭的才能決定著話語的意義,而且還有具體歷史語境中的話語的集體無意識的「自我運動」,決定了詩人的意識。
「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要求批評家保持對具體歷史語境和詩歌語言∕文體問題的雙重關注,使詩論寫作兼容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和詩學問題的專業性,從而對歷史生存、文化、生命、文體、語言(包括宏觀和微觀的修辭技藝),進行扭結一體的處理。既不是單一地對其文本解讀來傳釋詩歌母題與理念,避免只做主題的社會學分析;也不單純從本體修辭學的角度探尋其詩歌話語的審美特性,避免把詩歌文本從歷史語境中抽離,使之「美文」化、風格技藝化。而是將它們相互融滲,共時遊走。這樣,詩歌批評就可能有效地聯接起修辭學分析和歷史話語分析,文體學批評和文學社會學批評,體現出宏觀歷史洞察中的微觀專業化視角,使批評充滿具體歷史語境中的緊張感和摩擦力,和對詩歌寫作內部問題的有效打開。在自覺而有力的歷史文化批評和修辭學批評的融會中,才可能增強批評話語介入當下創作的活力和有效性,並能對即將來臨的歷史─審美修辭話語的可能性,給予「話語想像」、「話語召喚」的積極參與。
我認為,自覺地將對美學的省察與對歷史生存的省察交織在一起,從人的具體歷史語境出發去把握先鋒詩歌的活力和美,使語言不再作為修辭學意義上的「美文」,而是人與生存之間真正的臨界點和困境來考察,這些都是一個時代的詩學富於活力的標誌。雖然筆者做得尚顯粗笨,但也清晰地感到了批評理念的這種轉變,給自己帶來的較為開闊的批評視界。
或許會有同行說,你所說的「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不就是時下流行的那種告別「新批評」之類的形式主義研究,走向所謂的「文化批評」麼?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文化批評」對我確有啟發,但我以為,與「文化批評」相比,「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更多地具有詩學問題的專業性。它是對詩歌語言技藝環節和歷史生存的雙重關注。這裡的「修辭學」既指向審美的語言技藝,同時又被「歷史」所修正和限定,換言之,它同時指向對詩歌文本審美修辭特性的分析,和對人置身其中的具體歷史語境的揭示,是一種綜合的考察審美話語和歷史話語的「實踐-反思的詩學」。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抱怨道:「所有對文學作品審美價值持敵意者不會走開,他們會培養出一批體制性的憎恨者」,「文學研究者變成了業餘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我以為,從為「文學性」和「經典性」籠統地辯護上來看,布魯姆的抱怨有一定道理和糾偏的時效性。但布魯姆對支撐著何為「文學性」、「經典性」,誰的「文學性」、「經典性」,背後的價值預設和認知前提,缺乏某種必要的反思。似乎它們是「天經地義」、「從來如此」而無需爭辯的。比如,在他看來,艾略特(T.S. Eliot)的詩歌,不僅算不上「經典」,甚至算不上是好詩。難道就因為艾略特詩歌除審美話語外,尚有較多宗教、哲學、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甚至社會歷史文化元素嗎?而這些,在我看來恰恰是艾略特詩歌的傑出之處。他有能力完成話語「越界」,將之「融通」到詩歌之中。看來,指責別人是「憎恨學派」(不無道理)的布魯姆,也是一個與之構成戲劇性對偶的「憎恨者」,他陷入了一個自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框架,似乎詩學批評可以是一種「自足的」書寫行為,不需要在歷史、社會、文化視野中給出新的命題,新的應答。但真的是如此嗎?我看到布魯姆本人的詩學批評,其中某些最具激發力的部分,其實也不乏對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論、神學、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強力意志哲學、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歷史─文化週期」理論、科學哲學的「範式」理論、後現代思潮……如此等等,頗多的借重。
所以,我們完全不必站到「是歷史話語,還是審美話語?」的二元對立框架中的某一邊。它們並不是誰驅逐誰的問題,而是可以綜合處理的。我認同王一川對語言的「修辭性」所做的更開闊的理解,「語言是我們立身其中的世界本身的行為,是使我們的存在獲得自我理解的東西。……修辭性更突出的是語言活動的社會動機和社會效果:修辭指人為著感染他人,確立或改變自己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位置而有力和有效地運用語言,這勢必更注重語言活動中的扭曲、含混、破碎、掩飾、潤飾等複雜因素。這既可以解決語言與『生活世界』的複雜關係問題,又可以使一直未有著落的價值評價找到落腳點。」
今天的詩歌批評家,既要有能力越過單薄的「內部批評」的界限,向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語境敞開,又需要保持專業的文本細讀、修辭分析的態度。使詩歌話語不僅作為元詩意義上的「美文」,也是人與歷史生存之間真正臨界點和真正困境的「作為存在之家的語言」,使自己的批評話語能在歷史話語空間和審美話語空間,真切而機敏地縱深穿逐。長期以來,我們的詩歌批評過度強調社會性、歷史性,最後壓垮了語言審美性,這肯定不好。但後來又有過分強調「審美話語自主性」的大趨勢,這同樣減縮了詩歌批評的能量,使詩歌批評沒有了視野,沒有文化創造力,甚至還削弱了它的命題的承載力、摩擦力、推進力。有活力的詩歌批評,應能構築雙重視野,在對詩歌文體和語言修辭紋理的剖露中,同步作出某種有機的、具體的歷史性引申。注意,下面的話並非多餘──我這裡所說的「歷史」,之所以被「具體」所限制,是在強調現代詩歌批評要重視的是實際的、具體的歷史語境。它在具體歷史意識的多樣性、世界的多樣性、理論的多樣性、人的多樣性的氛圍中產生出來。與本質主義的軸心化的歷史意識不同,現代詩歌批評強調歷史的具體性,強調詩人「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的重要性。
在對理論批評姿態或對批評家角色的確認上,筆者也試圖體現出職業自覺,提醒自己理論批評相對的自立性,亦即理論批評與創作的「平行」和「對話」關係。批評為了更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價值,有必要重新確立自己。詩學批評不是詩歌創作的單純的附屬和輔助,批評家也不是詩人的「僕從」或「西席」。如果說過去曾經如此,那是由於真正意義上的詩學批評沒有合理、合法地建立起來。批評與創作的合理關係只能是平行和對話,一個自覺的批評家,應具有既深刻介入創作而又能獨立於創作的精神和書寫能力。對批評價值、職能和過程的一定程度的自覺,使筆者得以以較為敏銳和自如的心境,提出某些值得討論的問題。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感到了詩歌批評在獲具相對的自立後,煥發出的自身的活力與魅力。
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在《批評與真實》一書中揭示出一個有趣的事實,即如今許多有效的批評家也成了「作家」。這個說法可能會使那些「學院派」理論家蹙額,但若是我們換一種表述,就會看到它骨子裡的真確性。按照巴爾特的說法,「作家」不應以他所書寫的文類為特徵,而只應以某種「言語的自覺性」為特徵,他體驗到語言的深度,而不只是它的工具性或美感。以前,批評與創作是被一個古板的神話隔離了,而今天的作家與批評家處於同樣纏繞──也很可能是歡愉──的寫作環境中,挖掘著同一個對象:語言。我很認同巴爾特的說法,這種意識不僅會影響到理論批評話語的表面的修辭效果,而且還註定會激發出批評家的陌生的思考,異樣的書寫歡愉和情感經驗的衝撞力。文學理論批評,特別是詩學理論批評,不僅僅要做到「達意」,同時其本身也應作為一種揭示生存和語言奧秘的創造性的「寫作」。在挖掘語言的某些過程中,我的確曾享受過創造的快樂。
上述言及的,更多是筆者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所希望遵循的意識。希望做到和真正做到肯定還不是一回事。筆者究竟做到了怎樣的程度,還要請讀者批評指教。
本書得以在臺灣出版,多承秀威公司的認可,特別是黃姣潔女士和劉璞先生的熱誠幫助,謹此敬致謝忱。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杜棲梧女士,由於我的駑鈍,是她完成了全部的文字輸入(我近年出版的其他著作同樣如此),並同步修正了書中某些文句的訛誤。多年來,她一直無怨無悔地幫助我,我的感激和敬意是無法言說的。
陳超 記於2012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