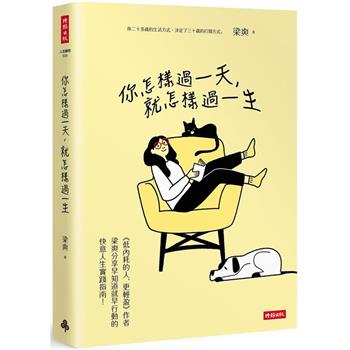新奇的發現──《敦煌圖錄》
有一天我從盧浮宮出來,經過盧森堡公園,根據多年在巴黎散步的習慣,總要經過聖傑曼大道,順便遛到塞納河畔舊書攤去流覽一下內容豐富的書籍。今天為了留一點參觀盧浮宮的古代美術傑作的紀念,我特意去美術圖片之部找尋……忽然發現了一部由六本小冊子裝訂的《敦煌圖錄》。我打開了盒裝的書殼,看到裡面是甘肅敦煌千佛洞壁畫和塑像圖片三百餘幅,那是我陌生的東西。目錄、序言說明這些圖片是一九○七年伯希和從中國甘肅敦煌石窟中拍攝來的。這是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前後一千年中的創作。這些壁畫和雕塑的圖片雖然沒有顏色,但那大幅大幅的佛教畫,尤其是五世紀北魏早期壁畫,氣勢雄偉的構圖像西方拜占廷基督教繪畫那樣,人物刻畫生動有力,其筆觸的奔放甚至於比現代野獸派的畫還要粗野。這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畫,使我十分驚異,甚至不能相信。我愛不釋手地翻著、看著那二三百幅壁畫的照片及各種藏文和蒙文的題字。這是多麼新奇的發現啊!半個鐘點、一個鐘點過去了,這時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臨,塞納河畔黃昏的煙霧也慢慢濃起來了,是收拾舊書攤的時候了!書攤的主認看我手不釋卷的樣子,便問:「是不是想買這部書?」我說:「我是中國人,這本書就是一本介紹中國敦煌石窟古代壁畫和塑像的照相圖冊。我很想買它,但不知要多少錢?」他回答說:「要一百個法郎。」那時我身邊沒有這麼多錢,正在猶豫著。賣書的人看我捨不得離開的樣子,就說:「還有許多敦煌彩色的絹畫資料,都存在離此地不遠的吉美博物館。你不必買它了,還是親自去看看再說吧!」
第二天一早,我來到吉美博物館。那裡展出著許多伯希和於一九○七年從敦煌盜來的大量唐代大幅絹畫。有一幅是7世紀敦煌佛教信徒捐獻給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經》,時代早於文藝復興義大利佛羅倫斯畫派先驅者喬托七百年;早於油畫的創始者文藝復興佛拉蒙學派的大師梵愛克八百年;早於長期僑居於義大利的法國學院派祖師波生一千年。這一事實使我看到,拿遠古的西洋文藝發展的早期歷史與我們敦煌石窟藝術相比較,無論在時代上或在藝術表現技法上,敦煌藝術更顯出先進的技術水準。這對於當時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跡。因為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自己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
上面的比較,使我驚奇地發現東西方文化藝術的發展有如此不同的差距,看到了我國光輝燦爛的過去。我默默思忖著:對待祖國遺產的虛無主義態度,實在是數典忘祖。回憶在艱難困苦中漂洋過海來到巴黎這個世界藝術中心,十年來差不多都沉浸在希臘、羅馬美術歷史理論與實踐中,竟成長發展到如此的地步。在這一事實前面,我對巴黎藝壇的現狀深感不滿,決心離開巴黎,而等待著我的,當然不是塔西堤,而是蘊藏著四~十四世紀民族藝術的敦煌寶庫。
就在我打算要離開巴黎之前,接到了南京國民黨教育部長王世傑的電報,聘請我為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教授,並要我從速返國任職。我接受了他的邀請。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守護敦煌五十年:常書鴻自述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331 |
學者/科學家 |
$ 332 |
美術 |
$ 332 |
人文歷史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社會人物 |
$ 378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420 |
人文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守護敦煌五十年:常書鴻自述
自我一九四二年接受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任務,一九四三年三月踏上敦煌的土地,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在我生命的長河中,一大半獻給了敦煌,獻給我所熱愛和嚮往的敦煌事業。無論是在戈壁敦煌,還是在異國他鄉,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牽夢繞的就是你──敦煌。
本書是「敦煌的守護神」──常書鴻先生自剖其一生及其與藝術的淵源。留學法國時精進於油畫的技藝,卻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驚訝地發現中國古藝術的珍寶:敦煌石窟壁畫。他在一九四三年遂其心願抵達敦煌,於隔年出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長達五十年的光陰,在國共時局交替的艱困下,他致力於敦煌藝術的探勘、描摹、修護和文獻整理,並將之付諸於出版、展覽,使世人重新發現此世界級遺產的瑰麗。凡此種種,透過常書鴻先生的自述紀錄,顯得格外的真實與珍貴。
本書特色:
為常書鴻先生自述其一生,尤其是保存敦煌藝術最真實的紀錄。讀者可透過本書,了解常書鴻等人是如何被保存中國珍貴的藝術遺產──敦煌石窟並將其發揚至世界。
作者簡介:
常書鴻(一九○四─一九九四)中國當代畫家、敦煌藝術研究家。一九二七年赴法國留學,學習油畫。一九三六年回國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一九三六年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主任。一九四三年抵敦煌。一九四四年後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一九八二年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因一生致力於敦煌藝術研究保護等工作,被人稱作「敦煌的守護神」。有《常書鴻油畫集》、《常書鴻繪畫作品集》、《敦煌藝術》等行世。
章節試閱
新奇的發現──《敦煌圖錄》
有一天我從盧浮宮出來,經過盧森堡公園,根據多年在巴黎散步的習慣,總要經過聖傑曼大道,順便遛到塞納河畔舊書攤去流覽一下內容豐富的書籍。今天為了留一點參觀盧浮宮的古代美術傑作的紀念,我特意去美術圖片之部找尋……忽然發現了一部由六本小冊子裝訂的《敦煌圖錄》。我打開了盒裝的書殼,看到裡面是甘肅敦煌千佛洞壁畫和塑像圖片三百餘幅,那是我陌生的東西。目錄、序言說明這些圖片是一九○七年伯希和從中國甘肅敦煌石窟中拍攝來的。這是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前後一千年中的創作。這些壁畫和雕塑的圖片雖...
有一天我從盧浮宮出來,經過盧森堡公園,根據多年在巴黎散步的習慣,總要經過聖傑曼大道,順便遛到塞納河畔舊書攤去流覽一下內容豐富的書籍。今天為了留一點參觀盧浮宮的古代美術傑作的紀念,我特意去美術圖片之部找尋……忽然發現了一部由六本小冊子裝訂的《敦煌圖錄》。我打開了盒裝的書殼,看到裡面是甘肅敦煌千佛洞壁畫和塑像圖片三百餘幅,那是我陌生的東西。目錄、序言說明這些圖片是一九○七年伯希和從中國甘肅敦煌石窟中拍攝來的。這是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前後一千年中的創作。這些壁畫和雕塑的圖片雖...
»看全部
作者序
新版前言
常書鴻先生《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書新版即將與讀者見面的前夕,友人們希望我能介紹一點關於這本書形成的過程。我腦海中浮現出我與先生共同生活、學習、工作四十八年一幕一幕的往事,心潮起伏,但又不知從何談起。我非常笨拙,就簡略談一點吧!
在與先生共同生活近半個世紀的日子裡,我深深感到先生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一位經歷了清朝、民國到新中國的三朝人物。在中國戊戌以來翻天覆地的歷史洪流中,他像一塊頑石,由黃河源頭隨著這條母親河浪濤翻騰、衝擊、滾跌以及河水的撫慰,而形成了一塊奇石,一個奇石式的...
常書鴻先生《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書新版即將與讀者見面的前夕,友人們希望我能介紹一點關於這本書形成的過程。我腦海中浮現出我與先生共同生活、學習、工作四十八年一幕一幕的往事,心潮起伏,但又不知從何談起。我非常笨拙,就簡略談一點吧!
在與先生共同生活近半個世紀的日子裡,我深深感到先生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一位經歷了清朝、民國到新中國的三朝人物。在中國戊戌以來翻天覆地的歷史洪流中,他像一塊頑石,由黃河源頭隨著這條母親河浪濤翻騰、衝擊、滾跌以及河水的撫慰,而形成了一塊奇石,一個奇石式的...
»看全部
目錄
目錄
季羨林先生的賀詞
初版前言/路甬祥
新版前言/李承仙
第一章 人生初途
1.童年生活
2.園遇知音
第二章 留學法國
1.巴黎學子
2.藝術上的彷徨
3.新奇的發現──《敦煌圖錄》
4.在巴黎—北平的國際列車上
第三章 西行前記
1.回國後的遭遇
2.大後方的風塵
3.破釜沉舟去敦煌
第四章 初遇敦煌
1.沿著河西走廊前進
2.致禮莫高窟
3.戰風沙 築圍牆
4.樂在苦中
第五章 艱難歲月
1.心血瀝瀝
2.苦度難關
3.父女畫展
4.黎明的前夜
第六章 國寶之光
1.歡慶解放
2.籌備京展
3.接待周總理參觀展覽
4.人民的表彰...
季羨林先生的賀詞
初版前言/路甬祥
新版前言/李承仙
第一章 人生初途
1.童年生活
2.園遇知音
第二章 留學法國
1.巴黎學子
2.藝術上的彷徨
3.新奇的發現──《敦煌圖錄》
4.在巴黎—北平的國際列車上
第三章 西行前記
1.回國後的遭遇
2.大後方的風塵
3.破釜沉舟去敦煌
第四章 初遇敦煌
1.沿著河西走廊前進
2.致禮莫高窟
3.戰風沙 築圍牆
4.樂在苦中
第五章 艱難歲月
1.心血瀝瀝
2.苦度難關
3.父女畫展
4.黎明的前夜
第六章 國寶之光
1.歡慶解放
2.籌備京展
3.接待周總理參觀展覽
4.人民的表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常嘉煌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3-04-25 ISBN/ISSN:978986591562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社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