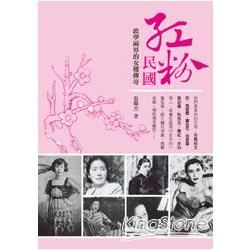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紅粉民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49 |
人文史地 |
$ 395 |
中文書 |
$ 440 |
社會人物 |
$ 450 |
女性人物 |
$ 450 |
社會人文 |
$ 450 |
歷史 |
電子書 |
$ 50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紅粉民國
民國初年的女性傳奇人物,多與政學兩界的家事、國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她們的內心掙扎、自我覺醒、社會參與、情感困局,乃至沉浮命運,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詭異和變遷。在傳統的中國男性「父權當道」中,走出家庭、爭取權利的多元面貌,以及她們豐富的內心世界,乃至長期以來自身性別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並深入考察該人物的歷史局限性和人性陰暗面,澄清還原已經被嚴重污染扭曲歷史事實,基於對史料和文獻之解讀的客觀認識和價值判斷,相對於一般的歷史述說,更具理性和思辨色彩。
作者簡介
張耀杰,男,一九六四年生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文史學者,傳記作家,書評家。農工民主黨北京市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已經出版著作有《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誰謀殺了宋教仁》、《民國底色:政學兩界人和事》、《北大教授:政學兩界人和事》、《民國背影:政學兩界人和事》、《曹禺:戲裡戲外》、《影劇之王田漢:愛國唯美的浪漫人生》、《中國話劇史》等十多部。寫作之餘還參與過《小關一家人》、《山河作證》、《農電之光》等數十部長短電視片的拍攝與編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