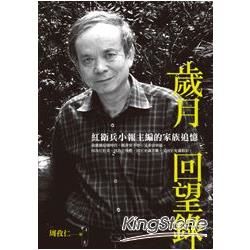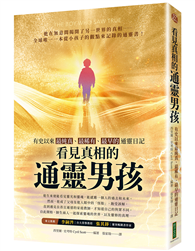序
命運總是樂此不疲地同我開玩笑:認真的和隨意的、殘忍的和荒唐的、早有預感的和猝不及防的。此生註定永無寧日。如被風暴和巨浪擊碎的船,只留給我一塊破碎船板。確實自由了,且再也不會沉沒,我只能在大海漂流,直到如今,年已遲暮,老之既至。
一位朋友,現在身居高位了,他的屬下曾告訴我,說這位高官不只一次在會上講:「我這權利誰給的?黨給的呀。人民給的呀。不能說明我水平高啊!我一位老師,水平比我高許多,時運不佳,最後只當了作家。」據說,他所稱「老師」,就是我。此語謬病存焉。其一,我水平怎麼說怎麼不高;其次,我肯定也不是作家。幾十年來,特殊時代把我整個兒拋在驚濤駭浪中,九死一生。為尊嚴,也為生存,我轉換過的角色太多,從省委祕書到反革命疑犯,從維修電工到高級工程師,從新聞人到經理人……有幾次,甚至幾陷囹圄。
前面提到這位高官,因為好心,讓我遭致了一次幾乎毀滅性的厄運:他為此內疚。我真心實意對他說:人生,不就是一場旅行麼,不就於不同社會途次閱讀了不同人生風景麼?深牆大院是一種風景,竹籬茅舍也是一種風景;高山大野是一種風景,小橋流水也是一種風景……誰能說哪一個更美?重要的是,我比別人閱讀了更多人生景致,這就夠了。歐陽夫子〈醉翁亭記〉有云:「醉能同其歡,醒能述其文」。我喜歡這種境界。醉者,與國與家與人同迷糊,同受難,同抗爭;大悲大喜之後,噩夢醒來,能豁達,能理性,能從容不迫地記錄自己(通過自己,記錄整個社會)所歷所為,所思所想。如認同人稱作家,其源唯當於此了。別無他好,我就喜對著電腦傾訴,說社會、人和自己的命運,並且思考。
如是,隔三岔五,我便寫了。利用工餘、假日和節日,沒完沒了地寫。無意發表,亦無經濟訴求,但得心裡平靜而已。文畢貼去網上,能有讀者點擊,便很滿足;若有被某編輯惠眼偶顧,得以登堂入室,印成鉛字,更加惶惶了。文壇多名利場、是非地,世間何處無知音?涉足渾水而何?七八年間,竟得數十萬字,在電腦螢幕上拼湊起來,密麻一片,其情何等欣慰!中國作家講究級別、講究三六九等。一個局外人,不經意間竟寫出這麼多,按洋人說法,作一WRITER(寫字的人),夠資格了。中國的「作家」二字翻成英文,好像也當是WRITER。
我遭遇這個時代,既非常不幸,又非常幸運。因為它壯美,因為它殘酷,因它充滿苦難,又因它充滿精彩。能以一個見證人的名義,為它的履歷表填寫一行註腳,余願足矣。
周孜仁 2012年10月 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