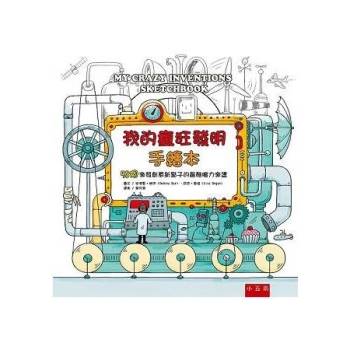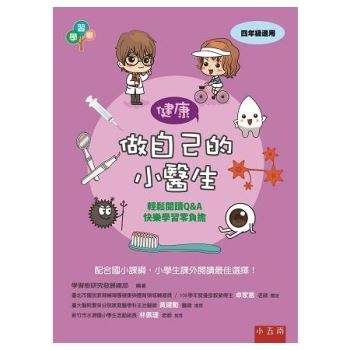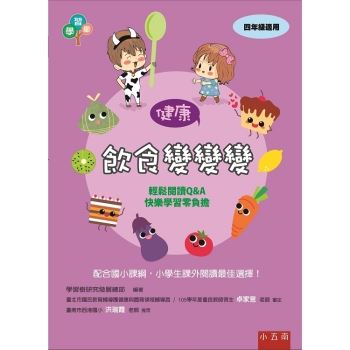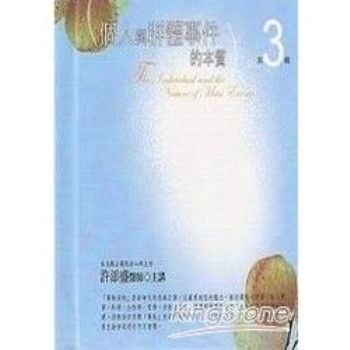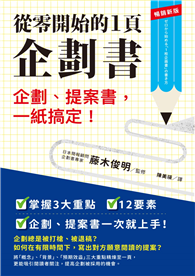「周揚」這個名字的含義
周揚在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壇的時候,用的名字是周起應。一九三四年秋突然棄周起應之名改用「周揚」這個名字。魯迅曾就周起應改名周揚的含義作過一番猜測,認為這表現了周起應要立大志,在文學上做出一番大事業。但他並不以為他的猜測是符合實際的。
一九九八年,譚林通的一篇紀念周揚的文章,才讓人們瞭解到事情的真相:
我認識周揚,是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間在東京小石川區林町的「國師館」,當時他二十一歲,我是初中剛畢業的十六歲少年,那時他叫周起應。他是在與蘇靈揚結合之後,作為一種紀念吧,才開始用「周揚」這個名字的。
(《難忘相識在東京》,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十二頁)
原來,周揚的「揚」,是取自蘇靈揚的「揚」,表示出對蘇靈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殊的親密關係的。
周揚與蘇靈揚的結合屬於婚外戀,是秘密的,時間在一九三四年秋。那時,周揚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原配夫人健在,和周揚一起住在上海。那年夏天,夫人吳淑媛懷的第三個孩子將出生。每次分娩,周揚的母親都要求必須回家鄉生,周揚這次也把夫人連同兩個小孩帶回益陽老家待產。過去,周揚都是等到孩子出生後才回上海的,這次卻沒等到孩子出生就以工作忙為藉口急著回上海。臨走時親口答應第二年暑假回來接母子們去上海。吳淑媛做夢也沒想到,周揚這一去卻是永遠不回來了。他急著趕回上海是要同蘇靈揚另組家庭。他同蘇靈揚另組家庭之後,啟用了「周揚」這個含有特殊意義的新名字。這年八月末寫的〈高爾基的文學用語〉,發表時署名「企揚」,透露了舊名向新名過渡的消息;到秋末寫〈高爾基的浪漫主義〉就正式啟用「周揚」這個新名字了。可憐夫人吳淑媛一直蒙在鼓裡,還一心一意地等著周揚接她出去。她根本沒有想到周揚會遺棄她。她和周揚結婚以來,雙方感情是融洽的。他們住在上海,周揚沒有固定收入,單靠一點零零星星的稿費,是根本無法維持一家的生活的。她每年夏天都要回娘家一趟,從娘家取回一些金銀珠寶首飾,把整個家庭經濟支撐起來,讓周揚能夠安心從事黨的工作。周揚那時能夠穿上考究的西服,能夠進入舞廳尋歡作樂,端賴夫人的經濟後盾。周揚的戰友們生活上有困難,都得到過吳淑媛的慷慨資助。夫人吳淑媛深信不疑,周揚是一定會回來接她出去的。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她還收到周揚從上海寄來的他的譯書《安娜‧卡列尼娜》。抗戰爆發後,吳淑媛的母親還專門寫信去問,是不是不要老婆、孩子了。周揚回信說得十分肯定,他現在在延安工作,決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的。這些現象,更鞏固了她等待的信心。周揚走後,她每年都要做一罈梅子泡製的蜜餞,放在櫃子上,等待周揚回來品嚐。她就這樣帶著孩子等著,等了一年又一年,做了一罈梅子又一罈梅子,等著周揚回來接她出去。直到一九四一年,可憐的女人才從《救亡日報》上的一則報導得知,在延安的周揚早已另有新歡。這個消息首先把吳淑媛的老母親擊倒,不久就含恨死去。老人去世之後,吳淑媛幾乎天天帶著三個孩子到十幾里路外的墓地,趴在墳上搶天呼地痛哭。一哭就是一兩個小時。她,向著遠在彼岸的親人,傾吐滿腔的悲痛,傾吐滿腔的悲憤。她很快就病倒,脖子上長了一串淋巴,全身浮腫,第二年就在極其淒慘的情況下死去。那整整齊齊擺在櫃子上的七罈梅子,見證了她無可告訴的的痛苦、悲憤和不幸。
事情清楚不過,如果不是周揚全無心肝,吳淑媛的老母決不至於遽爾奄忽,吳淑媛本人更不至於這麼年輕就離開人世的。
這樣,「周揚」這個名字,不僅體現了周揚和新人鸞鳳和鳴的甜情蜜意,更體現了周揚肆意玩弄弱女子的感情、棄舊人若棄敝履的冷酷卑鄙。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往事探微:中國文化沙皇周揚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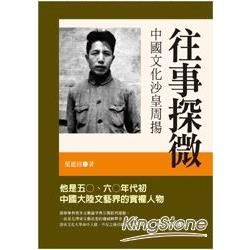 |
往事探微:中國文化沙皇周揚 作者:葉德浴 出版社: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3-07-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30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3 |
文學家 |
$ 308 |
中文現代文學 |
$ 343 |
中文書 |
$ 351 |
社會人文 |
$ 38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往事探微:中國文化沙皇周揚
他是五○、六○年代初,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指揮參與眾多文藝論爭與左翼批判運動,一直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卻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獄,平反之後引起的爭議不遜以往,真正的周揚是誰呢?
透過對文件、歷史中周揚本人以及與其他人的來往紀錄,深入探討周揚真正的面貌。
你想知道周揚對魯迅的忌恨程度嗎?
你想知道周揚對胡風的忌恨程度嗎?
你想知道周揚堅決不肯與丁玲和解的深層原因嗎?
你想知道周揚向病危的馮雪峰「懺悔」的真情嗎?
你想瞭解周揚在「魯藝」領導「搶救運動」的功績嗎?
你想瞭解周揚要把蕭軍打成「日本特務」的經過嗎?
你想瞭解周揚建國後狠整蕭軍的內情嗎?
你想瞭解周揚和江青過招的喜劇嗎?
你想瞭解周揚的「院士」桂冠的含金量嗎?
你想瞭解周揚的翻譯水平嗎?
你想更多地知道一些周揚有趣的和無趣的事嗎?
……
請讀本書。
它會讓你看到一個真正的周揚。
你想知道周揚對魯迅、胡風忌恨的程度?周揚堅決不肯與丁玲和解的深層原因?你想知道周揚向病危的馮雪峰懺悔的真情?你想瞭解周揚在魯藝領導「搶救運動」中怎樣把大批無辜者打成特務?又怎麼要狠整蕭軍把他打成日本特務?你想瞭解周揚與江青過招的喜劇嗎?本書讓你看到一個標準形象後面的周揚。
作者簡介:
葉德浴,一九二○年生,浙江杭州人。退休前為大連大學中文系教授。出版專著有:《走向魯迅世界》《七月派:新文學的驕傲》《難忘的一九五五》等。
章節試閱
「周揚」這個名字的含義
周揚在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壇的時候,用的名字是周起應。一九三四年秋突然棄周起應之名改用「周揚」這個名字。魯迅曾就周起應改名周揚的含義作過一番猜測,認為這表現了周起應要立大志,在文學上做出一番大事業。但他並不以為他的猜測是符合實際的。
一九九八年,譚林通的一篇紀念周揚的文章,才讓人們瞭解到事情的真相:
我認識周揚,是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間在東京小石川區林町的「國師館」,當時他二十一歲,我是初中剛畢業的十六歲少年,那時他叫周起應。他是在與蘇靈揚結合之後,作為一種紀念吧,才開始用「周揚...
周揚在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壇的時候,用的名字是周起應。一九三四年秋突然棄周起應之名改用「周揚」這個名字。魯迅曾就周起應改名周揚的含義作過一番猜測,認為這表現了周起應要立大志,在文學上做出一番大事業。但他並不以為他的猜測是符合實際的。
一九九八年,譚林通的一篇紀念周揚的文章,才讓人們瞭解到事情的真相:
我認識周揚,是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間在東京小石川區林町的「國師館」,當時他二十一歲,我是初中剛畢業的十六歲少年,那時他叫周起應。他是在與蘇靈揚結合之後,作為一種紀念吧,才開始用「周揚...
»看全部
目錄
「周揚」這個名字的含義
周揚翻譯《安娜‧卡列尼娜》
周揚緣何讀不懂艾青的詩
周揚評《臘月二十一》
周揚在魯藝的「搶救運動」中
周揚為什麼放過這個「日本特務」
周揚對東平的狂熱痛恨
周揚的一篇官架十足的《前記》
周揚一九五二批胡會上的總結發言
周揚與江青過招
周揚的「院士」桂冠
周揚「重新出版」《生活與美學》
周揚「仇魯情結」惡性大發作
周揚的探病「佳話」
周揚如此率先垂範「批判」「四人幫」
「周揚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周揚拒赴和解宴
周揚跟頭栽在茅公遺文上
周揚為什麼不向胡風表示歉意
周揚翻譯《安娜‧卡列尼娜》
周揚緣何讀不懂艾青的詩
周揚評《臘月二十一》
周揚在魯藝的「搶救運動」中
周揚為什麼放過這個「日本特務」
周揚對東平的狂熱痛恨
周揚的一篇官架十足的《前記》
周揚一九五二批胡會上的總結發言
周揚與江青過招
周揚的「院士」桂冠
周揚「重新出版」《生活與美學》
周揚「仇魯情結」惡性大發作
周揚的探病「佳話」
周揚如此率先垂範「批判」「四人幫」
「周揚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周揚拒赴和解宴
周揚跟頭栽在茅公遺文上
周揚為什麼不向胡風表示歉意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葉德浴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3-07-30 ISBN/ISSN:978986591578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0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政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