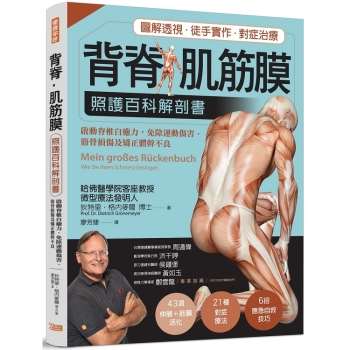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大飢餓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45 |
華文創作 |
$ 308 |
小說 |
$ 308 |
小說 |
$ 315 |
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 315 |
中文現代文學 |
電子書 |
$ 350 |
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大飢餓
本書為長篇小說,描寫中國1958年左右開始在全國推動的「大躍進」的不堪現實,以及那段悲涼而辛酸的歷史。在乾旱的杜家堡,人們大煉鋼鐵、引水上山,虛報浮誇產量的後果,便是隨之而來的「大飢餓」──從一開始的挖草根、堀土為食,到最後的人吃人,如同一場荒謬而可笑的鬧劇,卻是真實發生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