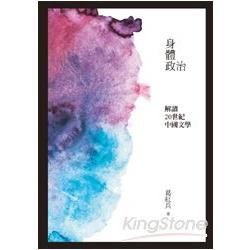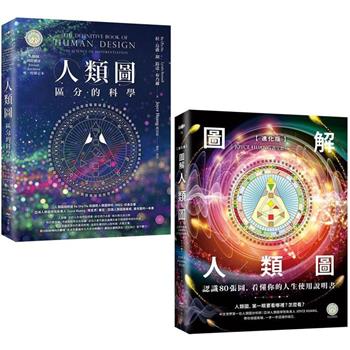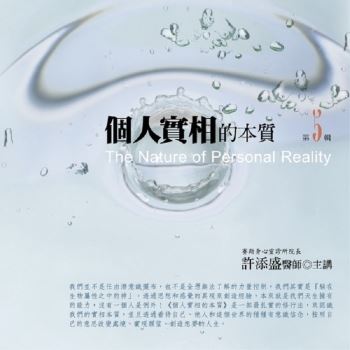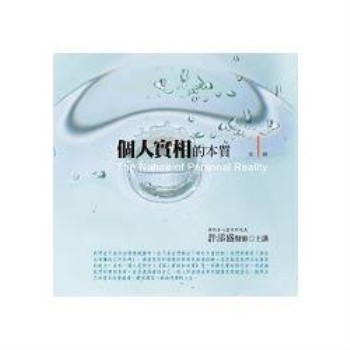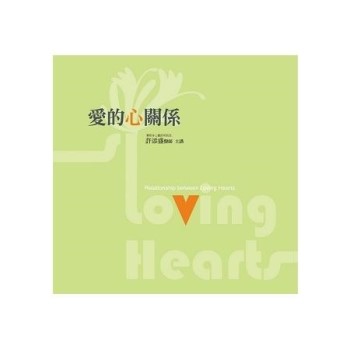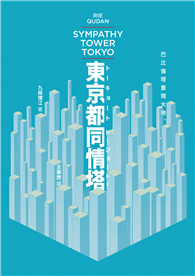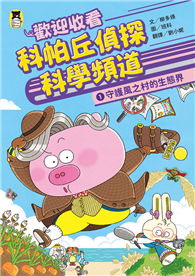序
身體倫理學:一個信念
身體倫理學的建立就是要恢復身體對於倫理學的奠基。存在就是身體,對於人來說身體性存在是第一位的,任何真正的自我言說必然是以身體性為依據的言說,靈魂的語言已經過多地被「公共信念」玷污和壓抑,今天要對壓抑性公共信念進行拆解,真正地傳達個體性體驗在倫理學中的應有的聲音,依據唯有一個,那就是我們的身體性存在。但是這簡單的真理,卻被迄今為止多數的倫理學家遮蔽了。他們殺死了身心一體的原始地安妥於世的人,建立了人的身心二分法,人的身體以一種匍匐的姿態莫名地承擔著這樣或那樣的骯髒與罪惡,而虛幻的想像的靈魂卻高高在上地站立了起來,被賦予了上帝、群集、集團等等名目,代表了正義、道德、良知。自古希臘以來人類道德的主導原則幾乎都是:愛絕對者(愛絕對主體或超級主體天神、聖人、領袖,遵從他們的意志),愛大全(愛群集、集團,將其意志當成自己的意志),愛(超越於自體的善)而無限地鄙視身體。這些原則看起來似乎絕對高尚,而實際並不如此,因為神、大全、超越之善並不顯身於世界,因而愛的原則最終就只能落實於它們在這個世界的代言人:地上的聖、神。在這裡人的身∕心二分法透過神秘的神∕人二分法、大全∕個體二分法、超越善∕自體善二分法的轉化進而發展為現世主義的聖∕俗二分法,並在結果上落實為現實世界的人在主體地位上的(超級主體與一般主體)的等級制度。
總的說來:一、傳統道德理念以人的身-心二分法為前提,它導致人的身心割裂,使人無法達成身心的一致和統一,是以心、理性、靈魂來壓抑身、感性、肉體,它是禁欲主義的、非行動的、反身體的、使人的肉體死亡的。尤其在中國,儒家的對於身體的蔑視(「捨身取義」、「殺身成仁」)是一以貫之的,中國歷史的源頭沒有像古希臘的伊壁鳩魯那樣的崇尚身體、感性的反對派倫理學家,又沒有經歷尼采那種非道德主義哲學的衝擊,所以中國的反身體、敵視感性、感官,視肉體為仇寇的道德主義觀念一直延續了幾千年,中國人在長達幾千年的過程中一直受著這些可恥的道德主義者的愚弄和欺騙,以至中華民族看起來似乎是先天就反身體的,不重視身體鍛煉、缺乏戶外體育活動的興趣,對身體的快感持之你比嗤之以鼻─對身體蔑視得太久了,幾千年的結果人們獲得了一種種族上的身體的頹敗形式,傳統的道德理念應該為這種身體素質的普遍虛弱、體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退化負責。二、人的身心二分法發展為大全與個人的二分法導致「大全」對「個人」的奴役。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它特定的墮落,而我們這個時代在倫理學上的特定墮落絕對不是享樂主義和淫靡作風,而是人們對於個人、個體、個性的蔑視。
我們已經到了蔑視個人卻不以為不道德的地步。如果我們承認人道主義的精髓在於對個體的人的自我選擇和決斷的權力的肯定,那麼我們會清楚地發現傳統的公共信念作為道德理念是多麼地反人道主義,它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消滅個體:自由自覺自主的個體,而代之以無個性無決斷的「群眾」,其結果是使無數個體放棄個體自主沒入公共信念之中。身體倫理學奠基於自體就是要在這方面和傳統道德理念對立,它不試圖代替其他個體作出道德判斷,不試圖為其他個體提供一套普遍有效的道德規範,它也不試圖告訴別人道德選擇應該是怎樣的。它將說明的是個體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真正個體和虛假個體之間的區別,呼喚個體自覺自主,呼喚真正的個體道德時代的來臨。
因而身體倫理學是一種反對身心二分法的以身心一體為基礎的新的倫理學:身體中心的倫理學,它呼喚一種嶄新的身體道德。這種道德將依持「人」的感覺而不是依靠神的意志,依靠「人」的自我意識而不是依靠外在的超越主體的威權,堅持身體的人作為唯一的道德主體(道德承擔者)的地位,堅信善就存在於我們的身體性存在之中,它不是超越於身體的「靈魂」的特權,不是「神意」的結果,道德內在於人的身體性存在,沒有超越於身體之外的善。如果人本善,那就是說人作為身體性存在本善。人不僅是身體的人還是個體的人,身體倫理學倫理學的中心基點是人類的道德實體是個人,而且是身體的作為行為主體以及結果的個人。離開了地獄與天堂的懲戒與誘惑,離開了神意以及社會大全,只剩下個體的人,這時道德的出發點就只有立足於自我意識和感覺的道德領受的個體的人。無數的平等的個體的人互相制約的社會關係構成了社會大全的善,因而社會整體的善並不神秘,它只是指無數個體身體中心的以互相制約為基礎的道德領受,並不需要什麼「聖人」的教化、領袖的威權、上帝的授意,總之並不需要一個絕對主體或超越物(靈魂)作為「善」的源泉。身體倫理學要求建構一個後上帝、後聖人的道德精神、「只有諸神,沒有上帝」的道德主義,強調人在規範倫理學道德教條面前的主體地位,強調個人對於公共信念的否定權和認同權一致,主張個體對公共信念的相對主義領受的合法性,它不是否定道德的共通與共同,但是它更清醒地認識到規範倫理學的歷史相對性,對於規範倫理學的保守性甚至反人道性具有更強烈的主體自覺和更主動的叛逆意識。自體中心的道德是將個體的身體的人的主體地位放在世俗的繼承性道德教條、公共信念的前面,這一點正好和規範倫理學的法則相反。
第一,身體倫理學將人視為自體, 一種雙重之實體(Doppelwesen),「我」是作為一個身體出現在倫理關係之中,身體倫理學對於人的靈魂性進行了懸擱。古往今來,對於人的解釋無非有三種,一種是將人作為純粹的自然物,一種是將人作為自然物身體和靈魂的結合,一種是將人看作是純粹的靈魂。
現在身體倫理學的方法是將人的本原作如下懸擱:對人的靈魂存而不論,而將人看成是純粹身體。對於身體倫理學視域來說,倫理學主體的生就是身體的誕生,死亡也是身體的死亡,身體是自在本體,身體不存在作為身體倫理學主體的人也就死了,身體倫理學在這裡對人的靈魂存而不論,這就把心靈的靈魂的反思的思的方面排斥在倫理學視域之外。
第二,身體的感性的自由,肯定人的軀體感受(快樂和痛苦)的倫理學意義,就是對人的感性而不僅僅是人的理性的自由作出了新的承諾。
第三,把人看作個人的觀點意味著「我」對於「我」的責任優先而不是像傳統倫理學那樣把「我」對於「他」的責任視為優先,這是一種提升:將人提升為「個人」。是以身體倫理學中不存在人的非我的目的論的問題,因為單純個體不能作為外在於其自身的合目的性來理解。在實踐倫理學中,首要的媒介就是人的客體化,「他人」被視為「有用」─一種物的特性,在這裡他人的善(實踐倫理學意義上的)是被作為可上手性來理解的,而在身體倫理學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以人的客體化而是以人的主體化為媒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以具體的善來加以規定而是以抽象的終極的善也即無數的「我」是無數的「他」成為主體的前提的意義上來被認識的。我的主體地位是他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人的充分的主體化是身體倫理學的媒介,在實踐倫理學中只有主體的物化,對於另一個主體來說成為有用的才是善的,這裡包含著「為他」的目的論,主體不以自身為目的。而在身體倫理學中主體只有充分主體化才能使自己成為對方的主體化的可能性,才是善的,因而首先表現為一種唯我的目的論,自體以自身的自體化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