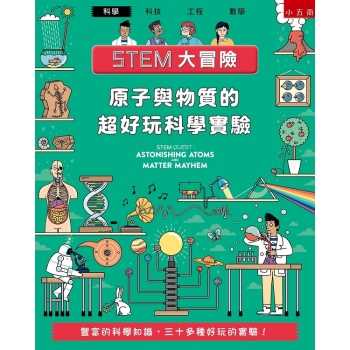以所羅門的名義,而留傳的箴言和詩篇,想來都是假藉的。喬托、但丁、培根、麥爾維爾、馬克.吐溫,相繼追索了所羅門,於是愈加迷離惝恍,難為舉證。最後令人羡慕的是他有一條魔毯,坐著飛來飛去--比之箴言和詩篇,那當然是魔毯好,如果將他人的「文」句,醍醐事之,凝結為「詩」句,從魔毯上揮灑下來,豈非更其樂得什麼似的。
每日向晚遙觀紅日緩緩沉下平線
悲壯無言,生命如浪花,而我還活著
我是兩度海灘的倖存者,深明海的啟示
愛海要在陸地上愛,登高山,瞭望大海
愛人亦然,萬全處,方可率性狂戀--摘自〈與米什萊談海〉
《偽所羅門書--不期然而然的個人成長史》,可說是木心半個世紀廣闊的成長史,他擷取世界文學大師的文句、意象,種種瞬間片段,構造無以倫比的紙上奇美旅程,成此書。
全書多以地名:黎巴嫩、匈牙利、開羅、瑞士、黑海、在保加利亞;或人名:艾倫、屠格涅夫;或物名,汗斯酒店、兩瓶敏托夫卡、六百萬馬克,此三類為篇名,關乎人生的篇章較少。這是木心尋著成長的軌跡,一點點回到過去的「點」,又從「點」擴大到具體的「面」,沒有太多關於自己的筆墨,沒有人與事的評論,卻是一個個具體的事件,流連光景惜朱顏,盡情滿足感官之欲,千迴百轉,交織出一幅幅旖旎風光。風雅、幽默、多情的異國風情,貪婪地走進他的生命。
作者簡介
木心
本名孫璞,字仰中,1927年2月14日生於浙江烏鎮,自幼迷戀繪畫與寫作。十五歲離開烏鎮,赴杭州求學,1946年進入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學習油畫,不久師從林風眠門下,入「杭州國立藝專」繼續探討中西繪畫,直到十九歲離開杭州去上海。五○至七○年代,任職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參與人民大會堂設計。畫餘寫作詩、小說、劇作、散文、隨筆、雜記、文論,自訂二十二冊,「文革」初期全部抄沒。「文革」中期被監禁期間,祕密寫作,成獄中手稿六十六頁。1982年遠赴紐約,重續文學生涯。1986至1999年,台灣陸續出版木心文集共12種。1989至1994年,為旅居紐約的文藝愛好者開講「世界文學史」,為期六年,陳丹青為其學生。2003年,木心個人畫展在耶魯大學美術館、紐約亞洲協會、檀香山藝術博物館巡迴,畫作受大英博物館收藏,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家中第一位作品被該館收藏,2006年,木心文學系列首度在大陸出版,同年,應故鄉烏鎮邀請,回國定居,時年七十九歲。年底,紐約獨立電影製片導演赴烏鎮為其錄製紀錄片。2011年12月21日凌晨三時,在故鄉烏鎮逝世,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