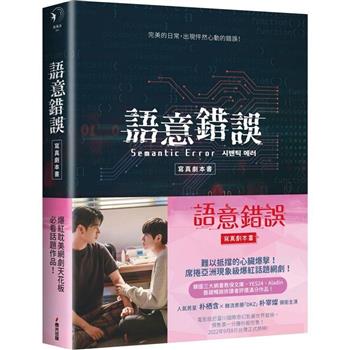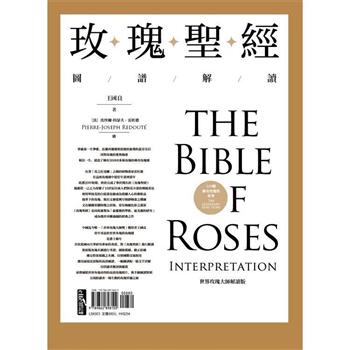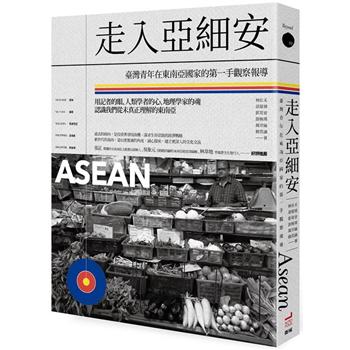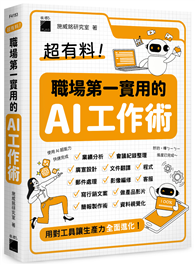「分身」、「化身」似乎是我的一種欲望,與「自戀」成為相反的趨極。明知不宜作演員,我便以寫小說(其實屬於敘事性散文),用「第一人稱」療慰、來滿足「分身欲」、「化身欲」,寬解對天然「本身」的厭惡。
離別,走的那個因為忙於應付新遭遇,接納新印象,不及多想,而送別的那個,仍在原地,明顯感到少一個人了,所以處處觸發冷寂的酸楚──我經識了無數次「送別」後才認為送別者更淒涼。 ──摘自〈此岸的克利斯朵夫〉
《溫莎墓園日記》是木心的小說選集。木心曾說,他的短篇小說可說是一種敘事性散文,就像音樂上的敘事曲。
本書取材駁雜,型態多變,時不論古今,地不分中外。有典型的故事新編,寓有人心不古的感慨;在生活廣度以及人性深度等方面多所探索,分別表現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與輕;牽涉到對於愛情的種種想法跟記憶;悼亡生命中幾位友朋行過的感懷述事。
《溫莎墓園日記》敘事平緩,不追求情節上的起伏,而變成淡淡散散的,像散文般的格局鋪展開去。寫著月淡如水的故事,沒有衝突,沒有煽情,充溢著一灣泓水,淡定如神,卻寫出了一個靈動的世界,用透澈而節制的筆調,描繪出人生的無奈、情愫、重聚、別離與生死。
作者簡介:
木心,本名孫璞,字仰中,1927年2月14日生於浙江烏鎮,自幼迷戀繪畫與寫作。十五歲離開烏鎮,赴杭州求學,1946年進入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學習油畫,不久師從林風眠門下,入「杭州國立藝專」繼續探討中西繪畫,直到十九歲離開杭州去上海。五○至七○年代,任職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參與人民大會堂設計。畫餘寫作詩、小說、劇作、散文、隨筆、雜記、文論,自訂二十二冊,「文革」初期全部抄沒。「文革」中期被監禁期間,祕密寫作,成獄中手稿六十六頁。
1982年遠赴紐約,重續文學生涯。1986至1999年,台灣陸續出版木心文集共12種。1989至1994年,為旅居紐約的文藝愛好者開講「世界文學史」,為期六年,陳丹青為其學生。2003年,木心個人畫展在耶魯大學美術館、紐約亞洲協會、檀香山藝術博物館巡迴,畫作受大英博物館收藏,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家中第一位作品被該館收藏,2006年,木心文學系列首度在大陸出版,同年,應故鄉烏鎮邀請,回國定居,時年七十九歲。年底,紐約獨立電影製片導演赴烏鎮為其錄製紀錄片。2011年12月21日凌晨三時,在故鄉烏鎮逝世,享年84歲。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我們時代惟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與五四傳統的文學作者。
木心是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他的小說很早就碰觸西方現代小說常探討的議題,包括辜負、遺憾、懺悔及追憶,也討論人如何站在現代荒原中,仍能保持文明人的尊嚴。──駱以軍
我所迷戀的是木心以及他這代人的語言方式,通透、溫厚、潑辣,大道理講得具體生動,充滿細節和比喻,一針見血,絲毫沒有空話套話,沒有學術腔。──陳丹青
木心的文字雖多玄思冥想幽默機智,而我認為,在氣質上,寧是傾向於地中海精神脈絡的。木心是講求密度的詩人,在這方面,他比我所見的任何人都要做得多、做得懇切。──楊澤
他的作品中有一種雍容,和一種恬淡,這不是表面的,而是面臨生活中苦難的消融和制服,也就可以說是「中古精神」。──林泠
「人有兩套傳統,一套精神,一套肉體。我的祖先在紹興,我能講一口紹興話。我的精神傳統在古希臘,在意大利,在達文西。所以我說我是紹興希臘人。」──木心
名人推薦:我們時代惟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與五四傳統的文學作者。
木心是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他的小說很早就碰觸西方現代小說常探討的議題,包括辜負、遺憾、懺悔及追憶,也討論人如何站在現代荒原中,仍能保持文明人的尊嚴。──駱以軍
我所迷戀的是木心以及他這代人的語言方式,通透、溫厚、潑辣,大道理講得具體生動,充滿細節和比喻,一針見血,絲毫沒有空話套話,沒有學術腔。──陳丹青
木心的文字雖多玄思冥想幽默機智,而我認為,在氣質上,寧是傾向於地中海精神脈絡的。木心是講求密度的詩人,在這方面,他比我所見的...
章節試閱
一車十八人
我們研究所備有二輛車,吉普、中型巴士。司機卻只有李山一個。
李山已經開了三年車,前兩年是個嘻哩哈啦的小伙子,這一年來沒有聲音了,常見他鑽在車子裡瞌睡,同事間無人理會他的變化,我向他學過開車,不由得從旁略為打聽,知是婚後家庭不和睦─這是老戲,戀愛而成夫妻,實際生活使人的本性暴露無遺,兩塊毛石頭摩擦到稜角全消,然後平平庸庸過日子,白頭偕老者無非是這齣戲。我拍拍李山的肩:「愁什麼,會好起來的,時間,忍耐一段時間,就好了。」他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曖昧,似乎是感激我的同情,似乎是認為我的話文不對題。
我漸漸發現《紅樓夢》之所以偉大,除了已為人評說的多重價值之外,還有一層妙諦,那就是,凡有一二百人日常相處的團體,裡面就有紅樓夢式的結構。我們這個小研究所,成員一百有餘兩百不足,表面上平安昌盛,骨子裡分崩離析,不是冤家不聚頭,人人眼中有一大把釘,這種看不清摸不到邊際、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況,一直生化不已。於是個個都是角色,天天在演戲,損人利己,不利己亦損人,因為利己的快樂不是時時可得,那麼損人的快樂是時時可以得來全不費工夫的。
有時我歎苦,愛我的人勸道:「那就換個地方吧。」我問:「你那邊怎麼樣?」「差不多,還不如你研究所人少些。」我笑道:「你調到我這邊來,我調到你那邊去。」─我已五次更換職業,經歷了五場紅樓夢,這第六場應該安命。
夏季某日上午,要去參加什麼討論會,十七個男人坐在中型巴士裡等司機來,滿車廂的喧嘩,不時有人上下、吃喝、便溺……半小時過去,各人的私事私話似乎完了,一致轉向當務之急─李山呢,昨天就知道今天送我們去開會的,即使他立刻出現,我們也要遲到了。
李山就是不來。
我會開車,但沒有駕駛執照,何況這是一段山路,何況我已五次經歷紅樓夢,才不願自告奮勇充焦大呢。
李山還是不來。
三三兩兩下車,找所長,病假。副所長,出差。回辦公室沖茶抽菸,只當沒有討論會這回事。
李山來了─大伙兒棄菸丟茶,紛然登車,七嘴八舌罵得車廂要炸了似的。
「十七個等你一個,又不是所長,車夫神氣什麼,也學會了作威作福。」
「瞧他走來時慢吞吞的那副德性,倒像是我們活該,李山,你知不知道你是吃什麼的!」
「我們給車錢,加小費,李山你說一聲,每人多少─你罷工,怎麼不堅持下去,今天不要上班嘛,堅持兩星期就有名堂了。」
「記錯了,當是新婚之夜了,早晨怎捨得下床,好容易才擘開來的。」
「半夜裡老婆生了個娃娃,難產,李山,你是等孩子出了娘胎才趕來的吧?」
「我看是老婆跟人跑了,快,開車,兩百碼,大伙兒幫你活活逮住這婆娘,逮雙的。」
李山一聲不響。自從我向他學開車以來,習慣坐在他旁邊的位子上。那些油嘴滑舌的傢伙盡說個沒完,我喊道:
「各人有各人的事,難得遲到一回,嚷嚷什麼,好意思?」
「難得,真是難得的人才哪,誰叫我們自己不會開車,會開的又不幫李山的忙,倒來做好人了。」
竟然把我罵了進去。這些人拿此題目來解車途的寂寞,也因為平時都曾有求於李山,搬家、運貨、婚事喪事、假日遊覽……私底下都請李山悄悄地動用車輛,一年前這個嘻哩哈啦的小伙子肯冒風險,出奇兵,為民造福。近年來他概不理睬,大家忘了前恩記了新怨,今日裡趁機挖苦一番,反正今後李山也不會再有利可用,李山是個廢物,只剩拋擲取樂的價值。
「話說回來,不光臉蛋漂亮,身材也夠味兒,李山眼力不錯,福份不小,該叫你老婆等在半路,我這麼攔腰一把,不就抱上車來了麼,夏天衣裳少,欣賞欣賞,蜜月旅行。」
「結婚一年了,老夫老妻,蜜什麼月。」
「我是說我哪,他老婆跟我蜜月旅行,老公開車,份內之事。」
哄車大笑。
「女人呀,女人就是車,男人就是司機,我看李山只會駕駛鐵皮的車,駕駛不了肉皮的車。」
「早就給敲了玻璃開了車門了。」
哄車大笑。
十六個男子漢像在討論會中輪流發言,人人都要賣弄一番肚才口才。我側視李山,他臉色平靜,涵量氣度真是夠的。
「閉上你們的嘴好不好,不准與司機談話,說說你們自家的吧,都是聖母娘娘,貞節牌坊。李家有事沒事,管你們什麼事?」
一個急煞車,李山轉臉瞪著我厲聲說:
「我家有事沒事管你什麼事?」
我一呆:
「我幾時管了?」
「由他們去說,不用你嚕囌。」
他下車,疾步竄過車頭,猛開我一側的車門,將我拉了出來。
「你倒怪我了?」我氣忿懊惱之極!
李山一躍進座,碰上門,我扳住窗沿,只見他鬆煞車,踩油門突然俯身揮拳打掉我緊攀窗沿的手,又當胸狠推了一把─我仰面倒地,車子一偏,加速開走了。
「李山,李山……」我倉惶大叫。
巴士如脫弦之箭─眼睜睜看它衝出馬路,凌空作拋物線墜下深谷,一陣巨響,鳥雀紛飛……
我嚇昏了,我也明白了。
心裡一片空,只覺得路面的陽光亮得刺眼。
好久好久,才聽到鳥雀吱唧,風吹樹葉。
踉蹌走到懸崖之邊,叢藪密密的深谷,沒有車影人影,什麼也沒有。
……
不能說那十六個男人咎由自取。我要了解那天李山遲來上班的原因─能聽到的是他妻子做了對不起李山的事,不是一樁一件,而是許許多多,誰也說不明說不盡,只有李山自己清楚。
夏明珠
在我父親的壯年時代,已婚的富家男主,若有一個外室,輿論上認為是「本分」的。何況世傳的邸宅坐落於偏僻的古鎮,父親經營的實業,卻遠在繁華的十里洋場;母親、姊姊、我,守著故園,父親一人在大都市中與工商同行周旋競爭,也確是需要有個生活上社交上的得力內助,是故母親早知夏明珠女士與父親同居多年,卻從不過問,只是不許父親在她面前作為一件韻事談。
寒假,古鎮的雪,廟會的戲文,在母親的身邊過年多快樂。暑假,我和姊姊乘輪船,搭火車,來到十里洋場,父親把我們安頓在他作為董事長的豪華大旅館中。姊姊非常機靈,而且勇敢,摸熟了旅館附近的環境後,帶著我,不斷地擴大遊樂的範圍。旅館中上自經理下至僕歐,悉心照料衛護姊弟二人,任何東西開口即得,就怕我們不開口。父親似乎知道不會失事出事,他也沒有餘暇來管束我們,倒是夏女士,時常開車來接我們去她的別墅共餐,問這問那,說到融洽處,要我們叫她「二媽」,我和姊姊笑而不語了─母親並沒有叮囑什麼,是我們自己不願如此稱呼。她的西方型的美貌、瀟灑的舉止、和藹周緻的款待,都使人心折,但我們只有一個母親,沒有第二個。而且她一點也不像個母親,像朵花,我和姊姊背地裡叫她「交際花」,吐吐舌頭,似乎這是不應該說出聲來的。姊姊告訴我夏女士是「兩江體專」高材生,「高材生」我懂,就是前三名,總平均九十分以上的。「兩江體專」是什麼?只在故事裡聽見過「兩江總督」。姊姊說,浙江江蘇兩省聯名合辦的體育專科學校,夏女士是游泳明星、網球健將。我聽了,不禁升起了敬意,可是這敬意又被夏女士的另一稱號所沖淡:姊姊說旅館斜對面不是有一家很大很大的理髮廳嗎,夏女士,她就是「白玫瑰理髮廳」的老闆娘,「老闆娘」,我討厭。所以每見夏女士,便暗中癡癡忖度,她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哪些是「老闆娘」,哪些是「運動健將」,愈辨愈糊塗,受夠了迷惘的苦楚。姊姊說,管她呢,反正我吃她給我的五香鴨肫肝,穿她給我的喬奇紗裙子,還不是爸爸的錢。我也吃鴨肫肝,我穿背帶褲,白麂皮高統靴,還不是爸爸的錢。(那是夏女士陪我們去挑選的,定製的,如果我們自己去,店家哪會這樣殷勤,兩次三次試樣,送到旅館裡來。)奇怪的是,一進店,她就說:「你喜歡這種皮靴,是嗎?」我高興地反問:「您怎會知道?」「很神氣,像個小軍官。」我非常佩服了,她與我想的一樣。姊姊的心意也被猜中,她是小小舞蹈家,薄紗的舞衣,一件一件又一件,簡直是變魔術,使我自怨不是女孩子,因此我走起路來把靴跟敲得特別響,我不能軟軟的舞,在路上,那是我神氣得多了。
假期盡頭,父親給我們一大批文具、玩具、糖果、餅乾,還有一箱給媽媽的禮物,說:
「對不起,我一直沒有陪你們玩,怎麼樣,過得好不好?」
「還不錯。」我答。
「什麼叫還不錯?」
「還可以。」我解釋。
「不肯說個好字麼?」
「還好。」我說。
姊姊接口道:
「很好,我和弟弟一直很快樂。」
爸爸吸雪茄,坐下:
「回去媽媽問起來,你們才該說『還好』,懂嗎?」
「我們知道的。」姊姊回答了,我就點點頭。
爸爸把我拉到他胸口,親親我,低聲:
「你生我的氣,所以我喜歡你。」
歸途的火車輪船中,我們商量了:媽媽一定會問的,哪些該講,哪些就不講,賽馬、跑狗、溜冰、卓別林、海京伯─講;別墅裡的水晶吊燈、銀臺面、夏女士唱歌、彈琴、金剛鑽項鍊─不講;波斯地毯、英國笨鐘、撒尿的大理石小孩,也不講,理髮廳?媽媽來時也住這旅館,也會到那裡理髮廳去,可是媽媽不會問「你們老闆娘是誰」,我同意姊姊的判斷。兩個孩子雖然不懂道德、權謀、卻憑著本能:既要做母親的忠臣,又不做父親的叛徒。
到家後,晚上母親開箱,我和姊姊都驚歎怎麼一只箱子可以裝那麼多的東西,看媽媽試穿衣服最開心。我心裡忽一閃,是夏女士買的;還有整套的化妝品,像是外科醫生用的。另外,一瓶雀斑霜,我問:「媽媽你臉上沒有雀斑呀?」
母親伸給我一隻手:
「喏,也奇怪,怎麼手背上有雀斑了,最近我才發現的呵。」
孩子的概念是:暑假年年有,爸爸年年歡迎我們去,媽媽年年等著我們回,一切像客堂裡的橢圓紅木桌,天長地久,就這樣下去下去。哪知青天霹靂,父親突然病故,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一年。從此家道中落,後來在顛沛流離的戰亂中,母親常自言自語:
「也好,先走了一步,免受這種逃難的苦。」
父親新喪不久,夏女士回到這古老的鎮上來了─她原是本地人,父母早亡,有三個兄弟,都一無產業二無職業,卻衣履光鮮,風度翩翩。鎮上人都認為是個謎,謎底必然是罪惡的。夏明珠綽號「夜明珠」,這次回鄉,自然成了新聞,說是夜明珠被敲碎了,亮不起來哉。
我父親亡故後,她厄運陡起,得罪洋場的一個天字號女大亨,霎時四面楚歌,憋不過,敗陣回歸。從傢具、鋼琴也運來這點看,她準備長住─像她那樣風月場中金枝玉葉的人,古鎮與她不配。她也早為古鎮的正經人所詬誶謠諑,認為她有辱名城。所以,據說夏明珠確是深居簡出,形如掩臉的人。當時消息傳入我家,母親輕輕說了句:
「活該。」
母親不以為夏明珠會看破紅塵,而是咎由自取,落得個慘澹的下場,抬不起頭來。
夏女士幾次托人來向我母親懇求,希望歸順到我家,並說她為我父親生下一女,至少這孩子姓我們的姓。母親賙濟了錢物,那兩個請願,始終是凜然回絕的。有一次受夏女士之托的說客言語失當,激怒了母親,以致說出酷烈的話:
「她要上我家的門,前腳進來打斷她的前腳,後腳進來打斷她的後腳。」
我在旁聽了也感到寒慄,此話不僅詞意決絕,而且把夏女士指為非人之物了。
說客狼狽而去,母親對姊姊和我解釋:
「我看出你們心裡在可憐她,怪我說得粗鄙了。你們年紀小,想不到如果她帶了孩子過門來,她本人,或許是老了,能守婦道像個人,女孩呢,做你們妹妹也是好的。可是夏家的三兄弟是什麼腳色,三個流氓出入我家,以舅爺自居,我活著也難對付,我死了你姊弟二人將落到什麼地步。今天的說客,還不是三兄弟派來的,我可只能罵她哪。」
我的自私,自衛本能,加上我所知的那三兄弟奇譎的惡名,聽了母親這段話,彷彿看到了三隻餓鷹撲向兩隻小雞,母雞毛羽張豎,奮起搏鬥─我不怪詩禮傳家的母親的忽然惡語向人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轉輾避難,居無定所。苦苦想念故園,母親決定帶我們潛回老家,住幾天,再作道理,心意是倘若住得下來,就寧願多花點代價擔點風險,實在不願再在外受流離之苦了。
當時古鎮淪於日本法西斯軍人之手,局面由所謂「維持會」支撐著。我們夤夜進門,躲在樓上,不為外人所知,只有極少幾個至親好友,祕密約定,上樓來一敘鄉情。入夜重門緊鎖,我和姊姊才敢放聲言笑,作整個邸宅的舊地重遊,比十里洋場還好玩,甚而大著膽子闖進後花園,亭臺樓閣,假山池塘,有明月之光,對於我們來說,與白晝無異。實在太快樂,應該請母親來分享。
暢遊歸樓,汗涔涔氣喘喘,向母親描述久別後的花園是如何如何的好,媽媽面露笑容,說:
「倒像是偷逛了御花園了,明夜我也去,帶點酒菜,賞月。」
洗沐完畢,看見桌上擺著《全唐詩》,母親教我們吟誦杜甫的五言七言,為了使母親不孤獨,我們皺起眉頭,裝出很受感動的樣子。母親看了我們幾眼,把詩集收起,捧來點心盒子─又吃到故鄉特產琴酥、姑嫂餅了,那是比杜甫的詩容易體味的。
這一時期,管家陸先生心事重重,早起晏睡,門鈴響,他便帶著四名男僕,親自前去問答。如果他要外出辦事,了解社會動態,他總是準時回返,萬一必須延遲,則派人趕回說明,怕母親急壞了。
自從夏末潛歸,總算偷享了故園秋色,不覺天寒歲闌,連日大雪紛飛。姊姊病了,我一人更索然無緒,槍聲炮聲不斷,往時過新年的景象一點也沒有,呆坐在姊姊的床邊,聽她急促的呼吸,我也生病躺倒算了。
一日午後,陸先生躡上樓梯,向我招招手,我悄然逸出房門,隨他下樓─夏明珠死了!怎麼會呢?陸先生目光避開,側著頭:
「我要向你母親說。」
「不行,你詳細告訴我,我知道該怎麼說。」
「應該我來說,而且還有事要商量。你上去,等你母親午睡起身,盥洗飲茶過後,你到窗口來,我等在天井的花壇旁邊。」
我上樓,母親已在盥洗室,等她一出,我便說陸先生有事要商談,母親以為仍舊是辦年貨送禮品的事,喃喃:「總得像個過年。」
我開窗走上陽臺,向兀立在雪中的陸先生揮手。陸先生滿肩雪花地快步上樓,一反往常的寒暄多禮,開口便說:
「昨天就知道夏明珠女士被日本憲兵隊抓去,起因是琴聲,說是法國馬賽曲,憲兵隊長一看到她,就懷疑是間諜,那翻譯纏夾不清,日本人故意用英語審問,她上當了,憑她一口流利的英語為自己辯護,加上她的相貌。服裝異乎尋常的歐化,日本人認定她是潛伏的英美間諜,嚴刑逼供。夜裡,更糟了,要污辱她,夏女士打了日本人一巴掌,那畜生拔刀砍掉了她的手,夏女士自知無望,大罵日本侵略中國,又是一刀,整隻臂膊劈下來……我找過三兄弟,都逃之夭夭……她的屍體,拋在雪地裡─我去看過了,現在是下午,等天黑,我想……」
我也去……陸先生想去收屍,要我母親作主,我心裡倏然決定,如果母親反對,我就跪下,如果無效,我就威脅她。
我直視母親的眼睛,她不迴避我的目光,清楚看到她眼裡淚水湧出─不必跪了,我錯了,怎會有企圖威脅她的一念。
母親鎮靜地取了手帕拭去淚水,吩咐道:
「請陸先生買棺成殮,能全屍最好,但事情要辦得快。你去定好棺材,天一黑,多帶幾個人,先探一探,不可莽撞,不能再出事了。」
我相信陸先生會料理妥善,他也急於奉命下樓,母親說:
「等著。」她折入房內,我以為是取錢,其實知道財務是由陸先生全權經理的。
母親捧來一件灰色的長大衣,一頂烏絨帽:
「用這個把她裹起來,頭髮塞進帽裡,墊衾和蓋衾去店家買,其他的,你見得多,照規矩辦就是。還有,不要停柩,隨即葬了,葬在我家祖墳地上,不要平埋,要墳墩,將來補個墓碑。」
當時姊姊病重,母親不許我告訴她,說:
「等你們能夠外出時,一同去上墳。」
夏女士殮葬既畢,母親要陸先生尋找那個希望作為我妹妹的女孩。
數日之後,回覆是:已被賣掉,下落不明。
一車十八人
我們研究所備有二輛車,吉普、中型巴士。司機卻只有李山一個。
李山已經開了三年車,前兩年是個嘻哩哈啦的小伙子,這一年來沒有聲音了,常見他鑽在車子裡瞌睡,同事間無人理會他的變化,我向他學過開車,不由得從旁略為打聽,知是婚後家庭不和睦─這是老戲,戀愛而成夫妻,實際生活使人的本性暴露無遺,兩塊毛石頭摩擦到稜角全消,然後平平庸庸過日子,白頭偕老者無非是這齣戲。我拍拍李山的肩:「愁什麼,會好起來的,時間,忍耐一段時間,就好了。」他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曖昧,似乎是感激我的同情,似乎是認為我的話文不...


 2014/11/17
201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