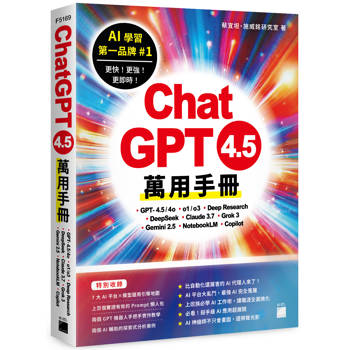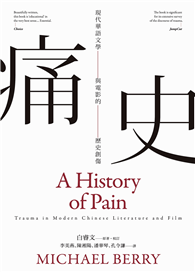只要「梗」在,就有花開
殘山剩水 人間百態 岩上無心雲相逐
22篇故事,寫人之初老,及其喜怒哀樂
年輕時,浦老喜歡看人、看劍、看花,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霸氣十足。
人到中年,開始看樹,春去秋來,林木森森,連成一片。
可是,這幾年,他從教書崗位退下來,看樹漸漸救他不了。
也許,看石頭的年紀到了。
小說家劉大任以極短的篇幅,凝煉生命轉瞬的攸長
——他向晚獨坐公園長椅,絲竹樂在耳畔奏起;他在深夜接起響鬧不停的電話,「他們決定拔管……」;他悉心呵護一株老梅,他從兒子公司剪回一枝喜林芋;他決定拜訪與前妻結婚的朋友,以及曾住了十年的舊址;她得知兒媳懷孕後成日哼著兒歌,他深信三個月大的女娃兒對他微笑;他與妻離婚只求留下貼梗海棠,她為幾十年不見的老同學辦起了年夜飯,他每日傍晚來此坐看白楊林,他在冬天的球場凝望一棵冬青樹,他以一畦菜圃見證貪嗔癡滅……
每個他∕她都在殘山剩水間尋求釋懷與坦然,每個故事裡都有一株植栽,靜靜立著,冒芽。
讀書∕練字∕打拳∕散步∕園藝∕弄孫∕訪友∕追憶∕送別
走過衝突與騷動的劉大任,曾以《浮遊群落》的熱血澎湃與《杜鵑啼血》的詭譎驚心震撼台灣文壇,集浪漫、現代與激進於一身,八0年代以降,他刻畫出一個個血氣旺盛的人物。人到中年,四十多歲時,他以《晚風習習》追憶父親,與人和解,將對文化的觀照、旅居國外的經驗內化為《憂樂》、《晚晴》等七本散文集。《枯山水》則是作家接受並願意面對「老年」的歷程,雖然草木與水,一概排除,但可不一定是乾枯與寂滅,他說:「我生性比較喜歡陽光,可能因此膚淺,但,無論如何,我的『枯山水』,是不可能沒有陽光的。」
作者簡介
劉大任
台大哲學系畢業,早期參與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研究所。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一九七二年入聯合國祕書處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現專事寫作。著作包括小說《晚風細雨》、《殘照》、《羊齒》、《浮沉》、《浮遊群落》、《遠方有風雷》等,運動文學《強悍而美麗》、《果嶺春秋》等,園林寫作《園林內外》以及散文和評論《紐約眼》、《空望》、《冬之物語》、《月印萬川》、《晚晴》、《憂樂》、《閱世如看花》、《無夢時代》、《我的中國》、《赤道歸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