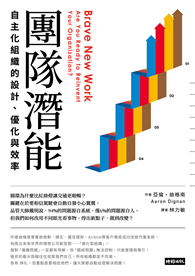櫻吹雪
東洋列島,新年伊始,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每個月忙忙碌碌都有花期。一月梅花,二月桃花,三月櫻花。這花是一種比一種開得嬌軟,桃花已失去了梅花的挺拔,櫻花更沒有桃花的翹首,簡直弱不禁風,一陣風過,就飄下一大片。然而賞花的事卻是越鬧越紅火。櫻花從南到北,從沖繩島到北海道,步步進軍,日本人用個很形象的詞——「櫻前線」。那不夾帶綠葉的櫻紅,野莽莽的,讓人們恍惚身處的不是人間,而是某個不可把握的地方。那些櫻樹下的飄蕩著的不陰不陽的日本小調,搖曳著的怪裏怪氣的舞姿,那些天當房、地當桌的人們,那些頭髮梳得精亮的男人和塗著厚厚脂粉的女人,那些洶湧的賞櫻人潮,都讓我們在感覺不可思議的同時,又有著隱隱的惶惑。果然,一場大雨就使得這一切銷聲匿跡了,宛若造物主將世界翻了個面。
提起日本的花,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櫻花。但日本的國花並不是櫻花,而是菊花,然而櫻花卻是象徵大和魂的。日本文化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物哀」,就是對物之易逝的傷感,一如對只開十多天的櫻花。在中國,也有「轉蓬之概」、「憂生之嗟」,比如晉人。但晉人由「哀」而轉狂狷,日本人則是由「哀」而沉湎。「哀」不是達到「不哀」的手段,「哀」本身就是目的。這似乎更符合「哀」的本質了,當我們哀傷的時候,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別人把我們拉出來,訴說,也只需要你傾聽,訴說本身就是目的。那種開導、勸導的企圖是令人討厭的。實際上,沉湎於「哀」,有一種「哀」的美,淒絕的美。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畫了不少樱花,最著名的一幅《花明り》,题作「明」,其實並不明,不是明艷,而是凄艷。
日語中有個美麗的詞,形容櫻花飄落——「櫻吹雪」。「美少女戰士」北川景子的一首歌,就叫《櫻吹雪》。據日本《廣辭苑》解釋,「櫻吹雪」就是櫻花的花瓣像雪花一樣紛亂飛舞。那年在東京上野公園,就看到了這種情景,夢幻一般,讓你分不清是雪紛紛從天上降落,還是花瓣紛紛飛上天離去;分不清是來,還是去;分不清是生,還是死。日本人把死看成是新旅程的開始,他們把死叫做「去天國」,我們中國雖然也有這種說法,但是我們是真的恐懼死的,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走這條不歸路的。但是日本人似乎不。2004年 10月 12日,一天之內,日本就有兩起集體自殺案件。富有意味的是,其中一個就發生在琦玉縣以觀賞櫻花聞名的美之內公園。四男三女共七個年輕人,租了一輛車,車內放了四個炭爐,燒炭自盡。他們還把車窗用膠帶密封,還在車外蓋一大片藍色帆布,顯示死意堅定。在日本,自殺不是個別現象,東京以西的靜岡縣的熱海,就是「情死聖地」。更不用說大量的作家藝術家,他們以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作品,三島由紀夫切腹,川端康成打開了瓦斯。川端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人生最絢爛時自殺的,有人用「人生最璀璨時,不忍見櫻花凋落、杜鵑悲鳴」來解釋死因。三島事件,看似因為「憂國」,但也難說沒有對自身生命的恐懼,不能忍受健美的身體終有老朽的一天,他要趁自己還沒有衰老,把精彩定格下來,讓其產生「刹那的永恆」。某種意義上說,與其日本人追求的是活得精彩,不如說追求死得漂亮。
從織田信長到三島由紀夫,到川端康成,太多的日本人像櫻花一樣在瞬間燦爛之後,慷慨赴死,以達永恆。燦爛,死亡;瞬間,永恆;乃至其中包含著的恥辱與光榮,這幾對意義完全相反的詞,在我們看來,無論如何也不能糅在一起,但在日本人的思維中統一了,在櫻花的品格中統一了。我甚至想,之所以不瞭解日本,是因為不瞭解櫻花。二戰期間,當盟軍艦隊遭遇日軍「神風特攻隊」自殺式撞擊,看著成群戰機櫻花般凋落,直墜在軍艦甲板上,他們怎麼也不能理解發生了什麼。是,發生了什麼了?在日本這民族身上發生了什麼?在日本人內心裏發生了什麼?這些彬彬有禮的日本人,這些愛花愛美的日本人,他們怎麼了?我們不明白日本文化有著兩面性:文雅而又暴躁,賞花落淚而又殺人不眨眼。
愛有期
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的小說《一年後》,講了一個奇特的愛情故事:女主人公惠理子失戀後,偶遇男子田村。但田村已有女友,他們就在田村女友去美國的一年期間,定下了愛情契約。她對田村說:僅僅是這一年,能和我戀愛嗎?
這毋寧是個殘酷的故事。這小說後來被搬上了銀幕,片名改成了《東京萬壽菊》。萬壽菊,是一種有很特別香味的菊花,但它只有一年的生命期。在這一年裏,開花,結果,然後凋謝,就像那場愛情。導演市川准闡述說:其實並不是每一場愛情都能天長地久的。確實,像萬壽菊那樣短暫地開放,然後迅速枯萎的愛情,在現代的社會隨處可見。
枯萎了沒問題,如果尚未枯萎,那怎麼辦?甚至愛還可能會越來越濃烈。人畢竟不是物,物租了一年,該歸還就歸還,人不行,人是有感情的。常聽一些人說不敢養狗,害怕養出感情來了,捨棄不掉。人是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要控制自己的感情,無異於揪著自己的頭髮要飛起來。那麼,怎麼能控制這愛只能到一年為止?
我常想,人最可怕的是想到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做什麼了。其實末日突然降臨,並不可怕,在你還沒感受到苦難的時候,苦難已經結束了。所以那些突然被奪去生命的人,還應該是幸運的,被車撞死,被突然飛來的東西砸死。相比之下,跳樓就比較殘酷了,從落下到著地,總有段時間。這一段時間怎麼辦?類似于「淩遲」,劊子手殺「二七烈士」林祥謙,一刀一刀切他的肉;曹禺《原野》裏的仇虎復仇,是把仇人的孫子殺了,讓仇人活著,活受煎熬。所以麻醉死亡是人道的,讓意識消失;所以拿槍自殺的人就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一扣扳機。我青春期時,老焦慮自己將來怎樣死,我總是必死的,可生命就像吹大了的氣球,要讓它消失,只能把它壓爆。為什麼會有氣球這比喻?因為我曾做過一個夢,夢中的自己就是一個氣球,它被吹得滿當當的,眼看要爆炸,我不知該怎麼辦。當然我可以解開紮口的線繩,但是我就是解不開,人是不可能解得開自己的結的,只能任它膨脹。它幾乎透明了,馬上要爆炸了,但是它還沒有爆炸,它只是用爆炸吊著我,漫長地等待爆炸,不可自拔地走向爆炸。可怕的不是它要爆炸,而是它走向爆炸的過程。
這不是《一年後》裏的事情,是另一個故事。他和她,三年前認識並且相愛。他們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之後,她必須離開他去她丈夫所在的城市,這是不可改變的。在這三年裏,他似乎忘記了這個事實,他覺得她就是他的,只有她去她丈夫那裏探親時,他才明白她不是他的,不能忍受。他不能忍受她和她丈夫在一起,不能忍受她丈夫姦污她,但是她丈夫有權利對她這樣,他是她的丈夫,那也不叫姦污,叫「同房」,甚至叫「做愛」。每次她去她丈夫那裏,殘酷的現實都會頓然擺在他面前,他都會痛苦不堪,像間歇性精神病發作,直到她回來,一切暫且平息。假像掩蓋了真相,她還會不會再走,姑且不管了,反正過一天算一天。但是現在,她要徹底離去了,徹底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了!已經定了離開的時間,餘下的每一天都得數著過了。過一天,就走向死亡一天,他清晰地看著死亡在一步步走近,他簡直崩潰——倒不如,把它給掐了!
據說古巴革命後,被判處死刑者可以有個最後的願望,許多人選擇了向行刑隊發出「開槍」的命令。既然不能把握生,那就把握死。迎向死亡,未嘗不是一種明智。當然最好是最初就死,不讓愛情發生。現代人有句話:不要愛,只要取暖。女主人公最後跟田村告別,她說,這一年過得真好!
日本人的表情
很早就聽說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這兩天才看到。先是《秋刀魚之味》,感覺並不好,生硬。也許跟大家的感覺大相徑庭。首先是色彩生硬,早期的彩色片,技術還不足以處理色彩的問題;還有表演上的生硬,好像是話劇,演員們好像總對著話筒念臺詞,至少是意識到要說給觀眾聽吧,總之是表演的感覺,不是真實的形態。
是不是當時演藝上的局限?但看幾乎同時期的黑澤明的電影,裏面的人物表演卻是很活絡的,給我們展現了有血有肉的日本人。但是小津電影中常用的演員,比如笠智眾,也是很好的演員。或者原因出在小津身上?據說小津是把演員當木偶一樣牽制的,這種牽制就像專制治國,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如果導演感覺失誤,那麼則無可避免地砸掉了。似乎小津的感覺並不對,並沒有給我們生動的日本人形象。那麼日本人應該是怎樣的形象呢?我們很容易想到「武士道」,暴力,好鬥,拼命,或者像高倉健那樣,話不多,從不笑,男子漢是男子漢,但也夠給人威壓的。早年看電影《生死戀》,兩車相撞,一語不和,車上人就下車打了起來。這似乎跟野蠻殘暴的日本鬼子很吻合。但是到日本後,發現日本人其實是很溫和的,他們幾乎不打架。吵架也很少,他們奉行「不爭論」原則,以至於見中國人爭論(有時候只是在討論,也許是語氣沖吧),或者是動手動腳開玩笑,他們都慌忙勸道:「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兩輛車相撞,雙方各自下來,不是打架,也沒有理論,一開口就達成共識:妥善私了。和和氣氣。當然之所以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叫員警的麻煩,彼此節約時間和精力。但這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如不理性,就只能惡語相向,拳腳相加了。
我本來應該明白的,現實和藝術的趣味是不一樣的。現實追求的是脫出現實,比如「江山如畫」,如果「江山」只是「江山」,是談不上「美」的,要像「畫」一樣才是「美」。而有意思的卻是,「畫」卻是相反,要竭力脫出「畫」,讓「畫」接近「江山」,「畫如江山」,甚至於竭力表現自然世界的殘缺,來實現藝術的「美」。比如畫樹,是一定要畫些枯葉的,而園林師修整樹木,則竭力要把殘枝敗葉去掉。當年看侯孝賢的《咖啡時光》(說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電影),主人公被安置在東京的アパ—ト(公寓),這種房子我住了好幾年,破破爛爛,但導演卻對之情有獨鍾,以它為背景,而且在影片中確實也美極了,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其美,當然其中也有因為懷舊而產生的美感。黑泽明也很能营造這種美的,而小津却不想把生活「文藝化」,他恪守着生活本身。
仔細想想,小津鏡頭下的日本,倒是真實的日本。只不過我自己離開日本太久,不自覺把日本「文藝化」了。剛回國時,整個人還浸在日本的氛圍中,對國內百般的不適應。但要說中國與日本有什麼不同,也說不出子丑寅卯來。日本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存在,好像鮮活的樹葉。但時間久了,水分沒了,剩下乾巴巴的葉片,甚至成了標本,它成了本質,被概念化了。於是腦子裏也就有了日本應該有的面貌了,而其實很多時候卻是從傳媒中接受的,或者是被點撥的。概念化的東西十分便於講述、傳播和接受。回頭想來,其實日本人的表情,就是小津電影中的人那樣。日本人極其講究「禮」,講究「禮」,就不能沒有一套禮儀。無論是《秋刀魚之味》還是《東京物語》裏,都體現了這種禮儀:舉止端莊,點頭鞠躬,乃至不喜形於色;說話謙和,節制,乃至謹小慎微。即使是家人之間,也是如此:父母到子女家,要說「打擾了」;父母在子女家吃了飯,要說「感謝招待」;子女對父母,也客套得像對客人;笠智眾表演的角色,最常掛在嘴上的口頭語是「そうが」(是這樣啊!)。套用老托爾斯泰的話,規矩的面目總是相似的,不規矩的面目則各有各的不同。不規矩的面目是生動活潑的,歪話臭話,總比正經話來得有趣,「黃段子」總是充滿了創造力。而規矩的面目,就一個詞:呆板。
但是呆板,並不等於傻;遵守禮儀,不等於人心不存在,只能表明,人心被規訓得很嚴實,你很忍耐。日本人確實是很忍耐的,小到人際關係,大到國家命運。比如二戰後被占領,日本人很知道自己是個「不正常國家」,但那是沒有辦法的,只能忍。兩次海灣戰爭和阿富汗反恐戰爭,日本或是出錢,或是出人,簡直成了「美國的提款機」,但還是忍著當了這個冤大頭,只求在這種忍之下,有朝一日能抬頭。其實,「明治維新」也是忍出來的。當年日本的國門也是被迫打開的,與中國一樣,只不過他們在無奈之下採取了與中國不一樣的態度。都說日本是個虛心學習的民族,但其實,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窩囊廢。原本堅定的「尊皇攘夷」分子、堪稱日本「義和團」式的人物伊藤博文,當他在上海和倫敦受到西方文明強烈衝擊的時候,內心一定複雜極了,抵抗,不甘,但他最後選擇了順應,把屈辱消化了。
日本人的消化能力常令全世界驚異。旅日作家劉迪曾經說過自己一個經歷,剛到日本時,他發現日本盒飯裏常有幾根麵條。「當時我很不解,為什麼米飯中還要加麵條,後來日本人告訴我說,那是為消化美國對日輸出的麵粉不得已採取的辦法。」作為基本以大米為主食的國家,二戰後美國曾一度給日本提供小麥作為援助,也從而向日本施壓,推銷自己的小麥。為了化解美國政府的壓力,日本政府採取了兩個方法:一方面為中小學「給食」提供麵包、麵條等,另一方面,派出大批飲食專家,通過電視、報紙雜誌等各種媒體廣泛宣傳麵食烹飪方法。
其實,這種承認現實的消化,是他們傳統精神的一部分。比如面對苦難的享虐,還有面對局限的接受,還可以將之發展成「美」。日本人認為「小即是美」,清少納言有句名言:「何も何も小さきものはみなうつくしい。」(無論什麼,凡是小的就是美的。)但是這「小即是美」的觀念,是必須有個確認者的,靠什麼來相信明明是「小」的卻是「美」的?靠心。為了緩解外界的擠壓,必須把心靈世界放得很大,所以日本人很喜歡「心」這個詞。在看不見摸不著的「心」中,「小」可能變成了「大」,苦難可以消化成了養料。
當然也總有難以消化的時候,比如《秋刀魚之味》中的少女道子,心儀的男性陰差陽錯失之交臂了,失望,痛苦,但還必須在父兄面前表現得很節制,於是就告辭了回到自己屋裏哭。但是如果是父親,德高望重,就不能這樣了,即使是死了妻子。《東京物語》中的老父親在妻子去世時,也躲開了眾人,但他並沒有哭。當他的兒媳找到他時,他只是站在海邊發呆,連悲愴的表情也沒有,他說:「漂亮的黎明啊!恐怕今天又會很熱。」生在島國的日本人,對世界有著與生俱來的宿命感,他們把哀心寄情于自然風景,這也是一種消化吧?
然而,既然是宿命的苦痛,長期壓抑下來,也終不是個辦法,那麼就將之分成受壓和泄壓兩個時段。比如公司職員,白天受壓,晚上就去酒吧泄壓,使得第二天再能去受壓,接受老闆的罵、客戶的挑剔,而可以面無慍怒。但有的時候面無慍怒是不夠的,禮貌也無法敷衍對方,必須要你表態,這時候就必須察言觀色,閃避談吐。有一種說法,日語的句式所以把謂語放在最後,就是出於察言觀色的考量的,比如你是否贊成某個意見,先說了「我」,再說「這個意見」,觀察對方的反應,然後再決定說「贊成」,或者臨時改成「不贊成」。
這麼表達的時候,那表情一定是複雜的。有人說日本人的表情就如同日本能劇裏的能面,兼有「悲哀與微笑兩種截然相反的表情」,那是一種曖昧的「大」表情。日本能面具據考證是來源於中國的儺面具,但精神實質卻是大不一樣的。所以我說過,中國離日本,要比離美國還要遠。這一點,當年被不可思議地轟炸了珍珠港的美國人,似乎也有類似感覺。也許是因為語言?語言不僅是表達思維的工具,還是思維方式。當然現在年輕的日本人也會講英語了,生活方式也很西方化了,面容表情也跟過去不一樣了。民族跟民族的距離在拉近,現代化的東京的面貌跟紐約似乎並沒有多大不同。畢竟地球變成了一個村,大家都這麼說。但這是不是也是「文藝化」的認知?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日本人的表情的圖書 |
 |
日本人的表情 作者:陳希我 出版社: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5-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70 |
二手中文書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文化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日本人的表情
中國人「輕」日本,又「重」日本,「恨」日本,「羨」日本。
在中國人眼中,日本文化是中國傳入的變種,但又倚賴日本的科技、商業等;他們受過日本的壓迫,其五千年的傲氣也瞧不起庇蔭在中國文化的日本,但某種層面上,又在骨子裡抱著羨慕的情緒,如此複雜的愛恨交織,造成難以言喻的情結。
泡泡襪、和服、秋刀魚、忠犬八公、茶道、A片、皇室、河豚……一個中國留學生看日本文化
作者在日本求學的過程中,觀察日本人的各種特殊文化,並與自身的中國背景做一比較,創造出獨特的「真我」日本觀點。他筆下的日本充滿奧妙,也用一種有機的眼光來看待「活」的日本,體察其變動的生活型態。在他的眼裡,公共澡堂裡的袒裎相見是新奇的體驗;泡泡襪帶有一種曖昧挑逗的性暗示;日本人的勞動精神更是令人佩服。
中國 V.S. 日本的文化衝擊
中國人對於在大澡堂與別人袒裎相見十分害羞,但對日本人而言則是見怪不怪。
中國認為紅色是吉祥的象徵,但對日本人而言則有不好的意思,如赤點(不及格)、赤字。
中國人罵狗兒子、狗腿、狗屁,日本人卻認為狗是忠心的象徵。
中國人聚餐喜歡大場面,去大酒家,日本人則喜歡找小酒館,或自己獨飲。
中國人要明確的答案,日本人則奉行「不理論主義」。
特別收錄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完整收錄簡體版部分刪減之文章〈蒼井空的青空〉。
作者簡介:
陳希我,小說家,福建人。曾留學日本,現居中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冒犯書》、《抓癢》(寶瓶文化)等。作品入選多種選本,獲「人民文學獎」等若干獎項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部分作品被介紹到海外。曾被《中國圖書商報》評為年度文學新銳人物,香港《鳳凰週刊》稱其作品是「活脫脫人性陰暗的浮世繪」。
章節試閱
櫻吹雪
東洋列島,新年伊始,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每個月忙忙碌碌都有花期。一月梅花,二月桃花,三月櫻花。這花是一種比一種開得嬌軟,桃花已失去了梅花的挺拔,櫻花更沒有桃花的翹首,簡直弱不禁風,一陣風過,就飄下一大片。然而賞花的事卻是越鬧越紅火。櫻花從南到北,從沖繩島到北海道,步步進軍,日本人用個很形象的詞——「櫻前線」。那不夾帶綠葉的櫻紅,野莽莽的,讓人們恍惚身處的不是人間,而是某個不可把握的地方。那些櫻樹下的飄蕩著的不陰不陽的日本小調,搖曳著的怪裏怪氣的舞姿,那些天當房、地當桌的人們,那些頭髮梳...
東洋列島,新年伊始,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每個月忙忙碌碌都有花期。一月梅花,二月桃花,三月櫻花。這花是一種比一種開得嬌軟,桃花已失去了梅花的挺拔,櫻花更沒有桃花的翹首,簡直弱不禁風,一陣風過,就飄下一大片。然而賞花的事卻是越鬧越紅火。櫻花從南到北,從沖繩島到北海道,步步進軍,日本人用個很形象的詞——「櫻前線」。那不夾帶綠葉的櫻紅,野莽莽的,讓人們恍惚身處的不是人間,而是某個不可把握的地方。那些櫻樹下的飄蕩著的不陰不陽的日本小調,搖曳著的怪裏怪氣的舞姿,那些天當房、地當桌的人們,那些頭髮梳...
»看全部
作者序
1989年我去日本,日本人總問我:中國來的,還是臺灣?十分莫名。我甚至懷疑對方是故意的,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這是我從小接受的教育。課文、廣播、電視、報紙總是向我們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臺灣跟中國分離,是政治錯誤,政治,是可以整死人的。糟糕的是這錯誤一不小心就犯了,即便成年了,即便成了國家幹部。2008年,我的小說《冒犯書》在臺灣出版,寄回的樣書被福州海關查禁,我辯解說這是臺灣正規出版物,一個海關幹部張口就應:是臺灣的,國情不同!這個幹部後來被調職了,不知跟說了這話有沒有關係。
雖然是...
這是我從小接受的教育。課文、廣播、電視、報紙總是向我們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臺灣跟中國分離,是政治錯誤,政治,是可以整死人的。糟糕的是這錯誤一不小心就犯了,即便成年了,即便成了國家幹部。2008年,我的小說《冒犯書》在臺灣出版,寄回的樣書被福州海關查禁,我辯解說這是臺灣正規出版物,一個海關幹部張口就應:是臺灣的,國情不同!這個幹部後來被調職了,不知跟說了這話有沒有關係。
雖然是...
»看全部
目錄
櫻吹雪
愛有期
泡泡襪之戀
穿和服的女人
女坂
白與紅
東洋年
秋刀魚之味
八公犬
茶之道
大寫的吃
日本人的表情
向「生」而「死」
渡邊
「縮」與「擴」
打屁股
另一道風景
不勞動的節
當「做」成為「活」的方式
放逐至水
自由下的囚徒
道歉
「終戰」的一天
東京審判
日本病後
外人
蒼井空的青空
豐田,你為什麼要道歉?
鴨子的喜劇
曖昧與準確
誰在說「同文同種」?
日本的「欺負文化」
日本人的潔癖
好色
非色
請讓我成為您的孩子
跪在她腳下
入佛界易,人魔界難
三島由紀夫的行為藝術
永遠的困境 ...
愛有期
泡泡襪之戀
穿和服的女人
女坂
白與紅
東洋年
秋刀魚之味
八公犬
茶之道
大寫的吃
日本人的表情
向「生」而「死」
渡邊
「縮」與「擴」
打屁股
另一道風景
不勞動的節
當「做」成為「活」的方式
放逐至水
自由下的囚徒
道歉
「終戰」的一天
東京審判
日本病後
外人
蒼井空的青空
豐田,你為什麼要道歉?
鴨子的喜劇
曖昧與準確
誰在說「同文同種」?
日本的「欺負文化」
日本人的潔癖
好色
非色
請讓我成為您的孩子
跪在她腳下
入佛界易,人魔界難
三島由紀夫的行為藝術
永遠的困境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希我
- 出版社: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5-30 ISBN/ISSN:978986596712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