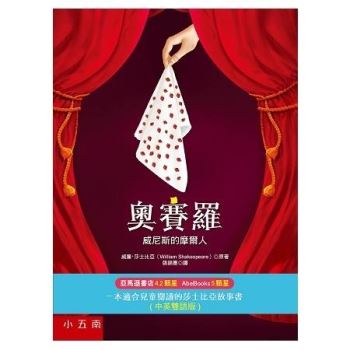八、 日本男人的銷魂之地
(1) 撒嬌的大男孩
說起來也真神了。什麼東西一到日本人的手裡,就變形失真,成為地道的和式的東西。
本來就是歐洲人發端的大杯喝酒、大聲調情的男人世界的酒吧,歐風東漸到日本後,日本人把它改造成了小盅飲酒,細聲調情的女人世界的酒吧。
男人世界的酒吧,是男人征服女人,男人是凱薩。
女人世界的酒吧,是女人主宰男人,女人是女王。
日本人的這一改造和顛倒,是基於這個社會「母性體質」的文化。
日本學者河合隼雄在其《母性社會日本的病理》中,把日本男人稱之為「永遠的少年」。
日本學者土居健郎在其《日本人心理結構》中,把日本男人的體質稱之為「撒嬌」的體質。
於是,美貌青春的酒吧女,就像百合花一樣,常開在「永遠的少年」的心裡。
於是,管理小小酒吧的掌門人,被「永遠的少年」親暱地稱之為「媽媽桑」。
於是,結束了一天的商務活動的日本男人到了酒吧,就像孩子回到了家,可以在媽媽桑那裡訴苦撒嬌宣洩,恢復身心的疲勞。而在媽媽桑的眼裡,這幫男人全是半大不小、需要哄的孩子,別看他們在外頭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白天狠三狠四地對部下發號施令,晚上來到酒吧後變得格外溫順天真,乖乖地掏出錢包,換取心靈的撫慰。
在凌晨五點半左右的銀座線地鐵的電車上,時常能看到總有兩三個青春女子人坐在椅子上。金黃色的長捲髮上面灑了一點亮粉,在燈光下一照,有點像頭皮屑。長長的耳環,挑黑的睫毛,淡淡的腮紅妝。黑色靴子,包裹著性感的小腿。皮草外套敞開著,露出裡面豹紋吊帶裙,裙角鑲著一圈白色的蕾絲花邊。膝上放著精緻的敞開拉鏈的小包,淺黃色的LOUIS VUITTON的,裡面放著手帳,還剩一半的爽健美茶,掛滿小裝飾物的手機。包包的邊緣已經磨損了,有點髒舊的感覺。臉色和眼神流露出一種苦澀的疲倦。這既有一夜不眠的疲倦,也有一夜勞心的疲倦。和OL小姐迎著朝陽上班不同,酒吧女是迎著朝陽下班。
黑白被顛倒了,作為女人的心相當然也顛倒了。
酒吧女和OL,前者更能閃現人性的本真。前者更能博得日本男人的歡心。
這令人想起作家井上靖的一句話:「無論什麼樣的女性,在一生當中,都有迷人的瞬間。」
銀座女的標準相
銀座為何能讓日本男人流連忘返呢?當然,銀座地處高檔商業區域,氣氛不同於新宿、池袋、上野等地是個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還在於銀座酒吧女個個姿色出眾:一雙白白的小腳踏在高高的木屐上,步子帶著飄逸感;一身淡淡粉紅色的和服包裹不住那嫩滑的香頸、玉背;那濕潤的豐唇、深沉的眸子又是如此的風情萬種而不失華貴的持重。據說這是銀座酒吧女的標準相。
除姿色之外,銀座酒吧女還會以「藝」技悅人。與只會點點煙、斟斟酒、遞遞毛巾的一般酒吧女相比,銀座酒吧女則需每天看報,又需知道文壇近事、體育近況,還需學心理學,這樣才能應付客人的種種話題,不至於冷場。銀座酒吧女和一般的酒吧女不同的是,她們霧裡霧外的,煙雨朦朧地哄騙男人還能提升為一種「術」。如在前幾年,有一位銀座酒吧女以蝶蝶的筆名,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成為一名小魔女的方法》。這位蝶蝶以自己在昏暗的酒吧裡練就出的對付男人的本領,教導要想成為點檯率高的小魔女說,即便不是美女,即便不是身材火爆的女子,只要能捕獲男人的心,就會使男人發狂,他就會時常來捧場。每天要有幾張臉,白天的臉、晚上的臉要有不同;高興的臉、冷淡的臉要不斷交替,如此等等。這本書一下成了老女人、小女人的必讀書。而另外一名銀座媽媽桑桝居櫻子(ますいさくら)所寫的《銀座媽媽桑教你看男人》,則是教導女人如何分辨好男人和壞男人,以及怎樣與這些男人交往。一下子也成了日本女人的經典。
客人們在銀座的女人堆裡穿梭,借此識破人性玄機,激發靈感,從而寫出好作品。而有的日本名流則乾脆拜倒在銀座酒吧女的石榴裙下,向她求婚,把銀座的世界帶回家,把銀座酒吧女的感覺帶回家。在這點上,日本男人比較寬容,不太忌諱酒吧女低賤的身份,與她們動真感情,最後結婚生子的大有人在。這和中國男人把風塵女看成「東風惡,歡情薄」有很大的不同。
對於銀座的男人們的盡情盡興,銀座的媽媽桑們也不是省油的燈。她們除了有討男人歡心的「藝」之外,還有最厲害的殺手鑭就是洩露男人們的老底,以抬高自己的身價。
最近又有一位叫英子的銀座媽媽桑寫了一本書叫《夜之文壇博物誌》,描述文人們在銀座的夜間活動:比如說野坂昭如是花花公子,說安部公房是三P(三個人的性遊戲)愛好者等。演員米倉涼子為了要在《黑色筆記本》的電視劇中扮演銀座媽媽桑的角色,請正牌媽媽桑傳授經驗。媽媽桑說了三條長袖善舞的經驗:要做酒吧媽媽桑第一要頭腦好,夠聰明,知道揣摩男人的心思。第二要有氣勢,要壓得住男人。第三則需要無情,懂得逢場作戲,永遠都不付出真感情。看來銀座的酒吧女還實在不好欺。
日本文學作品的代表《徒然草》曾如是說:「以女人髮作繩,能繫大象;以女人屐作笛,能招秋鹿。」如是而論,銀座能有如此的知名度,是否也和銀座媽媽桑的肌膚艷美有關呢?進一步而思,酒吧和吧女,是否就是日本男人生存的母胎呢?我在想,世界上可能也只有銀座的酒吧,銀座的媽媽桑能把男人的色、欲、情、性完好地平衡在一個點上,從而使男人的意欲昇華,創造出男人應該創造的東西。這就應了歌德在《浮士德》裡的一句話:
永恆的女性,引導男人上進。
九、青春女子的神秘世界
(1)解構美麗之謎
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的那種獨一無二性、最能代表大和民族的那種陰濕柔軟性、最能代表日本人的那種母性體質的,恐怕就要屬日本的舞妓和藝妓了。
這是一個神秘的青春女子世界,這是一個充滿迷幻的為上流社會男性客人服務的地方。因為神秘,因為迷幻,所以三百多年來,日本的舞妓、藝妓又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巨大「黑洞」,吸引了為數不少的日本文人學者來解構其謎。
為追蹤京都舞妓,為她們拍攝了二十多年藝術相片的日本著名舞妓攝影家溝緣先生(溝緣ひろし),前幾年出了一本《京都的舞妓──歲時記》的寫真集。打開這本寫真集,我真是被震動了,這是怎樣一種令人感歎的美的世界啊!其中,有一幅《雪中祗園》的作品──
一位頭戴十二月花簪的美麗舞妓,身著淺色素雅的和服,足蹬高高的木屐,右手輕巧地撐著白色絲綢的傘,靜靜地佇立在茶屋的門前。暮色時分,團團的雪花在空中飄灑,在舞妓的周身飛舞。
靜謐。寒風。冷雪。
雪花中的舞妓,就像飛舞著的精靈。
攝影師溝緣先生在其作品下面題字:
這樣的光景已經很少見到了。
作家永井荷風在其《江戶藝術論》中曾這樣描寫日本的藝妓:
憑倚竹窗,茫茫然看著流水,她們總是令我歡喜。
藝妓的人生如同窗外潺潺流水,帶給人瞬間歡樂的同時,最後剩下的只有回憶。踏著小碎步的藝妓優雅地回眸,和著櫻花那開在最絢爛時的浪漫,讓古老沉靜的京都神秘依舊。
(2)舞妓的技藝
這裡,問題的費解之處在於──
僅僅是因為生了一張漂亮的臉,長了一副窈窕的身材,或者說,僅僅是因為青春女子的青春魅力,日本的舞妓、藝妓才得以積三百年之傳統而成為一種文化嗎?才得以能吸引一批批腰纏萬貫的大亨、一幫幫精神世界的富有者和顯赫一時的政界風雲人物嗎?顯然又不是。
因為如果是那樣,舞妓、藝妓又和青樓女子有何區別呢?因為如果是那樣,難道日本人心目中的藝妓文化就是娼妓文化?這又與歷史不符,與事實不符。那究竟什麼才是藝妓的精神心相呢?究竟什麼才是藝妓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呢?
現在一般公認,京都是日本舞妓的發源地。現存有五大藝妓館,分別為祗園甲部、祗園東、宮川町、先斗町和上七軒。它們組合成了京都著名的「花柳界」。在五大藝妓館中,祗園甲部最負盛名。其歷史可追溯到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當時為了提高女性的自立,京都著名茶屋「一力亭」的九代當家杉浦治郎衛門、京舞井上流家元、京都府知事長谷信篤等有財有勢的人,創立了「祗園甲部歌舞會」,專門培養女性從事歌舞藝術,並明言「賣藝不賣身」的精神。就在這一年,在京都舉行的博覽會上,舞妓們第一次在小木屋裡面對客人獻藝,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祗園甲部的名聲也因此大振。
培養一名舞妓並非輕而易舉。在京都每年春天各部開始選考招收十五歲左右的美貌女子,經過五年的嚴格訓練,才能正式出台獻藝成為舞妓,此前為舞妓候補。一般經過十年的舞妓生涯,藝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便可升為藝妓。由於現代女子普遍習慣了洋式的生活起居,因此,和風、和式、從穿衣跪坐到站立行走的稽古訓練對她們來說更是不可缺少的科目。此外,她們還得修習琴棋書畫、歌舞及茶道等。
舞妓從頭飾到著裝都非常講究。比如髮型就有嚴格的格式。舞妓的髮型不用像藝妓那樣夾入假髮,全靠自身的一頭長髮梳理而成。
頭上所插的髮飾也因月份而變化。一月為松竹梅,二月為梅花,三月為菜花,四月為櫻花,五月為紫藤,六月為柳條,七月為團扇,八月為芒草,九月為桔梗,十月為菊花,十一月為紅葉,十二月為辭舊迎新的吉物薈萃。而在正月期間舞妓們一般插稻穗狀的髮飾,舞妓戴右,藝妓戴左,祈願新年五穀豐登。舞妓著正裝時腰帶的結法與藝妓不同,不是弄成方塊小包背在腰背上,而是將腰帶垂在背後,直至小腿肚,給人一種飄逸感,尤其當她們翩翩起舞時。
據說要成為一名出色的舞妓,除了藝術到位之外,在情性上還要修煉得心靜如水,既無雜念也無野心,純而又純,使見了她們的客人也變得純潔、善良。
這正如中國清朝駐日本公使黃遵憲,在一首題名為《藝妓》的詩中所言:
手抱三弦上畫樓,低聲拜手謝纏頭。
朝朝歌舞春風裡,只說歡娛不說愁。
十、從和服裡掙脫出來的放蕩
(1)外遇最純情嗎
在每年都有名人自殺的日本,文學評論家江藤淳在一九九八年的自殺,最令日本人看不懂了:為先走八個月的妻子江藤慶子而自殺,為長相廝守的純愛而自殺。這在婚後多有「不倫」經歷的日本社會,真屬天方夜譚了。
「不倫」是日語的說法,它的中文意思就是「婚外情」、「外遇」。渡邊淳一的「不倫」小說《失樂園》,把日本人本來就不軌的「不倫」之情給燃燒得旺旺的。泡溫泉、看雪景、觀櫻花、賞紅葉、吃法國料理、喝高級葡萄酒、進出高檔賓館、達到高潮的一次次做愛……原來「不倫」竟有如此的風情萬種,原來「不倫」竟是一個如此夢幻般的世界。《失樂園》令日本人大開眼界,想入非非。更為重要的是,本來屬於有閒階級的婚外情,渡邊淳一給它普及到平民大眾階級。因為《失樂園》中五十歲的男主角久木就是一家小出版社的上班族。他和端莊美麗的三十八歲凜子墜入靈肉一體的私情後不能自拔。戀情暴露後苦惱的凜子無可奈何地傾訴道:「同不再愛的人牽強地在一起會傷害對方,但與真愛的人相愛難道只能被說成是不道德?」久木安慰說:「既端莊又情迷,既非常認真又有可能失卻常態,我愛的就是這樣的你。」凜子說:「我也是。」就這句看似簡單的「我也是」,卻把日本女人天性裡跳動的春心和從和服裡掙脫出來的放蕩表現得相當到位。
日本人天性比較單純,因此「你太漂亮」、「可愛」、「我愛你」這些肉麻的話語出自日本男人之口,日本女人會信以為真地認為:他喜歡上我了。而請客吃飯是「不倫」的前奏。日本人認為如果男女在外一起吃火鍋則表示關係非同尋常,因為兩雙筷子在同一鍋裡撈來撈去,這對公私碟筷分明的日本人來說,頗富淫樂意味。此外,在居酒屋等平民價格的小店內肘碰肘地吃東西也等於貼了「戀愛中」的標籤。「不倫」的婚外情一般發展都很快,再加上日本人本不擅長談情說愛,於是去情人旅館發生肉體關係那是很快的事情。按日本人的說法,一對男女如果並排坐著吃壽司,那肯定是發生過性關係的,不是夫妻就是情人。
只有外遇最純情──這是相當一部分日本人的想法。在影視圈最早拍裸體寫真集的葉月里緒菜就說過「外遇是最純真的戀情」,並身體力行,出道後便先後與真田廣之、唐澤壽明等有婦之夫傳出醜聞。但這種最純情的外遇付出的也多,結局也較慘烈。因此現在年輕的日本人逐漸拋棄傳統婚外情的做法:雖說動了真情,但絕不是嘔心瀝血式的;雖說刺激新鮮,但更接近於逢場作戲。以「不倫」的雙方來說,男人不願犧牲家庭,女人不願為「不倫」之情而煎熬受苦,更不願做不明不白的「二奶」。
在日本「不倫」已經變得相當輕巧,相當隨意,相當日常化了。那種《失樂園》式的轟轟烈烈、要死要活的婚外情(久木和凜子最後到了雪花飛舞的山地,服藥自殺。死時兩個人還在做愛,肉體緊連),照日本人的說法那是少數「專業」選手才能達到的專業水平,而絕大多數的「業餘」選手只能是業餘水平。你看,那些當眾在垃圾箱翻找食物的拾荒者也在「不倫」,那「不倫」還會浪漫嗎?
(4)榻榻米文化的演繹
「不倫」社會要有「不倫」文化作先導。在這方面,兼好法師在《徒然草》第一三七段有以下的敘述:
世間萬事,唯始與終特有意趣,或不得相會而憂戀事之不終,或悲歎無常之契,或長夜間隻身待至天明,或寄思緒於遠地,或身棲荒居而緬懷昔日,唯此方可謂通曉戀情之真諦也。
換句話說,從中所品味到男女結合前後那種若即若離的情趣,就可想成是「風流好色」的內容。又如第一九○段中說:
妻者,男人不應保有者也。……無論何等女人,與人朝夕相處,亦當覺可厭可憎。自如方言之,亦當有懸空無著之苦。雖不同棲而時時過往相見,則反而成為歷年所而感情始終不渝之伴侶。不期而至,止而宿之,則可常保新鮮之感也。
一般認為兼好法師的這段話,被視為日本「不倫」文化的先導。而驗證這一「不倫」文化的,則是在一千年前寫成的《源氏物語》。《源氏物語》中有一段為我們所熟悉的話:
我的主子身份高貴,地位尊嚴,然而年方青春,容姿俊秀,天下女子,莫不風靡。尚無色情之事,未免缺少風流,美中不足吧。
主人公源氏的第一個婚外戀對象是父親的寵姬,他們通姦後生下了日後成為冷泉天皇的皇太子,而兩人心中並沒有什麼罪惡感。
再從自然風土來看,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天災頻發。這就讓日本人產生了「人生五十年,如幻如露」的不安定感。他們悲歎世事無常,認為應該及時行樂,便逐漸形成了自憐自戀的心理。沒有性,人生便不過是一場浪費。而在性事的活動中,又對轉瞬即逝的美特別推崇。在他們看來,越是悲情的、短暫的、注定要毀滅的東西,就越是美的、精緻的。而「不倫」對他們來說,就屬於轉瞬即逝的美,其結局雖然是悲情的,注定要毀滅的,但毫無疑問,它是美的。這就像月是殘月最美,花是落花最美,雪是融雪最美,而女人則是情人最美。
日本的榻榻米文化其實也養育了日本男人奇特的性心理。對於跪坐在榻榻米上的日本女人來說,身材的美感被坐姿消解,胸部的丰韻被和服遮掩,但白白的粉脖卻成了焦點。由於和服的領子常常像花瓶的瓶口一樣張開,唯一露點的粉脖就像走光一樣引起日本男人的想入非非,由此湧動對肉體的占有欲。窈窕艷女的矜持與烈焰紅唇的誘惑,使榻榻米也蒙上了性的曖昧。這就像谷崎潤一郎所說,精神不存在美好的東西,最美的東西就是人的肉體。再加上日本古來就有「神婚」和「神樂」之說。前者強調既然日本之神也可以超然地享受性的快樂,那麼作為神的「民孫」當然也可傚法。這就在觀念上與古希臘神話中對性的「罪與罰」分道揚鑣,為日後日本人的性開放掃清了來自世俗的批判。後者強調既然性器崇拜成了讓神快樂的「神樂」,那麼盡情放蕩和取樂豈不順理成章?
於是,浪漫女詩人與謝野晶子寫下了極富挑逗的詩句:
你不接觸柔嫩的肌膚,
也不接觸熾熱的血液。
只顧講道,豈不寂寞?
「好色」,在中國屬於下流的含義,在日本則沾上了美學的含義,成了男人和女人交歡的一種審美情趣。「好色一代男」成了風流男。「好色一代女」成了風雅女。以至在一百三十年前的明治初期,英國學者張伯倫赴日本留學,打算將日本神話《古事記》譯成英文出版,結果譯文被誤認為色情小說,留下令人回味的趣談。
在康德那裡,人的「快樂的原則」和「道德的原則」總是處在對立的狀態。而日本人則聰明地繞開這種對立,講人的快樂原則和美學原則。日本學者佐佐木孝次在《母親和日本人》一書中談到日本人與性時,不無深刻地說,多少年前一位與日本男人結婚的英國教師,以她的生活經歷向世人表白,對日本男人來說,所有的女人只不過是能走路的性工具。這並沒有說錯。在日本固有的觀念是,男人看到女人燃起情欲是自然的。也就是說女人僅僅是男人的性夥伴。但它又是在至美的原則下進行的。這就像日本女人穿的和服,確實美如一朵花。但這朵花總給人柔軟而凌亂的感覺,它總被作為蹂躪的對象被扔在曖昧的榻榻米的一角。
因此無論從歷史、文化和傳統上來看,日本社會中的色情和「不倫」是與其民族性有關。如今日本性產業的規模基本都在十萬億日元左右,相當於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更為奇觀的是,日本還總有「不倫」後備軍往裡面擠,他們諳熟情愛之道:偶爾苟合還有一時篝火之溫暖,一旦長相廝守不免會落個焦炙冷炭的下場。他們比誰都懂得婚姻,更不願踏上紅地毯。他們會以經濟或優柔為托詞,良心和責任為光環,耳鬢廝磨之餘,把這段露水情緣意淫成一段偉大的愛情而欷歔不已。現如今,從和服裡掙脫出來的日本女人正和染著金色頭髮的日本男孩,他們在快樂法則的運轉下,正在續演著《愛的流放地》和《東京塔》的故事。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山櫻花與島國魂:18個關鍵字看穿日本的圖書 |
 |
山櫻花與島國魂:18個關鍵字看穿日本 作者:姜建強 出版社: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9-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5 |
二手中文書 |
$ 269 |
社會學 |
$ 289 |
社會人文 |
$ 299 |
中文書 |
$ 299 |
文化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山櫻花與島國魂:18個關鍵字看穿日本
本書是作者從綜合角度對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情緒心態作思考的學術性散文。書中涉及日本人的生活、習俗和人生觀,對於了解日本人的歷史傳統、文化特徵和生存觀念等,提供了具體而生動的例證。作者將日本人生活中的許多細節,結合學術界對日本文化的評價,融入言之有理的論述,可以幫助讀者考察真實的日本人既不同於西方人又有別於其他東方民族的獨特行為與思維方式,從而對日本文化的特點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作者簡介:
姜建強,一九五六年出生於上海。出國留學之前在大學任教十年,并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發表各類學術論文一百多篇,編著多部。因其學術成績,本人曾被收入英文版的社會科學針人詞典。二十世紀九○年代留學日本,在東京大學就讀。后在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擔任客員研究員,致力於日本哲學和文化的研究。發表各類文章百篇以上。現在東京從事新聞媒體工作。著有《另類日本史》(三聯香港)
章節試閱
八、 日本男人的銷魂之地
(1) 撒嬌的大男孩
說起來也真神了。什麼東西一到日本人的手裡,就變形失真,成為地道的和式的東西。
本來就是歐洲人發端的大杯喝酒、大聲調情的男人世界的酒吧,歐風東漸到日本後,日本人把它改造成了小盅飲酒,細聲調情的女人世界的酒吧。
男人世界的酒吧,是男人征服女人,男人是凱薩。
女人世界的酒吧,是女人主宰男人,女人是女王。
日本人的這一改造和顛倒,是基於這個社會「母性體質」的文化。
日本學者河合隼雄在其《母性社會日本的病理》中,把日本男人稱之為「永遠的少年」。
日本學者土居健...
(1) 撒嬌的大男孩
說起來也真神了。什麼東西一到日本人的手裡,就變形失真,成為地道的和式的東西。
本來就是歐洲人發端的大杯喝酒、大聲調情的男人世界的酒吧,歐風東漸到日本後,日本人把它改造成了小盅飲酒,細聲調情的女人世界的酒吧。
男人世界的酒吧,是男人征服女人,男人是凱薩。
女人世界的酒吧,是女人主宰男人,女人是女王。
日本人的這一改造和顛倒,是基於這個社會「母性體質」的文化。
日本學者河合隼雄在其《母性社會日本的病理》中,把日本男人稱之為「永遠的少年」。
日本學者土居健...
»看全部
目錄
前言:春日眺望,群鳥嬉游,心最樂
一、落櫻的美學
(1)本土感覺
(2)賞落櫻更動情
(3)自覺的無常觀
(4)不大喜也不大悲
(5)用落櫻美學對抗玫瑰哲學
二、看京都滿眼淚
(1)魂系京都
(2)哲學小道
(3)寺院神韻
(4)街巷意趣
(5)花木情調
(6)景致氣氛
(7)梁思成的義舉
三、濕氣文化的智慧
(1)風土與性格
(2)鎮守的森林
(3)綠的文化
(4)濕氣無處不在
(5)木造住房
(6)木屐與和服
(7)壽司和味噌
(8)蟲鳴和青苔
(9)黏糊糊的日語
(10)幽玄之美
(11)簡約的習俗
四、從陰...
一、落櫻的美學
(1)本土感覺
(2)賞落櫻更動情
(3)自覺的無常觀
(4)不大喜也不大悲
(5)用落櫻美學對抗玫瑰哲學
二、看京都滿眼淚
(1)魂系京都
(2)哲學小道
(3)寺院神韻
(4)街巷意趣
(5)花木情調
(6)景致氣氛
(7)梁思成的義舉
三、濕氣文化的智慧
(1)風土與性格
(2)鎮守的森林
(3)綠的文化
(4)濕氣無處不在
(5)木造住房
(6)木屐與和服
(7)壽司和味噌
(8)蟲鳴和青苔
(9)黏糊糊的日語
(10)幽玄之美
(11)簡約的習俗
四、從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姜建強
- 出版社: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9-06 ISBN/ISSN:978986596731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