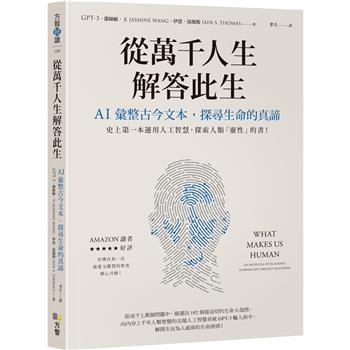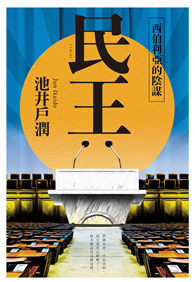序
追尋歲月的河──論程寶林詩風的嬗變( 代序)
程寶林在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積累了大量的詩作,其詩風鮮明而富於變化。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和詩人的旅美經歷對於詩風的轉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以這兩件大事為界可將程詩創作分為三個階段,主導風格分別是單純明朗、隱晦遠奧、從容雋永。本文將從詩歌主題立意、詩人內在心理依據、時代精神特徵、文化變遷及文化相遇的角度綜合把握程寶林詩風的嬗變,並試圖以詩風嬗變的分析來揭開時代精神特徵、文化變遷及文化相遇的一角面紗。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活躍於高校校園的「學院派」詩人中,程寶林可算是個佼佼者。他的輝煌不是曇花一現,二十年的不輟筆耕成就了累累碩果。從開始成名的八十年代初到現在,其創作生涯已有二十餘載。二十多年在滾滾歷史長河中實在不算什麼,然而這二十多年對於崛起中的中華民族來說卻是國運轉關的關鍵。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資料的豐足,而且有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衝擊、精神的震盪;而國門的打開,更使出國接受外來文化成為可能。親歷八十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且旅居美國長達十年之久的程寶林決不是消極出世的隱逸詩人,其詩歌也不可能絲毫不受文化變遷的影響,從詩風的嬗變,不僅可以見出詩人的個人經歷、精神追求的軌跡,更能在詩篇的流淌中,重現歷史與文化於變遷中的綽綽身影。
詩歌的形成和發展,與先天的秉賦氣質有關,但更要受到客觀社會條件的制約和影響。「任何創作個性和風格,都毫無例外地要受到他所在的社會的政治、經濟、哲學、文化等等的制約和影響。這些影響是複雜的、多方面的,既影響其世界觀和人生態度,也影響其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緒。」 同樣,程寶林所處的時代變革及其旅美經歷都通過其人間接地影響到了其詩,從而使詩歌的總體風格在八十年代末和1997-2001年中發生了兩次較明顯的轉變。以這兩次轉變為界,可將程詩創作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以單純明朗、隱晦遠奧、從容雋永為主導風格。
一、 單純明朗的早期詩風
感受青春、禮贊生命、吟頌民族之魂是這一時期的主題。或抒個人情愫,或發民族情感,無論是清新綺麗還是激昂雄渾,都體現出單純明朗的個人風格與時代風格。
在83年所作的〈季節河〉 中,詩人自喻為河,來自雪山,奔往大漠。這條年輕而又清澈的河,沖下漸融的冰峰,呼嘯著狂放的野性,湧動著執著的期待,氾濫著溫柔的渴望,跳動著青春的脈搏。他的詩歌不僅為詩壇帶來了一股新鮮淨朗的氣息,更為時代之曲的譜寫添上了美妙的一筆。無論是〈初戀〉 的單純清澈、羞澀遲疑,還是〈野浴〉 的歡快淋漓、叛逆不羈都給蘇醒中的華夏大地增添了新的生機;〈南方啊,我的搖籃〉 描寫飽滿而豐盈的生活與情感,往事歷歷在目、故人盈盈可親,一柄油紙傘觸發了遐想無盡;〈天氣預報〉 採擷雲雨雪晴,於輕鬆明快中再現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這些詩篇既與詩人的少年情懷相恰,又與八十年代中期整個社會煥發出青春活力的時代風貌不無關係。如果說〈大西北,一群年輕人〉 以少年的朝氣與銳氣、年輕的自信與豪情唱響了時代的強音,那麼〈雨季來臨〉則貼切地表達出具有時代特徵的社會心態:久盼甘霖而得,初沐春風而樂。「在經過了長長的旱季之後∕雨季來臨」。充滿著誘惑、焦躁與渴盼,孕育著幻想、美妙與生機,在經過了長長的旱季之後,「鹹澀而潮濕的海風」吹送了雨季的來臨,它「沖斷亞熱帶密密設防的緯線∕撲進每一雙因渴盼而流淚的眼睛」。 這以震撼人心的力度呼嘯而來的正是時代變革的洪流、創造力與生命力的覺醒。
流覽程寶林早期的詩作,可以發現「土」與「水」是經常出現的兩個意象。「土」與「水」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因素,正是生命的源泉。在程詩中,故土意象俯拾即是:那家鄉的獨木橋和瀟瀟雨巷,那春日裡的梨雲桃霞,那陽光明媚的早晨,那長勢喜人的麥子苧麻,那兌了陽光新釀的包穀酒;還有那些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那追隨春天而來的放蜂女郎,那秋夜的平原上,銅鈴兒叮噹叮噹的馬幫,那個走南闖北卻鰥居而死的講古佬,那些多情而又活潑的南方的女人們。對於土地的眷戀是程寶林終生難以釋懷的情結,無論是遷居屋頂還是困守高樓,無論是逢著小雨還是遇到冰雹,他對故土的癡念都註定了無法變更。
然而,在遠方,還有另一種東西招引著他,慫恿著他的渴望與追求。那是雋永流動的芳蹤,是生生不息的衝動,是深沉遼闊的雄心,是鹹澀神秘的磅□。那是水,是大河、是大海,是奔騰、是激越,是藍色的幻影,是永恆的誘惑。它一忽兒是男性的海,「每一次裸露的衝動∕都會給渴望擁抱的陸地∕帶來痛苦,和痛苦之後勃勃的生機」 (〈颱風季〉)一忽兒又變成女性的河,彈奏潺潺淙淙的伯牙之曲,濺濕青石上晾曬未乾的詩經,閃耀著古典美的流光溢彩,彌漫著書卷氣的淡淡芬馨。水,這種透明的液體,是那麼神秘莫測,它讓祖祖輩輩生長並安葬在土地中的人們感應自己體內血液的流動,「讓住在狹隘的山谷裡的∕都跟著長江走出,投向東方∕那沉澱著藍色血液的古遠的遼闊!」 (〈跟著長江〉)「生命源於水而歸於土。」 對故土深深的愛是人生的根基,對大海的崇拜與追求是生活的動力。「土」所代表的厚實的穩固感與「水」所代表的流動的生命力相反相成,不僅鼓蕩著詩人的心胸,而且暗合著時代的脈搏。
吟頌民族之魂是程寶林早期詩歌的又一主題。〈屈原〉 感慨對故國詩篇、中華血脈的無限崇拜,〈世紀之初〉 痛陳對清朝昏庸、國人愚昧的無比憤恨,〈寫大字的人〉 切言對國學漸微、文化承傳的無盡思索;而〈廢墟上的玉米〉 以玉米的堅韌不屈、蓬勃生長象徵中華民族不能被暗殺的生命力量,使民族性格躍然紙上;令人掩卷深思的〈百年茶客〉則講述了一個故事。故事中的百年茶客不滿因循守舊的沒落文化,他「痛感這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比大清的龍旗更不易腐爛」。他抱著一絲幻想,希望等到一壺茶,於是在茶館的一角坐下,一坐就是一個世紀,不問世事,木然飲茶。百年茶客懂茶、等茶,卻縮在一個角落裡獨酌,寄希望於等待之後的賜予,可他卻等來了一杯棕黑色的液體,滋味既澀又苦,「百年茶客就這樣死於一口咖啡」 。世事變遷,茶館悄然改變。咖啡代表的異質文化裹脅而來,衝垮了百年茶客的最後防線;那把硬朗的紫砂茶壺也作為他的棺槨葬入土中,讓位於當下流行的咖啡壺。茶客作為舊時代的老古董,他的存在似乎是不和諧的、可笑的,然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民族情愫的固守,所以他的消失讓人不禁感喟萬端,而他的木然、孱弱、一層不變的冥頑、閉目塞聽的枯朽,又讓人扼腕憤然、怒其不爭。憤恨未過,心頭卻又一驚:如果人人都在啜飲咖啡、追逐「情調」,那流傳百世的「茶」還有誰能記起?茶的奧妙、茶的精神、茶的血脈又將交付給誰? 這正是一個民族於進退之間的艱難選擇。
感受青春、禮讚生命、吟頌民族之魂,但不停留於表面的顯附。哲學層面上詩歌立意的深化使詩的格調既高且豐,境界為之闊大,底蘊為之深厚;這也使得詩歌在風格上的單純明朗不會流於輕淺單薄。
二、 隱晦遠奧的中期詩風
人生的思考、艱難的選擇、難解的困惑;這是程寶林中期詩歌的主題。異質思潮和多元文化隨著改革開放大潮一擁而入,令人耳目一新的階段過後,這些因素在文化層面的影響進入了一個更加深刻的階段,並於八十年代末達到了峰值。此時的詩人恰從學院走出數載,正好經歷了這一思想解放和文化整合的過程。面對著接踵而至的思考、選擇和困惑,他的詩風也漸漸脫盡了早期的單純明朗,而變得隱晦遠奧起來。
創作於88年的〈病鳥〉與優美、自由、快樂無關,一句「天空黏住了靈魂的悲鳴」奠定了陰鬱隱晦的基調。「看天看井∕看井中的天和天上的井∕許多鳥深陷其中∕翅膀在空氣中腐爛」 ,天和井意味深長的錯位,使人在天空中看不到自由,卻看到了鳥的深陷和腐爛。而這種錯位象徵著什麼?若渴望高飛的「鳥」是人的理想願望、歡樂幸福、愛情詩意的象徵,那麼本該提供自由空間卻淪為閉塞枯井的「天」又象徵著什麼?這種消極的感情意緒到底是什麼造成的?是內心的矛盾和困惑?如果是,那麼造成人們矛盾困惑的社會因素又是什麼?詩風的隱晦遮掩了答案,卻激起了無盡的追尋和考問。再看〈栽培葡萄〉這首89年的作品。「每一粒葡萄都至少面臨∕三種方式∕但你一生不能同時栽培∕三粒葡萄∕一粒釀酒一粒贈美人∕一粒懸掛枝頭 被風無謂地吹落」 。人生的選擇多而又多,可以執著於現實,幹出一番大事業,可以溫柔繾綣、沉緬於溫柔之鄉,還可以散漫自在、與世無爭;然而卻只能選其中的一條路來走。這首詩言在「葡萄」而意在人生抉擇,雖遠奧卻更有餘味,是一種形象化的哲學思考。體現隱晦遠奧詩風的還有創作於89年的〈玻璃〉 和〈鼓手〉 。前者以蒼蠅的附著與飛離表現玻璃的透明空虛,給人一種強烈的視覺感,彷彿是影視藝術中的現代手法;後者表現鼓手在舞臺上的荒誕感,與荒誕派戲劇的手法相類,像是莫名其妙的夢魘。也許隱晦遠奧的背後並不總是藏著固定的答案,而只是意欲表達一種心理、一種意緒,一種對於社會和人生的困惑。「對中國人我說向前走吧∕對外國人則說go ahead∕沒有誰知道∕我是真正迷途的人」 。〈詩人〉的最後四句正是內心困惑的某種反映。
面對紛繁雜蕪的多元文化思潮,一時的困惑在所難免。由於暫時無法接受容納這些複雜多元的文化形態,詩人思想上的二元對立也成為一大特徵。如〈開闊地〉 中,平原的開闊平坦藏不下人的自由走動,來自隊伍的不安與敵意將他瞄準;再如〈廚房中的兩位廚師〉 ,一位將刀拿在左手,一位將刀握在右手,他們彼此警惕和恐懼。無論是平原上那一個人和一支隊伍,還是廚房中的兩位廚師,他們之間的關係都是不理解、不信任,和充滿敵意的相峙。
當然,程寶林這一時期的詩作並不僅僅是顛覆和諧的相峙、象徵暗示的隱晦,也有前一時期思鄉主題的延續。1996年的〈你被剪掉的頭髮〉 和〈夏天〉 正是他隻身在美的思親、思鄉之作。前者講述詩人作為父親,兩年不見幼子,偶見自己襯衣中兒子的胎髮,勾起了無盡的思念和無端的憂愁。後者描繪詩人在滿眼都是路燈光的紐約,在不堪忍受的刺目、耀眼中,卻辨認出有一點故鄉的流螢,飛抵了這個夏天。這種思親懷鄉的暖意給中期的隱晦遠奧帶來了一抹亮色。
三、 從容雋永的近期詩風
穎悟現實的複雜,容納文化的多元,於非位和無理之間找到恰當的位置,成就一種別樣的、藝術化的人生;這是旅美數載之後,步入不惑之年的程寶林的精神狀態和內心追求,也是其詩作轉入從容雋永風格的內在依據。
在1997-2001年之間,詩人鮮有詩作問世,這是一個積累和蛻變的過程。當2002年作者再度提筆的時候,〈擦亮馬燈〉所顯示的力量確與往昔大不相同。海外寫作提供了雙重的文化視角,正如詩中提著馬燈「在電燈與霓虹的城市摸黑趕路」的意象所象徵的雙重文化燭照。「馬燈」所象徵的古老中國的文化傳統與「電燈」「霓虹」所象徵的資本主義美國的現代文化並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區別、各有優劣。在到處閃耀著電燈與霓虹的城市依然可能摸黑趕路,馬燈的光線雖然微弱,卻可以「照亮腳尖前的小路」 ,在燈火輝煌的現代化都市中,馬燈並沒有喪失存在的意義,雖然鏽跡斑斑,但依然有人將它點燃,將它輕輕擦亮,在電燈照不到的黑暗中,用它的微光散佈光明和溫暖。這不僅體現了詩人對美國文化的接受、對中國文化的珍視,更體現出詩人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應對從容的氣度,以及在雙重文化燭照下開闊而嶄新的視野和具有穿透力的睿智。
在美國文化中浸染數年的經歷為詩人提供了又一文化背景,而人到中年的沉穩豁達則為思考的明晰透徹提供了內在心理依據。不惑之年的思考是濾去色彩的線條,嚴肅而冷靜。詩作中深藏了激越的情感、澄澈了繽紛的才情,雖簡約卻有力,發一言而雋永;這都是因為不惑的目光不再停留於事物的表面,而是切近了事物的實質。在〈對比〉中,乍一看「蘋果」和「子彈」被聯繫在一起進行對比,不由得會感到匪夷所思,而一旦洞穿了它們的實質,不禁要感佩於詩人見解的獨到和精闢:「蘋果」可以被吃掉,用來滋潤生命,而「子彈從不會被吃掉∕它們只是飛翔,並且吃掉」 ;這正是在生命主題下一個嚴肅的對比。同樣,在〈紙的鋒刃〉中,詩人也發現了刀片和紙之間的關聯,「紙可以像刀片一樣將人割傷∕甚至殺死∕但刀片卻無法像紙那樣∕折疊成小船∕在小溪裡順流而下」 。「紙」是文明的載體,「刀片」是暴力的象徵,文明可以比暴力更有力,而暴力卻永遠也無法超越文明。
與對比聯想相比,「他者」主題更具有哲思的魅力。〈自由女神雕塑下〉 一詩中,淺灘上的魚就是一個「他者」意象。魚兒被海浪或誆騙或裹脅,來到自由女神雕塑下,卻無法呼吸著岸邊自由的空氣而活下來,只能漸漸停止了與海浪的搏擊,窒息而死。〈跳摟之前一分鐘〉裡的「我」是美國這個黃金國度裡的他者。「一個陌生者、一個外國人」,「我」登上雙塔的頂部,準備「把我的死亡發表在水泥地上」,卻正趕上一架飛機飛來,「此刻是早晨8點45分,2001年9月11日」,「我的名字被錯誤地加在遇難者長長的名單上」 。結尾以一種近乎滑稽的幽默實現了「他者」向主流文化圈的融入,而融入的方式卻是名字被加在罹難者的名單。無論是自由女神雕塑下的魚,還是「罹難」於911的「我」,都是「自由國度」裡的「他者」。他們的存在和死亡都向所謂的「自由」提出了不容回避的質疑。詩作的意味悠長、含義雋永與詩人的旅美經歷和自身修養是分不開的。正是在穎悟了現實的複雜、容納文化了的多元之後,詩人才能夠兼收並蓄,不受其亂、而得其豐,於無理中尋找意義,在非位中尋找自由,從而形成從容雋永的詩歌風格,並再此達到一個哲學的高峰。當然,這並不是一個休止符,歲月流徙,歲月之河亦不停息。歲月的塵埃掩不住閃光的東西,抹不去,是流淌於歲月中的詩篇。
投身詩壇二十年,從民風淳樸的故土到日新月異的都市又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從激情澎湃、才情縱橫的青年到深刻睿智、豁達從容的中年,程寶林且行且唱,或單純明朗,或隱晦遠奧,或從容雋永,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動人的詩篇。他那鮮明而富於變化的詩風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奠定了他在當代詩壇的重要地位,同時也為我們反觀時代精神、文化變遷、文化相遇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視角。
張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