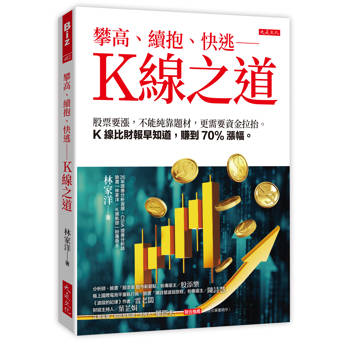序
張堃詩美學的三個向度∕瘂弦
其一、率真是語言的極致
人在海外,每當鄉愁來襲,常在越洋電話中與台北的朋友談詩論藝或閒話家常:但能夠長談者並不多有,張堃與我之間便有一條這樣的熱線,我們雖分處美、加二地,卻好像同住一城。鈴聲一響,兩人拿起話筒便放不下來,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不亦快哉!特別是最近,他計畫出詩集,囑我撰序,自慚學殖荒落,未敢著筆,乃在熟讀他的書稿之餘,以更多長途電話向他請教細節,作為撰稿之參考。這是一個新的經驗,主要是彼此有交會,有共振,有啟發,也有意想不到的創造。經過充分的溝通,張堃的詩,詩的張堃,一下子我全懂了!內心有悸動,舌尖有語言,這序言,我可以勉強成篇了。
我們最近對談的內容,多半環繞在詩的語言方面。我發現,張堃的詩,在語言的處理上,不是策略的,而是美學的,他所提出的「率真是語言的極致」這個原則,乃是通過長久的創作實踐所獲得的結論,他要以這樣他自己相信的語言,來承載他心靈生活的真實紀錄,表達他對世界的愛與希望。此一訴求篤定而明朗,不容有任何的異化、變形,這便是為什麼他那麼重視傳達的真確性與一致性。對他來說,語言是中性的,應用之妙,存乎一心,端在使用者的操作意向。
張堃深信,語言充其量只是手段,是過程,而不是目的,一旦它偏離了思想,就變成了一堆空洞的符號。在文學創作上,永遠是藝術要求決定遣詞用句,而非遣詞用句決定藝術要求,是詩人完成了語言,而不是語言完成了詩人。如果本末倒置,過分迷信語言的功能,甚至對語言產生拜物情緒,那就失去率真的基礎。
說詩人是語言的魔術師,那是對語言在詩中重要性的一種強調,語言並不是第一義的。修辭上的拗句,文法上的胡亂換位,是語言的偽裝,語言的不誠實,感性的怠惰,藝術的敗德。
假設問張堃,佳句和佳篇,二者僅能擇其一,他必定選佳篇而棄佳句;形式與內容,二者僅能擇其一,他必定就內容而捨形式。雖然他會說,二者兼而有之最好,不過我想張堃對佳句的定義跟很多人是不一樣的。對年輕人來說,句法和樣式是迷人的,他們常常逃不掉這種誘惑而陷入語言的遊戲。語言的遊戲是率真的敵人。
「清遠簡淡」,這四個字或可概括張堃率真語風的精義,這是清代文學家王士禎的話。王氏談詩畫三昧,說詩要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畫要「意在物墨之外」,講求「略有筆墨」即可,形成「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的視覺效果。畫家面對遠處的山巒,可以不著一筆,而以「霧失遠山」為題,照樣可以引發觀畫者的想像。如此「極簡主義」的作風,無疑是對雕琢得過了頭的惡質語言的一種顛覆。
我舉文學評論家唐德剛先生多年前在寫給我的信上的一段話,想聽聽張堃的看法。唐說:「中國新詩也不過七、八十年的歷史,但傳統詩(舊體詩)的毛病新詩差不多全都有了。這毛病多半來自語言的放縱,語言的褻玩。」「褻玩」這兩個字乍聽有點刺耳,不過當我聯想起古文〈愛蓮說〉上那句「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就覺得唐的話並無惡意。張堃說唐的觀點使他想起胡適之先生,胡曾向人表示他看不懂五、六十年代台灣年輕人寫的現代詩,胡適說的年輕人想必就是「我們那一伙人」(辛鬱語)。張堃的看法是:胡適並非真的讀不懂現代詩,而是他不喜歡,新詩到了李金髮,大概他就不喜歡了。的確也是如此,李金髮師承法國象徵派,新詩看不懂,大概就是從「髮翁」開始的。一般來說廣東人國語不大靈光,加上象徵的朦朧,再加上文言白話參雜,胡適無法忍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違反了白話文學運動的「初衷」,被認為是白話文學的第一次反動。所以胡才說看不懂;張堃說,也許胡大師真的看不懂哩。
我們又談到胡適批評杜甫〈秋興八首之八〉「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句,胡適說它「嚴重違反文法常規,不通之至」。詩人余光中說老杜此句可以作為現代詩顛倒字序的張本,古典詩詞研究學者葉嘉瑩則說「文法通了,詩也沒了」,她希望大家應該去探索文句背後深遠幽微的詩意。老年杜甫「晚節漸與詩律細」,說明他是有美學上的原因的。不過這種「錯綜對」可一而不可再,如果後學者依樣畫葫蘆,寫起詩來滿篇都是這樣的倒裝句,那不煩死人才怪。張堃說可見每一個人都有其時代的限制,有時候毋寧說是革命期的矯枉過正吧。有句話說:「語言是風。誰能管得住風?」不過文學史上可以找出一個發展規律,關於語言演變的反省與檢討,似乎從來沒有停止過。而語言的節度,總是代表一種文學的成熟。
雖然張堃的年紀比我們「七老八十」一代要小很多,但他卻與老一輩有同樣的時代感情,這一點很難得,也是他跟我們「那一伙」銀髮族「玩」在一起最重要的原因。老哥子們對他始終堅持率真樸素的語言風格,十分欣賞。近年,張堃詩的語言更走向單一、淺淡、清寂、蕭散,特別是清寂和蕭散,這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迷人的語境,張堃從這個方向去追求,說明他詩藝的層樓更上。此外,他並為自己定下兩個原則,一是更審慎的刪繁就簡,一是在哲學的指涉中直接抒情。這樣的省思無疑將為他的作品帶來更多新的可能。
生活從八方來,詩人向一方去。他望著大隊人馬留下的煙塵,寧可選擇一條少人行走的幽徑。在言必稱「後現代」的今日文學界,張堃這個人,不怕陷入「時代的錯位」,也不急匆匆地「與時俱進」,更不搭趕任何新名目的順風船,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美學原則,誠屬難得。
其二,從人出發
周作人早年提倡「人的文學」,特別強調「闢人荒」的重要。所謂闢人荒,就是希望作家到廣大人群去墾人荒、開人礦,去發現人的真理,人的價值。周作人認為人性有強韌也有軟弱,但不管處於何種狀況,喜劇或悲劇,但人們對未來的盼望永遠不會停止,每個人總是把赤裸裸的追求和夢想推向生活的前沿。激情是可貴的,有時候錯誤的激情也比沒有激情好。人生依然神聖、美麗。
多年來的台灣現代詩,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水仙花精神」式的自我觀照,以及對存在意義的參悟。這當然是好的。但在「闢人荒」方面,表現就顯得薄弱,詩人的關懷面,小我多於大我,殊相多於共向,很少關注社會學意義的現實生活戲劇。為了彌補這方面的空白,張堃平原極目,擴大自己的文學視域,掌握「對世界的愛與希望」的寫作脈絡,推出不少新作,成績可觀。這些年他利用在外商公司工作之便,經常到世界各地作商務旅行,以詩人之眼,飽覽人的風景。他走遍了通都大邑,博物館、畫廊、作家藝術家故居、歷史上著名的文學現場,收集資料,發為創作。除此之外,他也關心基層人民的生活,流連忘返於街頭巷尾、攤販市場、貧民窟,不為別的,就只為了看人、寫人,這與周作人主張的「闢人荒」可謂不謀而合。
通常,旅遊時間比較匆促,張堃的「客中作」多半採用快筆速寫的白描方式,雖是馬上作業,卻也展現出他捕捉形象的功力。白描講求「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魯迅語),這樣的歸納,與張堃不施濃墨重彩、簡煉傳神的行文習慣特別吻合,往往寥寥數筆,就能把描摹的對象活現在讀者的眼簾。有時候時間充裕,他的人物詩便相對的長一些,且帶有詠史的性質,〈翁山蘇姬〉一詩便是一個代表。在這首詩中,詩人為這位緬甸良心象徵的女傑寫下很多「可以燃燒起來的句子」(穆旦語)。句子可以燃燒,那是因為寫它的人有一顆燃燒的心。盡管如此,他仍然以冷靜的態度來處理這個作品。骨子裡千迴百結,迭宕騰挪,但所有的激情,都壓在底流之下。而改以景語和情語交替進行,以「淺」和「緩」的方式,表現大動亂之後仰光的窒悶氣氛,手法特殊。古人論詩,有所謂「其語愈淺,其意愈切」、「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的說法,這種古典詩的技巧,被張堃活學活用了。至於「緩」,乃是一種靜水流深式的平緩,在平緩無波的下層,埋藏著電影上說的「畫外音」,戲劇上說的「潛台詞」。這樣的設計,加大了感染力,也使作品飽含更豐沛的思想含量。〈文德路的巷子〉也是一首力作,詩的主人翁是有「創世紀火車頭」、「詩壇老管家」美稱的張默,若說開人礦,張默就是個大礦藏,值得開採。獨特的人自有獨特的寫法,整首詩好像用的都是閒筆,別的不寫,只寫張默內湖家門前的那條巷子,同一個句式重覆了三次:「一條巷子」、「一條走了幾十年的巷子」和 「一條巷子走了幾十年∕最終走成了∕詩人之巷的必然結果」。層層迭進,直到詩眼出現。古人說閒筆不閒,好的詩,無一字閒著。而那個閒,也許是用來作「對應」的吧。
T. S.艾略特曾提出「客觀對應物」的理論,說在藝術形式裡表達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出一個客觀對應物,一組事物,場景或事件,具有一種特殊情感的固定形式,藉此可以喚起特殊的情感,以避免直接的陳述。寫詩人張默,沒有什麼比他家門前那條巷子更具典型性和象徵意味。「篇不可以句摘,句不可以字求」(胡應麟語),通篇應該是一個綰合嚴密有機的生命,一體成形,不容拆散。這麼說來那重複了三次的「一條走了幾十年的巷子」,便成了不是佳句的佳句,功在全篇,不可小覷。
〈人物素描六幅〉,一口氣側寫了六位台灣當代女詩人,未註明寫的是誰,讀者一讀就可以呼出名字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趣味盎然。這樣的功夫要善於寫真,才能勾勒得如此唯妙唯肖。主要的是作者對每位詩人的精神世界,體會深刻,才能出現神傳寫照的點睛之筆。如果只寫人而忽略了詩,少「情實」而多「故實」,那就成了浮面的掠影,無法入木三分,少了回環往復的想像空間。又因為是詩人寫詩人,是從詩到詩的一種再創作。張堃遂把整輯作品定調在似與不似之間,「似」是實,「不似」是虛,虛實相互生發,作者才能自抒機杼,熔裁諸家詩境,把素描對象著上「我」之色彩,以延伸出更豐富的不盡之意。這也是闢人荒更積極、更富創造性的意義吧。
〈達賴喇嘛十四世〉是一首典型的開礦之作。此詩「以氣勢為主,不以字句為主」(蘇東坡語),這裡說的氣勢不一定是縱橫恣肆、閎衍浩大一類,而是一種整體的氛圍,無關乎規模的大小。張堃緊扣這一點,全詩都是主人翁的獨白,充滿了戲劇性,也使文勢飛動流轉,在平鋪直敘中凸顯了題旨,這是非常高明的寫法。也使我想到早年五四詩人卞之琳純粹用「大白話」寫的詩,他的名句「下雪了,真大!」,至今為人稱道,因為任何形容詞也比不上這句村頭街坊上的尋常語形象。語言極簡主義的張堃似乎不讓前輩專美,而在音情理趣上有更多的設計。
其三、靈瞬之美
在張堃和我很多次的長談裡,比較少觸及到靈瞬的問題。不過在張堃的詩中,時常隱現出類似靈瞬的審美經驗,我甚至想稱他是一位靈瞬的詩人。
靈瞬,本是西方宗教術語,意思是神祇顯靈,後來也用在文學藝術的討論上,意義也變得廣泛,凡人在思考時出現那一剎那的洞見,或對事物的真諦有所頓悟,均可稱之為靈瞬現象。事務不分大小,甚至日常生活的枝枝節節,瑣瑣細細,也能引起心靈的悸動,靈瞬的閃現。不一定天君泰然,精神澄澈才叫靈瞬,心事浩茫,無以自解,不知何適何從,也可以稱之為靈瞬經驗或靈瞬症候。張堃在本書中帶有佛理和禪味的詩常常流露這種美感意識,有時候還加上一些東方的倫理,如此更把靈瞬提升到救贖的層次。這就接近泛宗教的領域了。
張堃詩中的靈瞬經驗,自然與西方的宗教無關,與佛門的「靈覺」、「靈應」、「靈異」也大異其趣。他當然也不是一個耽於神秘的神秘主義者,不過中國文學上的「心領神會」、「妙對通神」、「遷想妙得」、「登山則情滿於山」的境界,他都觸及到了。這樣的「如有神助」,乃是在心智高度集中下,窮究事物的內在本質所閃現出來的現象,是感性的絕對誠實獲得的成果,是「大哉問」換來的「大哉答」,再以納須彌於芥子的方式,將它壓縮在短小的詩型中。精省的語言加深了詩的純度,而展現出一種淡永靜穆的意境,低沉諧美,氣完神足,令人為之神往。如此的美學效果,非靈瞬而何?
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短詩易寫難工,高明的作者表面上神閒氣定,看似閒閒敘寫、不事張揚,但他們的內在都具備一種曲筆隱忍的功夫。所謂行散而神不散,絕對不可以浮想雜感視之,而是長期沉澱後厚積薄發的菁華。不妨試作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我們進入張堃的練功房(通常練功房是不讓外人進入的),心想他的練功處一定擺滿了槍刀劍戟三節棍流星錘。結果仔細一看,四壁蕭然、空無一物,除了因長久研讀而磨破了函裝封套的一部佛經和論語老莊外,沒有別的東西。但是也千萬不要據此而判斷他作品缺乏現代元素,他是一個周遊世界的人,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的詩藝來自多方面的師承,有些是跨行學習得來的,西方文學中的詩、小說、散文、戲劇,甚至現代電影、現代繪畫,他都有所涉獵,並進入他的創作實驗中。張堃最喜歡的題材就是訪舊,看老朋友、重臨住過的老房子和他童年玩耍的地方,其中關於時間的流逝、今昔之比感受特別深刻。這種感覺最宜用電影上的淡入淡出、化出化入、切出切入、定格、深鏡頭等等的手法來處理,以保持他旋律流動的快速,時空轉換的靈活而又不失簡潔的風格。此外,張堃的詩對於顏色特別敏銳,有一種特殊的暗調和漸層的色感,他喜歡寫黃昏、夕陽、暗夜,所以很自然地採用了現代繪畫的視覺藝術、偶發藝術、拼貼等手法。雖然有這麼多元的影響,但最後他還是要統調在樸素的整體風格中,務必做到只見性情不見技巧,不是技巧的賣弄,而是技巧的隱藏。張堃常思索古代論詩者說的「無意工而無不工」,如果刻意求工反倒不工了。他也完全贊同詩詞研究學者葉嘉瑩說「作詩」和「做詩」絕對不可以混用,「作詩」是創作,「做詩」是造作,前者是詩的領域,後者是工匠的範疇了。
靈瞬經驗也常常出現在張堃一些悼亡傷逝的作品中,他悼商禽、念秦松、哭大荒,痛友痛己之外,更把頌讚惋惜之情錯落有致地表露出來,並找出亡友生前鮮為人知的行誼加以彰顯,謹厚大度,一片率真。君子交,兄弟情,文人相重,應如是。
張堃有三首悼念他母親的詩,字字悲愴,嗚咽頓挫,讀後令人潸然淚下。其中〈夕陽已冷〉:「從你陽台望去∕最後幾年的落日∕一年比一年沉重∕你卻說∕一年比一年輕了∕∕我不解∕落日何以變輕∕難道妳早就看到那抹晚霞∕已燒成了灰燼?∕∕從妳陽台望去∕陪伴妳的晚風不再吹起∕流雲也不再飄浮∕夕陽真的冷了之後∕孤星滅了∕寒月沉了∕陽臺外∕除了不醒的永夜∕∕空了」。另一首〈媽媽,對不起〉,最後一節:「這回送你∕你一直微笑,不再哭了∕我一直跪著,不再揮手∕千言萬語也只有一句∕媽媽,對不起」。面對著永訣的時刻,語言已經無濟於事,一句「媽媽,對不起」有千斤之重,再多的語言都沒有意義了。
且讓靈瞬閃現出的一條無形臍帶,緩緩向西,跨過那永隔的幽明。
附記
一:張堃在他的詩集《調色盤》後記〈也算是詩路歷程〉中說:「詩是一種追求、一種探索。那麼,我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生活的紀錄,呈現了對世界的熱愛與希望,應該也算是我生命中的追求與探索的一部分。」這段話決定了張堃詩美學的三個向度。
二:早年詩人羅青送瘂弦一幅水墨小品,題為〈霧失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