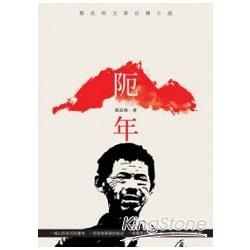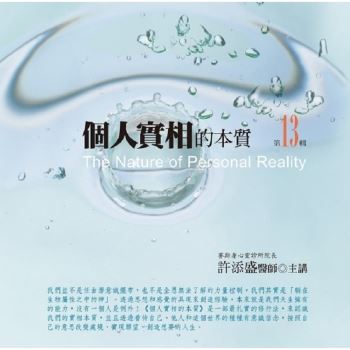題記
人們說「文革」發生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無論國內國外,有人研究是好事,怕的不研究,都忘掉。我曾跟一位當今文科的博士生交談,說到「農業學大寨」,居然不明白怎麼回事。什麼是博士?我孤陋寡聞,答曰:「讀書讀上頂的人」。天吶,一般人還情有可原,讀上頂的書生說不知道,著實讓人駭了一驚。
我跟季羨林先生有同樣感受,他的《牛棚雜憶》許多人讀後禁不住淚流滿面,然而他們的子女讀了卻說季羨林在寫小說,在胡編,在造謠。他感到了吃驚,說:「這一次十年浩劫是中國歷史上最野蠻、最殘暴、最愚蠢、最荒謬的一頁;是中華民族空前絕後(這是我的希望)的大災難。它把我們國家推到了瀕於破產的邊緣上。我們付出的『學費』不可謂不高矣。然而學到了多少東西?得到了多少教訓呢?現在看來,幾乎沒有。」(《千禧文存.龍抄本《牛棚雜憶》序》新世紀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5頁)
驚恐過後我再細想,事非經過不知難,叫人家怎麼說呢?譬如那會兒的口糧結構、定量的標準、集體與社員分紅的比例等等,要我這個親身體驗過的人準確回答出來,恐怕也難得交個好卷。況且如同家裡的家私,大人叫不准傳的事就不能傳。沒有經歷,沒有渠道,責怪年輕人就失去了應有前提。
「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以糧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都是「農業學大寨」的重點內容,是「文革」在農村的具體表現,是殃及中國八億農民的罪魁禍首--簡而言之,它就是農村的「文革」。
我參加過紅衛兵破「四舊」運動,在「農業學大寨」紅旗下種過田,承受過賣柴扣口糧的懲罰,鍋裡煮過清水,看到過餓死在田間的大漢……這一幕幕人間的大劇,既沒給老百姓好處,也沒使人變得聰明,待影響到我的一面,倒是真正弄懂了一個字的涵義:餓!「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
一九八二年,中國農村盼來了土地變革--「大包乾」。這一年我擁有了四畝的土地,當我捧起潮濕的泥土,湊到口鼻跟前吸食它誘人芳香的時候,竟一時醉意醺醺,差點像范進中舉帶出痰氣而轉了狂--因為我從此吃上了飽飯,跟那個壓迫我幾十年、淫威我幾十年的春荒告了別!老輩子告誡我們:「吃上飽飯不能忘記餓肚子,忘記餓肚子,飽飯就吃不長久。」為了不使那段艱苦歲月像迷霧一樣被夜風吹散,為了飽飯吃得長久,責任同義務便一起來到我的肩上。文學的意義就在於對生活的記憶和呼喊。呼喊我沒有學識的底氣,記憶倒還能勉強為之。於是便沿著我生活的路子,一步步走了下來,記錄了我的一份粗糙生活,同時也記錄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荒唐歷史。
無論歷史的、文學的寶塔都應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之上,當我們在向它添磚加瓦時要捫心自問:手中的材料接受過烈火的燎烤和鍛鍊嗎?有鋼的質地嗎?有金的純真嗎?只有如此的材料構建寶塔,狂風才吹不垮,暴雨淋不壞,立於世界之林,無愧!
二○一一年十二月於興山古夫桂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