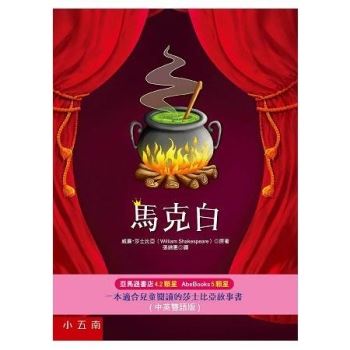我懷著灰暗的心情走完了餘下的兩天路程。
邁阿密的海藍得不真實似的,高高的棕櫚樹搖曳生姿,陽光普照的海灘上擠滿了遊客,年輕的女郎穿著細細一線的比基尼在沙灘上打排球,古銅色的胸脯和大腿塗了防曬油閃閃發亮,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忘記一切的狂歡的氣氛。青春的記憶是短暫的,人生途中有那麼多的峭壁和險灘,那麼多的陰霾風浪,何不乘此時此日盡情享受?這兒崇尚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兒的女人賣弄豐乳肥臀,隨時準備叉開大腿,這兒的男人眼睛像探照燈般地掃射,恨不得用陰莖代替大腦。邁阿密是北美洲的嘉年華,是有錢人的銷金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沉浸在聲色光影和醉生夢死之中。
我坐在白色的遮陽傘下抽煙,面前是一瓶冰涼的海尼根啤酒,喬埃要我在這兒等他,我們會一起去港灣裡看他那艘剛下水的船——文藝復興號。
比基尼女郎們踩著高跟鞋在我眼前來來去去,健美的胴體,淡金色的頭髮在微風中揚起,修長的手臂大腿,比基尼嵌在股溝裡,露出整個渾圓的臀部,乳房隨著步伐一步一顫,像一匹匹發情的母馬昂首挺胸地行進在被太陽曬得發燙的人行道上。
我眼前卻浮起金妮那無助的眼神,像鳥一樣望著外面碧藍的天空而振翅無力。我好像看見她被湯姆們送進那個像冰窟般的醫院,頭髮被剪得短短的,換上囚衣似的病人服,面無表情地被逼著吞下一把又一把的化學藥物,我好像看到她在醫院的視窗徘徊不去,幻想如何從高處一躍而出,一雙天使的翅膀穩穩地將她托住。這兩天我內心一直責備自己,在整個旅途中我應該對她更溫柔一些,像最後那個早晨,金妮是那麼地柔順平靜。而我卻為了點小事而驚慌失措地去打電話給湯姆,使得她又被關進那個該死的籠子裡去。她真應該跟我們一塊去義大利,去到她年老的祖母身邊,到那山谷環抱的古老城市中去休生養息,她會一點一點好起來,重新拾起她的花樣年華,而把過去的噩夢留在三藩市。老天,我做了什麼樣的蠢事啊。
神思恍惚中一回頭,看見喬埃站在我的身邊,他穿著大塊鮮豔色彩的襯衫和黑色絲綢短褲,頸項上粗大的金項鏈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他熱情地跟我大力握手,我囁嚅地抱歉沒能把金妮帶過來,喬埃的眼中閃過一抹憂傷的神色,但很快地隱去,他面無表情地聳聳肩說:「天主會保佑她,湯姆會很好地照顧她,我們只能為她禱告。我想不起其他事我們可以做的。」他很快地在胸前劃了個十字。把我帶到一輛敞蓬跑車邊上,拉開車門:「現在去看看我的新女朋友,在接下去兩個月裡,她將日日夜夜地陪伴我們飄洋過海,去到那不勒斯完成我的夢想。」
沿著海濱公路,我們來到一個泊滿遊艇的港灣,望過去桅檣林立,一陣輕風而過,船上的索具叮璫聲一片,我們走下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道盡頭處有一扇鐵門,喬埃取出鑰匙打開門鎖。沿著浮橋來到遊艇區的最盡頭,我看見了「文藝復興」號流線型的船身。
這是一艘七十英尺長的大型遊艇,船身漆成乳白色,船頭上用花體字漆出Renaissance的船名。一個彪悍的男人赤裸著上身,正用一條水管在沖洗甲板。我們踏著跳板上船,喬埃介紹那叫哈尼的漢子說他是船長,哈尼伸出手來歡迎我,他的掌心滿是老繭,像銼刀一樣。從他體型上看來還很年輕,肩膀上全是壘壘的肌肉,但胸口上的胸毛全白了。近看那張臉上刻著叢橫的皺紋,像個鐵鑄的胡桃,一口牙齒倒是雪白。哈尼講起英文來有很重的口音,喬埃說他是葡萄牙人,跑了三十多年船。我們橫度大西洋就全靠這個老水手了。
我跟在喬埃的後面參觀了這艘藍白相間的船,船上到處被哈尼收拾得一塵不染,所有的金屬部件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鑲木板的船艙散發著松節油的氣味,在前甲板上的駕駛室配備著最新式的導航儀,自動駕駛器,無線電對講機,甚至一部小型的雷達。在駕駛台上方,供奉著一尊聖母瑪麗婭的塑像。哈尼打開引擎,對喬埃說他剛試測過改裝的發動機:「你聽聽聲音是多麼地平順。」喬埃告訴我說這艘船有兩部發動機,也可以像傳統的遊艇升起船帆靠風力航行。我們沿著狹窄的舷梯下到船艙下面,靠後面是引擎房和儲物間,走道旁邊是個小小的洗浴設備,靠走道前半部是個較大的船艙,有個用電爐的小廚房,吃飯的桌子固定在地板上。我問喬埃我們睡在哪裡?喬埃打開儲物櫃上的一塊木板,露出一個像棺材那麼大的空間,鋪著一條軟墊:「這就是我們的總統級套房。」哈尼說我們還需要一個水手,晚上輪班掌舵,所以這小小的空間要擠四個人了。
接下去幾天我幫著哈尼採購航海的必需品,我們的儲物室塞滿各種各樣的蔬菜罐頭,大瓶大瓶的瓶裝水,一大堆粗粗細細的繩索,用巨大塑膠桶裝的備用柴油和潤滑油,一個冷凍櫃裝著凍得像石頭一樣的牛排和三文魚。前艙大大小小的櫃子裡藏著紅葡萄酒,香煙,和醫藥用品。喬埃把櫃子仔細地上鎖,鑰匙則只有他和哈尼才有。
在啟航前三天哈尼找到了他的助手,一個滿頭紅髮的澳大利亞人,膀大腰粗的橫蠻傢伙,臉上滿是雀斑,身上佈滿刺青,一條巨大醜惡的龍從脖子一直繞過胸膛盤到腰際,名叫尼爾,講一口粗魯難懂的澳大利亞英文。哈尼對他並不是十分滿意,說他的經驗還不夠,但是啟航在即,沒辦法再挑揀下去,尼爾成了我們遠征軍的第四個成員。
臨行前一天,喬埃請來了個天主教神父做彌撒,為Renaissance遠行祝福。那個神父穿著紫金二色的道袍,嘴裡念念有詞,把手中的聖水灑向船的每個角落:「天父保佑船頭,使她能辟開萬傾波濤,順利航向目的地。天父保佑船尾,使她能產生足夠的動力。天父保佑風帆,使她乘風破浪。天父也保佑船上每一個乘客,使他們身體平安,愉快地完成航行。阿們。」喬埃和哈尼都低著頭,用手在胸前劃著十字。尼爾避得遠遠的,我則嘴裡含糊不清地咕嚕一句,心不甘情不願地在胸前飛快地做了個手勢。
預定是第二天早上十點起航,哈尼在九點就發動引擎暖機,但十點十分還不見喬埃的人影。好容易在十點半時一輛計程車在岸邊停下,鑽出車廂卻不只是喬埃一個人,另外還有個黑頭髮女人,提著一個小提箱。上了船之後喬埃簡短地向大家介紹:「這是索妮婭,她搭我們的船去那不勒斯。」
我真希望當初沒答應喬埃乘船去義大利,我從不知道自己會暈船暈得那麼厲害,一出海兩個小時我就睡倒了,五臟六肺像兜了個底,吐了無數次。哈尼給了我一個大塑膠袋,讓我吐在袋裡。胃裡的東西都吐光了,就吐清水。小小的鋪位像個水泥攪拌機,躺在上面直覺得天旋地轉,渾身冷汗。每一陣顛簸都使得我胃裡翻騰不已,捧著酸臭的塑膠袋直嘔,到最後連清水都吐不出來了。
哈尼弄了兩片藥丸讓我吞下,說:「沒關係,初次出海的人都是這樣,三天之後你就滿甲板跑了。」我服下藥之後蒙頭大睡,天昏地黑地好像要一路睡到世界盡頭。亂夢連連中那個天主教神父一臉獰笑:「你對天父敷衍了事,天父也對你敷衍了事,你吃的苦頭是自找的。」我想我日後對天主教的反感就是被這個夢裡氣量狹小的神父逼出來的。
昏頭昏腦不知睡了多久,哈尼跑來一把把我拖出鋪位:「夠了,你這樣睡下去會起不來的,總要學著慢慢適應,去甲板上透透氣,人都發霉了。」我拗不過他,勉強爬起身來,高一腳低一腳地爬上舷梯,來到甲板上。
觸目所見的是一片藍色,藍得使人暈旋,天空低低的,像張深藍色的網罩在萬傾碧波之上。遠方的海面上泛著一片耀眼的銀光,近處的水面上卻波濤洶湧,藍色的浪頭一波一波湧來,在船舷邊拍出很響的聲音。船上的馬達平穩地運轉,在船後拖著一條白色浪花,幾隻海鳥跟隨著船上下飛舞。
極目望去,一點陸地的影蹤也看不見,也不見一片帆影。天地間就我們的船像個雞蛋殼一樣漂浮在無邊的洋面上。引擎聲單調而繼續地鳴響,感覺上船卻像凝固在海上一動不動。我突然有個錯覺——船上的推進器失靈,我們要困在這茫茫無際的大海中了。直到船後的浪花濺到我臉上,才從怔忡中醒轉過來。
我彎下腰,小心地扶著船舷的欄杆,向前甲板走去,路過駕駛艙時,看見紅頭髮的尼爾戴了一副很大的太陽眼鏡,嘴上叼著一截香煙屁股,專心致志地在掌舵,喬埃,哈尼都不知所蹤。
我背靠駕駛台坐下,耀眼的陽光使得我閉上眼睛,身上暖烘烘的,自己都聞得到胳肢窩裡騰起的酸氣,上船之前哈尼就告誡我們要節約用水,一個星期只能洗一次澡,不知能不能想辦法先去洗一次?這樣滿身臭味自己聞了也想吐,怎麼走到人前去。
伸出手來,我看見自己的手指肚都癟下去了,嘔吐使人脫水。人虛弱之極,眼前還是金星飛舞。我摸了摸口袋,掏出包擠得扁扁的香煙,挑了根還算完整點的點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辛辣的煙氣直衝腦門。看看手中那包不成形的香煙,隨手往船舷外一扔。
一個黑色的身影一閃,身手敏捷地接住半空中的香煙,我定睛一看,是喬埃臨開船時帶上來的那個女人,這兩天暈得糊裡糊塗的,根本忘了船上還有這個人存在。
她把香煙放在鼻子下聞了聞,又扔回給我:「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也許需要這包香煙,不要忘記我們現在在海上。」說完徑直走到船頭坐下,把個背影對著我。
從背後看過去這女人瘦瘦的,腰和臀部的線條還不錯。很難說出她的年齡,大概三十多歲,黑色的長髮垂到腰際。據我的記憶,她長得不算難看但也說不上好看,完全不是喬埃平日所交往的那種頭腦簡單的美女,她在啟程最後一刻上船,看來連哈尼也不知道我們會有一個女人同行。那麼她在船上是怎麼樣一個角色呢?喬埃的義大利親戚?搭順風船的旅客?走私人口?廚娘?或者乾脆是喬埃在邁阿密找來的古巴妓女,以解決長途航程中的寂寞?她叫什麼來著?
正在我苦苦回想這女人的名字時,她回過頭來,嘴上叼著一支沒點燃的香煙,我彎腰把我手中的香煙遞上,她接了過去,對上火,點了點頭又轉身回去。我在她遞回香煙一刹那時看到她的眼睛,那是一副使人迷惑的眼睛,深黑色的瞳仁,在瞳仁的深處閃著一股冷冷的光芒,冷得使人覺得不像是活人的眼光,而像一個古老的幽靈,隔著時空在遠處窺視你,不但窺視你的外表,連你的內心都被她看得一清二楚。我沒來由地突然打了個寒噤,一個名字躍入我腦際——「索妮婭」。
我幾天來第一次坐到那張小小餐桌邊,晚餐是喬埃烤的牛腰肉和土豆泥,加上罐頭蔬菜。每人發一瓶礦泉水,葡萄酒卻隨便喝。尼爾在上面掌舵,喬埃和哈尼討論一切順利的話,還有一個禮拜我們可以通過直布羅佗海峽,索妮婭坐在我的對面,靜靜地低著頭吃盤中的食物。偶爾抬起頭來,不等我捕捉到她的眼光又垂下頭去,帶著一副迷一樣的表情。
喬埃坐在她的身邊,我仔細看了看他的瞳孔,雖然也是深色的,但喬埃的眼珠在光線下呈現棕褐色,還透著一絲灰中帶綠。相比之下,索妮婭的眼珠是帶著煤黑色的褐色,像口井一樣深不可測。她的眼皮厚重,鼻子稍微帶點鷹勾,臉上骨架分明,基本上不參與喬埃和哈尼的談話,間或目光一閃像探照燈穿透帷幕似的。
喬埃和哈尼都對她彬彬有禮,沒有任何的狎戲的舉動或言語上的輕薄。但也沒有和她有任何交流,仿佛她根本是個買票上船不相干的乘客而已,用完餐之後我拿著紙盤子去扔掉,看到她在後甲板上抽煙,一雙眼睛炯炯發亮,像黑暗中的貓頭鷹一樣。
我漸漸地適應終日搖晃的生活,暈船不那麼不可忍受了,在風平浪靜時我來到上甲板抽煙曬太陽。眯著眼睛看遠遠的海面,一片單調的藍色。為了打發大把的時間,有時和喬埃,尼爾和索妮婭玩紙牌,索妮婭老是贏,沒人是她的對手,那雙黑眼睛好像能看穿你手中的每一張牌。尼爾輸得最多,欠了索妮婭不少錢。不打牌時我為哈尼和尼爾畫頭像速寫,索妮婭在一旁頗有興趣地看著,叫她坐下來卻無論如何不肯。
一個禮拜過去了,連陸地的影子都沒看到,喬埃用詢問的眼光看著哈尼,哈尼含含糊糊地不敢肯定他的航線是否正確了,所有的儀器都指出離大西洋東岸還有一千二百多海裡,走了一天一夜之後還是一千二百海裡,哈尼把資料讀了一遍又一遍,臉上顯示出一股迷惘的神情。喬埃緊張地問他怎麼了?哈尼說航線應該沒問題,太陽每天早上從船頭的右舷升起,晚上又落入船尾的左面。我們是朝著東北方向航行,這條路線我以前也走過,不知為什麼這次像鬼打牆一樣。
船上大家都緊張起來,喬埃宣佈為了預防萬一,每人每天三瓶食用水減少為一瓶半,並且取消洗澡,平時的食物份量也顯得少了。哈尼一天到晚憂心忡忡,手上拿了把航尺規在海圖上量來量去,嘴裡不斷喃喃自語。喬埃一遍一遍地檢查儲存的食品,開飯時分到每人盤子裡的東西精確得不能再精確。尼爾,平時一直沉默寡言的,現在卻活躍起來,有一天他跑到我的鋪位上,低聲說道:「中國人,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困在這裡?」
我諤然地望著他:「為什麼?」
尼爾左右看看沒有人,把手往天花板上一指:「因為我們船上載了個巫婆。」
「你是指索妮婭?」
尼爾點點頭:「不是她還有誰,打牌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女人有問題,所有的牌都像被她透視過似的。只有吉普塞女人有這個本領,而吉普塞女人十個有十個是女巫。」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丁托雷托莊園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99 |
文學小說 |
電子書 |
$ 224 |
小說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奇幻小說 |
$ 288 |
小說 |
$ 288 |
華文奇幻/科幻小說 |
$ 288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2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丁托雷托莊園
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受委託臨摹文藝復興時期大畫家丁托雷托的作品,來到義大利丁托雷托莊園。
坐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突然有一種茫然莫名襲來,我是誰?
我怎麼會來到這個地中海邊小山莊的?
真的像喬埃說的會有個紀念館在這兒建立起來嗎?
還有,在屋裡的那個女孩子又是誰?
我在兩個禮拜之前還不知道有這麼個女孩存在。
而剛才她那麼緊地貼在我胸前,鼻息裡還存有她頭髮上的味道。
本書特色
1.人物刻劃鮮明,書中人物性格強烈,加上故事情節的戲劇張力足夠,主角帶領著讀者,猶如親身經歷過貪婪、誘惑、欺騙、背叛、死亡。
2.如同驚悚片般的劇情。有時感覺像穿梭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和文明的世界。傳說的女巫好像真的存在,隨時會呼風喚雨。純潔的少女所處的伊甸園其實是魔鬼的引誘。身邊所看到的事物一瞬間全和自己所認知的都不相同。
作者簡介:
Victor Fan范遷
現居美國,作家,畫家。著有《錯敲天堂門》《古玩街》《桃子》《風吹草動》《失眠者俱樂部》等多部長篇小說及《三藩市之吻》《聊齋新章》中短篇小說集。
章節試閱
我懷著灰暗的心情走完了餘下的兩天路程。
邁阿密的海藍得不真實似的,高高的棕櫚樹搖曳生姿,陽光普照的海灘上擠滿了遊客,年輕的女郎穿著細細一線的比基尼在沙灘上打排球,古銅色的胸脯和大腿塗了防曬油閃閃發亮,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忘記一切的狂歡的氣氛。青春的記憶是短暫的,人生途中有那麼多的峭壁和險灘,那麼多的陰霾風浪,何不乘此時此日盡情享受?這兒崇尚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兒的女人賣弄豐乳肥臀,隨時準備叉開大腿,這兒的男人眼睛像探照燈般地掃射,恨不得用陰莖代替大腦。邁阿密是北美洲的嘉年華,是有錢人的銷金窯,一天二...
邁阿密的海藍得不真實似的,高高的棕櫚樹搖曳生姿,陽光普照的海灘上擠滿了遊客,年輕的女郎穿著細細一線的比基尼在沙灘上打排球,古銅色的胸脯和大腿塗了防曬油閃閃發亮,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忘記一切的狂歡的氣氛。青春的記憶是短暫的,人生途中有那麼多的峭壁和險灘,那麼多的陰霾風浪,何不乘此時此日盡情享受?這兒崇尚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兒的女人賣弄豐乳肥臀,隨時準備叉開大腿,這兒的男人眼睛像探照燈般地掃射,恨不得用陰莖代替大腦。邁阿密是北美洲的嘉年華,是有錢人的銷金窯,一天二...
»看全部
作者序
那年我二十一歲。
坐在電腦前打下「丁托雷托莊園」這個標題時,我不由得嘴角牽動起一絲苦笑;二十一歲的年華在螢幕裡看來是那麼遙遠,遙遠得像漂浮在地平線上依稀的夢,一個燠熱夏夜的夢,雷聲隱在雲層裡,空氣中飽含著水分。身體懶懶地睡著了,潛意識卻在黑暗中分外活躍。
當我走過一長段磕磕絆絆的人生之後,突然明白了能做夢是一種福氣。夢不帶有善惡和道德的評價,夢不帶有日常功利和經濟考量,夢只描繪一種美麗,夢闡述一種與生俱來的慾望,在夢中我們赤身裸體,像安琪兒一樣。也許那是一個更真實的我們,自由地遊走在現實和虛幻之...
坐在電腦前打下「丁托雷托莊園」這個標題時,我不由得嘴角牽動起一絲苦笑;二十一歲的年華在螢幕裡看來是那麼遙遠,遙遠得像漂浮在地平線上依稀的夢,一個燠熱夏夜的夢,雷聲隱在雲層裡,空氣中飽含著水分。身體懶懶地睡著了,潛意識卻在黑暗中分外活躍。
當我走過一長段磕磕絆絆的人生之後,突然明白了能做夢是一種福氣。夢不帶有善惡和道德的評價,夢不帶有日常功利和經濟考量,夢只描繪一種美麗,夢闡述一種與生俱來的慾望,在夢中我們赤身裸體,像安琪兒一樣。也許那是一個更真實的我們,自由地遊走在現實和虛幻之...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范遷
- 出版社: 釀出版 出版日期:2013-01-16 ISBN/ISSN:978986597699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4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