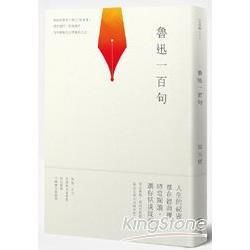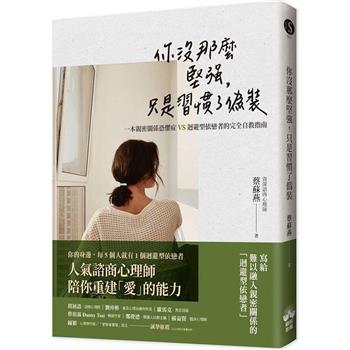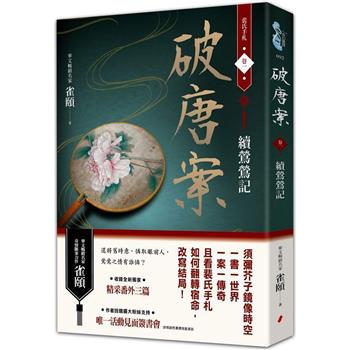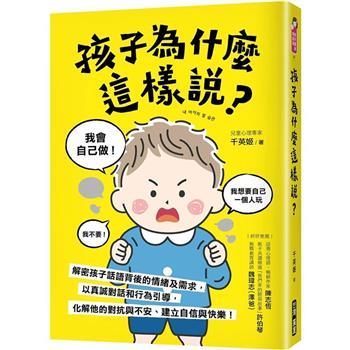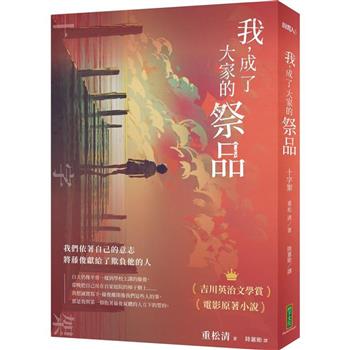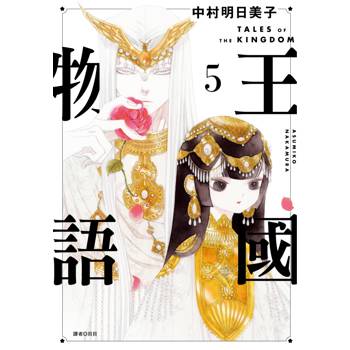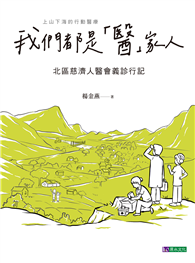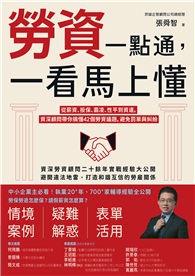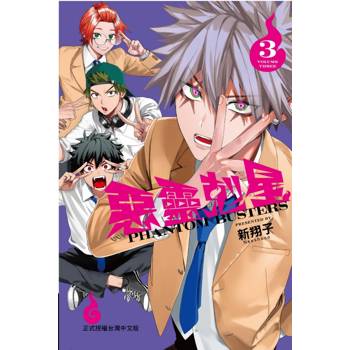引言
解讀者言
研討魯迅,高頭講章尚矣,但文辭之美,尤堪玩味;棄如微末,至可惜也。此「一百句」萃取疏解,偏重文辭,不敢謂盡得原著之精神;照隅識小,或可當愚者之一得。
譬如〈「來了」〉一篇,批評中國無真實之主義,唯報導主義「來了」之叫嚷。叫嚷不斷,「來了」亦不斷,故最終來了的,唯有「來了」。此等立論,痛快何似,豈 「老吏斷獄」可比;然究其神髓,仰賴「文字遊戲」多矣;而文辭之美,兼收於思想啟 迪之外。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雲:「語言總在說出它自己。」日常言談隱含無量啟示,深察細味,善用此天然富藏,使奧妙之事暢快表出,文章家之能事,莫過於此。
蔡元培序《魯迅全集》,特以「用字之正確」概括其天才,每為論者所不解。其實「用字之正確」豈屬末技。魯迅論詩,主張「實利離盡,究理弗存」,自謂其文只是 「悲喜時的哭歌」,「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真精神直追〈毛詩大 序〉和陸機〈文賦〉標舉的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然「嗟歎」、「詠歌」、「舞之」、 「蹈之」、「緣情而綺靡」者賴何?文辭而已。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謂文學「須言之有物」,「物」者,「思想感情」也。但光有「思想感情」可乎?章太炎批評宋以後作家「不懂小學」,「文辭也不能動人」,也 許把「小學」抬得太高,但以「動人」與否在乎「文辭」,見識卓絕。作家文辭荒蕪而 想以別種手段感動讀者,謬矣。文辭動人,哪怕墮落為幫忙幫閒,仍然可取——此點魯迅雜文〈從幫忙到扯淡〉論之頗詳。
但魯迅認為漢語本身不精密,須大量引進西方邏輯語法。〈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結語:「我敢將唾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裡,借 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就是一個實踐。三十五個漢字的「定語」包含多重轉折,並非同義重疊,這等造句法,「五四」至今,絕無僅有。 若論「歐化」,誠然「極端」,卻非「惡劣」。吾人讀之,不但不拗口,反覺錯落有 致,聲調鏗鏘。漢語學習域外語言之空間與彈性很大,然亦唯善學者,方能出奇制勝。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紀念劉和珍君〉所謂「出離憤怒」之後的曠古奇文,而因「神聖的憤火」(胡風語)的淬煉,愈見 燦爛。論其妙絕,已非單純「煉字」,亦不僅依託西文邏輯語法,而植根於中國文章 特有的排比、對偶、雙聲疊韻的悠久傳統,亦即周作人所謂「因了漢字而生的修辭手 段」。
民初,太炎弟子進入北京學界,中國文風,從此丕變。他們崇尚六朝文章,作白話文也特別講究藻采氣勢,與喜好唐宋古文的「桐城派」成對壘之勢。錢玄同痛罵「桐城 謬種,選學妖孽」,掊擊「桐城」是真,捐棄「選學」是假。周作人上世紀四○年代初作〈漢文學的傳統〉,繼續聲討「謬種」,對「妖孽」卻網開一面:「至於駢偶倒不妨 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於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 點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郭紹虞深得周氏用 心,二○年代,探索「中國文學與漢字之關係」,於雙聲疊韻,特多發明,五○年代初並提出「白話賦」的構想,念念不忘從漢文學傳統尋找新文學可資利用的資源。有此識 見者,代不乏人。白話文通過這一系的努力,向古文繼承遺產不少。
現代作家,善用排比對偶與雙聲疊韻者,無人能及魯迅。「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只是一個著例,全集中他自己所謂出於積習的「對子」,不勝枚 舉。《野草》諸文,幾乎全用嚴格對稱。但魯迅文辭,並不倚賴某一方面,雙聲、疊 韻、排比、駢偶之外,還有根基於《楚辭》、漢賦與「小學」的「煉字」,變化西語繁 複語法(李長之所謂善用「關聯詞」而使多重複句聯絡一氣),「向活人唇吻學習」的 新鮮潑辣的口語——中西古今,熔鑄配合,韻散雅俗,存乎一心,隨物賦形,盈科以進,收放張弛之間,常予人新鮮刺激,可以針勞,可以藥倦,作者讀者之心遂綸結一 體,不覺其隔。文辭至此,曲盡其妙矣。
魯迅,我嘗終日與人而論之,不如須臾讀其文章也。魯迅文章,我嘗終日而讀之,不如把握其思想感情也。魯迅之思想感情,我嘗終日而玩索體貼之,不如涵泳記誦其格 外鏗鏘精悍之警策句段也。研讀魯迅,章句之儒不可哂。何哉?蓋魯迅文學之精髓,泰半在其煉字之用心,造句之奇崛,音節色澤變化之自然而豐饒,以至寫情狀物之絕少滯礙也。
郜元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