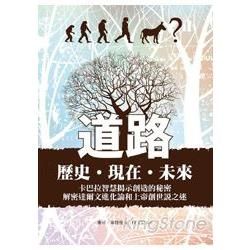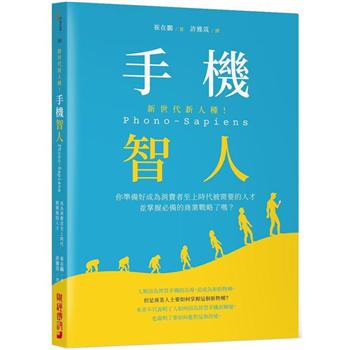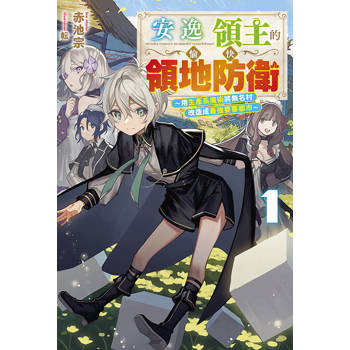卡巴拉智慧揭示創造的秘密
解讀達爾文進化論和上帝創世之謎
《歷史‧現在‧未來》從卡巴拉智慧的嶄新視角,縱覽了整個宇宙創造的過程和人類歷史的關係,揭示了那個驅動了生命起源和進化的隱藏著的力量。在對創造者和創造物,也就是給予的願望(利他主義)和接受的願望(利己主義),這兩個宇宙中唯一存在的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的解讀當中,讀者不但可以瞭解創造和生命進化的秘密,還可以看到我們人類在這整個宇宙創造和進化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為什麼我們人類歷史是過往這麼一種痛苦的歷史的背後秘密;我們人類又為什麼會在今天處於一種全面的危機當中;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清晰地「看見」創造者將引領人類到達的將來是什麼,危機與歷史事件,現在狀況和人類未來的關係,我們人類的自我在整個進化過程中的變化和作用。我們人類目前面臨的危機只有在真正「看見」將來的情況下才能知道如何去化解並同時步入一個幸福的未來。
透過閱讀本著作讀者還可以對達爾文的生命進化論和《聖經》的上帝創造論之間存在了幾百年的矛盾有一種全面的認知,從而真正解開宇宙創造和生命意義之謎。
作者簡介:
當代最著名的卡巴拉學家麥可.萊特曼 博士
麥可.萊特曼是本體論和知識理論的教授,擁有哲學和卡巴拉科學的博士學位。萊特曼博士在過去的三十多年時間內,對卡巴拉科學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他已出版了四十多本卡巴拉科學著作, 並以幾十種語言在全球範圍內發行。
萊特曼博士在很多年前就預見到了人類現在面臨的危機狀態,並成功預測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且在2008年就警告人們採用那種過去曾經成功應對危機的方式不但不會解決目前的危機,而且會引發更大的危機,而這正是現在正在不斷惡化的歐債和美債危機..
為了指引人類正確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全面危機,萊特曼博士領導的阿斯拉格研究會(ARI)正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合作以提供人類在應對當前的全球化帶來的越來越巨大的挑戰所需要的在教育方向上做出的調整。並為解決危機提供唯一他認為可行的解決方案。
卡巴拉科學在被隱藏幾千年之後在今天出現並開始在世界流行,為的就是向人們揭示隱藏在自然中的客觀規律。從而透過揭示人類一直渴求的自然規律,幫助人們應對全球性危機的挑戰,發現宇宙創造和生命存在的意義。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人類對於一的追求
2008 年8 月,當自1929 年大蕭條發生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爆發時,許多知名政要和金融家強調團結與合作的必要性。他們呼籲限制主導華爾街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框架的必要性,並且表達了對分裂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擔憂。如標題是「世界領導人尋求團結抗擊金融危機」的文章(The Economic Times,2008 年9 月24 日),呼籲廣泛的團結和合作,共同應對不明朗的經濟前景。
乍看之下,如果自己沒有被要求的話,那麼這種精神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世界的金融家們知道他們的機構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以致於一個機構失敗其他機構也會跟著倒塌,他們是脣亡齒寒的關係;同時政客們被警告,如果他們不站出來拯救自己國家的銀行,那麼自己本國的經濟將會崩潰並帶來多米諾骨牌效應式的連鎖反應,進而拖累整個世界經濟。
然而,在危機面前,人們總是很自然地做著相反的事情:封閉自己,保護那些屬於自己的東西。當然,這和團結那些「外國人」—特別是那些可能被視為引發危機的元凶的外國人,或者至少,對於今天的困境負有責任的外國人—聯合相比,這似乎是一個更安全的方法。
因此,美國,這個被普遍認為是造成金融危機和使其迅速升級的國家,並沒有因為孤立而承受痛苦。因為全球經濟的這種相互聯繫性,迫使諸如中國等經濟體不得不購買美元國債,並進而支撐了美國的經濟。
然而,對於政治家而言,把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似乎顯得再自然不過了,這就如同19 世紀英國頒佈的《穀物關稅法》和胡佛總統(Hoover)1933 年頒佈的《購買美國產品法案》一樣。雖然,合作和自我利益兩者之間微妙的平衡一直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然而今天,當我們在調查金融危機造成的破壞時,似乎大多數人還是擁護團結而譴責自我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那麼,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如果我們只是從純粹的經濟或心理學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就無法得出一個定性的結論。然而,當我們從卡巴拉科學的角度來探究它時,我們將會看到,在國際關係中所涉及的力量(事實上,在任何關係裡),是一體化的力量,而不是孤立的力量。它們的強大遠遠超過任何理性或非理性的決策過程,而它們在「幕後」決定著我們的行動。
在國際層面上,這些力量決定著全球的貿易、政治、條約、衝突和生態。在國家層面上,它們決定著教育、福利政策、媒體和當地經濟的發展趨勢。在個人層面上,它們決定著我們與家人的關係,而在存在的最深層面,它們則決定著我們以及自然界中的每種其他元素的進化發展。
當我們瞭解了這些力量時,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拿破崙會貪多地去試圖征服俄羅斯;為什麼希特勒也是同樣如此地貪心(而且是想征服同一個國家);為什麼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在他應停下來之時卻不能停止直到被別人停止時。這種「貪得無厭」綜合症是一種人類的典型的陷阱,是一種哪怕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和將要成為未來領導的領導人也無法抗拒的陷阱。事實上,導致我們如此表現的力量,是我們自身和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果對它缺乏瞭解和正確的認知的話,我們將招致無法承受的危險。
為了瞭解這些創造了現實的那些元素和力量,並且在其過程中影響它,我們必須先來瞭解它們的起源和最終歸宿。否則,就會像描述一個汽車內部的工作方式,例如它的發動機,和齒輪的連接,齒輪給軸承傳遞力量的方式等,而不去解釋汽車是一個將人們從A地安全、舒適並快捷的運輸到B 地的機器一樣。如果不解釋它的目的,那麼討論汽車的構造又有什麼益處呢?
卡巴拉和其他科學一樣,研究現實的內部運作。科學透過觀察現象而總結得出解釋其最後目標的理論,但對於卡巴拉科學而言,卻是首先看到目標,然後以目標做為出發點解釋結構。正如卡巴拉解釋的,那個目標就是為了使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發現創造和支配著全部生命的那個單一的、根本的力量。換句話說,卡巴拉的目標就是讓每個人都認識到自己生命的創造力量並獲取它,然後收穫這
一發現所可能帶來的全部好處。
20 世紀被稱為巴拉蘇拉姆(Baal HaSulam)(階梯的主人)的偉大的卡巴拉學家耶胡達•阿斯拉格(Yehuda Ashlag),在他的《光輝之書》(The Book of Zohar)的注解性著作《蘇拉姆》(Sulam)(階梯)中,用如下的方式說明了卡巴拉和生命的目的:
「這種智慧不多不少是一種根源的秩序,這些根源透過一種固有的、預先確定好的規則根據因果關係傳遞下來,交織成一個被稱為『在這世界向它的創造物揭示其神聖』的單一的、崇高的目標。」
我們的生命是用來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因此,卡巴拉學家將我們這個世界中物質的、歷史的和社會的現象視為實現這一最終目標的不同階段;正是從這個角度,本書將討論人類的歷史和當前的狀況以及未來的狀態。
第三章 人類共同的起源
平行的名字—我們的這個世界
在《卡巴拉智慧的本質》一文中,巴拉蘇拉姆解釋說世界ABYA相互之間都非常相似。
卡巴拉學家們發現這分別叫做Atzilut,Beria,Yetzria,和Assiya 的四個世界的形式,從第一個叫做Atzilut 的最高的世界開始,直到這個叫做Assiya 的物質的可見的世界為止,實際上就是完全相同的。這意味著在第一個世界發生的所有事情也都會被完整不變地發現在下一個更低的世界裡,就這樣在所有接下來的世界中都是這樣,知道這個可見的物質世界。
它們之間除了在程度上,在每一個世界的現實的元素的實質上感知到的不同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區別。越高的世界,與所有那些更低的世界相比,都更純潔(更多的給予)。在第二個世界裡的現實的元素的實質比起第一個世界的現實的元素的實質更粗糙(更多的接受),但比下一個程度的世界要純潔一些。
這種相似性一直延續到我們面前的這個物質世界,這個世界裡的現實的元素的實質比起前面的幾個世界的都要粗糙和黑暗(即具有最多的接受的特性,一直到利己主義的狀態)。然而,現實的形狀和元素以及它們的發生和發展卻是沒有任何變化,而且在每一個世界中都是相同的,包括在數量和品質兩方面。
因此,雖然卡巴拉談論的是願望,而非具體的物質對象,因為對象所有世界都是在同樣的規則下構建起來的,實際上都是相等的,所以卡巴拉學家通常用來自這個物質世界中的物體或過程的名字來解釋那些在願望層次出現的精神狀態或過程,這個物質世界的例子可以更加清楚和容易理解。我們之前討論過的Partzuf(臉)便是這樣一個例子。一個「更時髦」的例子便是Zivug de Hakaa(透過撞擊而耦合),它其實是描述一個排斥光(撞擊)、然後只接受(耦合)那些以給予為目的一定量的光的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
相應地,在他的《光輝之書的序言》中,阿斯拉格解釋說,之所以用「靜止」一詞來命名阿茲魯特(Atzilut)世界,是因為它包含了階段1 中的那種完全被動的接受的願望:之所以這樣接受是因為它就是這樣被創造的,而不是用它自身的接受的願望來抵制這個接受。
在物質世界裡,和阿茲魯特世界相對應的物質是無機礦物。所有的無機物都努力(希望)保持它們的形狀,它們沒有讓自身發生變化的任何願望;但如果你嘗試改變它們,你便需要使用一些能量和手段:因為它們會抗拒這些改變。用阿斯拉格的話來說,「第一層次的接受的願望被稱為『靜止的,無生命的』……是接受的願望在這個物質世界裡的最初的顯化,但在它的特定的物質中還沒有任
何運動。而且因為只有一個很小的接受的願望存在……它作用於單個物體上(無機物)的力量是分辨不出來的」。
貝里亞被稱為「植物的」是因為它是一種獨立的願望的開端。顯然,這種願望的物質顯化形式是植物。植物生長,開花,凋謝,興衰,與形成無機物的分子的那種聚集體不一樣,每株植物都是一個獨特的可分辨的個體。然而,植物在它們的運動上仍沒有自由選擇,仍然無法自由移動。當同一種類的植物種植在一起時,它們的行為都表現的完全一致。例如,向日葵的花盤總是朝向太陽(圖10),而豐收時節的小麥竿都會同時變黃。
耶茲拉被稱為「動物的」,和接受的願望進化發展的階段3 相對應。和原來的階段3 一樣,在耶茲拉裡,創造物享受著充足的「自由和個體獨立性……每個生命都有各自的生活」。阿斯拉格在之前提到的那篇介紹中寫道。但是,在耶茲拉裡,他解釋說:「這種願望仍然缺乏對其他人/物的感知,這也就意味著它們還沒有參與到任何其他人/物的『痛苦或歡樂』中。」
阿希亞被稱為「語言的」或「人類的」,因為它反映了一種最為完整和最複雜形式的接受的願望。在人類的層面上,「這個接受的願望包括著對其他人或物的感覺」(《光輝之書的序言》,第38條),而這正是人類層面和動物層面間最根本的區別。
阿斯拉格接著說到「在動物層面中的接受的願望缺乏對其他人/物的感覺,僅僅只能產生與其自身內部天生註定的程度相對應的需要和願望。但是人類,卻可以透過感覺到他人,變得同樣渴望獲得他人所擁有的所有東西,因此,變得充滿了羨慕和嫉妒,渴望獲得他人所擁有的一切」。因為這個原因,「當一個人擁有一百時,他想要得到二百,擁有二百時,他想要四百,他的需求就是這樣不斷加倍地膨脹著,直到他想要吞噬並擁有全世界的所有事物」。
要想真正理解人類的層次的這種願望和其他所有層次的那些願望之間的區別,有一個例子可供試驗:將一部新款智慧型手機和最美味的狗糧擺在一隻狗的面前,觀察牠會選擇哪一個。然後,如果您願意為了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而賠上一個智慧型手機的話,請將狗糧換為人類的食品,並同時保留智慧型手機做為選擇,對人類再做一次同樣的實驗。
第五章 人類
人類:唯一的例外
在上一節中,我們看到了為了賴以生存的系統的利益而犧牲自身的利益以尋求系統的照料的規則,它不僅適用於所有的生物,而且也適應於生物在棲息環境中(生態系統)的功能的發揮。然而,這個規則有一個例外的情況:人類。
要理解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我們就需要對四個階段進行深入的思考。階段1 到階段3 反映的是從一個給予者那裡獲得快樂的接受的願望—無論是透過直接接受來自它的快樂,還是透過返回給給予者獲得的快樂。但階段4 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它反映了一種成為給予者的願望。換句話說,階段4 要達到一個從定義上來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正如一個兒子不能成為他的父親,階段4 也不能成
為階段0。但是,正如一個兒子能像他的父親一樣,階段4 也可以變得和階段0 相似。
做為一個接受的願望,並且知道變得和階段0 一樣,也就是和根源一樣,是可能獲得的最高回報,這就是階段4 所渴望的。因此,做為它的物質化身的我們,一直在努力希望實現這個相同的目標。
在潛意識中,我們對名利、權力、財富、學識和不朽的渴望,實際上是想真正變得和上帝一樣的願望。沒有人能逃脫這些願望,因為我們都是階段4 的一部分—我們都隨同亞當在其靈魂破碎時一起破碎了。這些願望在人類中的區別僅僅在於這些願望的強度和比例,而不在於它們的構成。
顯然,有些人對於名利、財富和學識的願望都非常小,他們就是那些滿足於自己的居所、家庭和最基本的物質需求的普通大眾。
在這樣的人群中,屬於階段4 的願望並不佔主導地位,因此這樣的人很少有雄心勃勃的目標。
但是,即使在那些最安靜的人心中也都會有一個「魔鬼」,希望自己的錢能多一些,或者至少多過自己的鄰居。這些就是階段4的願望,也就是特溫吉和坎貝爾所描寫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感(sense of entitlement),而且它們幾乎是人類所獨有的一種願望。
這些願望同樣也是那些使我們成為直到智人的出現之前,一直統治著進化演化規則的例外情形的願望。因為人類具有一種天生變得像創造者一樣的渴望,所以,我們往往會用更積極的方法去迎接挑戰,而不是像其他動物一樣,只是被動地適應環境。
因此,我們不是竭盡全力使我們的身體能夠像其他的動物一樣適應環境的變化或威脅,我們是在試著改變環境或者消除那些可能的威脅。
這種努力之一就是改變我們的「私人小氣候」,也就是改變我們最直接的環境,來應對我們周圍的環境,比如,透過披上比我們自己更好的「皮膚」──動物的皮毛,來更好地保護我們自己以避免環境對我們的侵害。而且,並非依賴於我們的(顯然是不夠的)身體來為我們自己提供足夠的食物,我們不斷開發出越來越精密複雜的工具幫助我們狩獵,也幫助保護我們自己免受肉食性動物的捕
食……等等。
今天,當然也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靈長類動物、一些哺乳動物、鳥類,甚至會使用諸如岩石、樹枝和工具來幫助自己覓食和爭鬥。但系統的工具和武器的生產,例如把石頭和骨頭雕刻成長矛,卻是人類獨有的(圖16)。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是:早期人類(直立人)的成果是火的使用。火使人類的棲息地保持溫暖,防範獵食動物,甚至可以做飯。發現和使用火的各種方法,象徵著進化過程中發生的巨大轉變。人現在變成了一種可以改變自己環境的動物,而不是為了適應環境去改變自己。
美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發佈的一份題為「偉大的冰河時期」的文件中寫道,「冰河時代出現在一百多萬年以前」。廣大冰原的出現使人類可從非洲遷移出去,並逐漸蔓延到全世界。有了火和衣服,他們就可以使自己適應那些氣候不宜居住的地方,從而成為世界上適應性最強和無處不在的哺乳動物。
第一章 人類對於一的追求
2008 年8 月,當自1929 年大蕭條發生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爆發時,許多知名政要和金融家強調團結與合作的必要性。他們呼籲限制主導華爾街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框架的必要性,並且表達了對分裂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擔憂。如標題是「世界領導人尋求團結抗擊金融危機」的文章(The Economic Times,2008 年9 月24 日),呼籲廣泛的團結和合作,共同應對不明朗的經濟前景。
乍看之下,如果自己沒有被要求的話,那麼這種精神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世界的金融家們知道他們的機構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以致於一...
作者序
緒論
在這些文字被寫就時,世界才剛剛開始擺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的經濟衰退。世界各地的千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健康保險、他們的家園,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
我們的健康似乎並不比我們的財富對我們更有利。現代醫學,西方文明的驕傲,正在掙扎著應付以前認為已經滅絕的疾病。聯合國全球健康理事會(the Global Health Council)發表的一份報告稱,「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的疾病,已重新做為主要的全球性威脅而出現。抗藥性的細菌、病毒和其他寄生蟲菌株的出現,讓人類在控制傳染病方面面臨著新的挑戰。疾病的多重感染為預防和治療感染製造了重重阻礙」。
地球,也不像以前那樣友善了。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蓋亞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aia)、歐文•拉茲洛(Ervin Laszlo)的《混沌點》(The Chaos Point)和艾爾•高爾(Al Gore)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只是眾多有關地球氣候不斷惡化的警告式報導中的三個代表而已。
隨著全球變暖、兩極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已經造成了驚人的巨變和悲劇性的災難。斯蒂芬•法里斯(Stephan Faris)發表在《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份報告列出了已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一些地方。在蘇丹達佛(Darfur),由於長達10 年的乾旱,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之間爆發了衝突,而後發展成為反對蘇丹政府忽視他們的叛亂。
隨後,這場危機蔓延到查德中非共和國。此外,在該報告中,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已經宣佈其土地不再適宜居住和要求協助疏散人口。在2009年3 月24 日的一則新聞中,彼得•波法姆(Peter Popham),《獨立》(The Independent)雜誌的撰稿人之一,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了氣候的困境:「全球變暖使高山冰川融化迅速,以致於義大利和瑞士政府已經決定重新劃訂它們的國家邊界線,以應對這一新的現實。」
氣候變化導致的一個更加悲慘的結果是饑餓,是由於一些地區長乾旱而其他地區洪水不斷氾濫造成的。據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的數據,全世界中有十多億人飽受經常性的饑餓,而且這個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更糟糕的是,每年因饑餓和相關原因而死亡的人數超過九百萬,其中超過一半是兒童。這意味著,在今天這個人類歷史上技術最先進的時代,每6 秒鐘就有一個孩子僅僅因為缺乏食物和飲用水而死亡。
而我們的家庭,同樣存在著諸多問題。根據2006 年10 月由美國社區普查公佈的調查結果,離婚率的上升速度令人咋舌:和已婚夫婦相比,今天的美國有更多的未婚情侶。在人類歷史上,單親家庭第一次成為了常態,而雙親家庭則變成了例外。
許多科學家、政治家、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有關機構警告說,人類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災難的風險。無論是核戰爭、變異禽流感還是任何的一場大地震,都可能吞噬上百萬的人口,並把數十億人推進貧窮。
然而,危機始終貫穿於人類的整個歷史。我們人類並非第一次處於危機之中。14 世紀的黑死病大流行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都遠遠超過我們目前的困境。不過和以往危機不同的是,當前的危機以目前的人性的狀態為特徵。我們的社會已經向兩個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極端方向發展—一方面是要求相互依賴的全球化,而另一方面人們卻又變得越來越自戀。而對於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災難而言,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其他更多的領域,都有解決的方案。
今天,全球化關心的問題遠遠不單單是經濟相互依存的問題。我們生活中的每個領域都在全球範圍內連接在一起:我們用來自娛自樂的電腦和電視機來自(主要但不完全)中國大陸、臺灣和韓國。我們開的車來自(同樣,僅為主要的)日本、歐洲國家和美國,我們穿的衣服來自印度和中國,我們冰箱中的食品則來自世界各地。
更有甚者,世界上觀看好萊塢電影和學習英語的人數以百萬計。事實上,在全球約14 億使用英語的人中,只有4.5 億人以英語為母語。《亞洲時報》(Asia Times )作家因陀羅耆特•巴蘇(Indrajit Basu)在2006 年9 月15 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以英語做為母語」正在失去它的影響》。
2009 年3 月8 日,美聯銀行集團(Wachovia Corp)的經濟學家馬克•維特納(Mark Vitner)介紹了世界全球化的形勢。他在微軟全國有線廣播電視新聞(MSNBC)上淺顯地描述了信貸市場的相互聯繫:「這就像試圖把打散的雞蛋還原,不會那麼容易。我甚至不知道這是否可以做到。」
但是,全球化的相關問題不僅在於它使我們相互聯繫;雖然它使得我們相互依賴,但並非這些相互聯繫使得人類繁榮,而是它導致了持續的拉鋸戰爭。如果世界突然轉向使用風能和太陽能,那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會發生什麼呢?如果中國停止購買美元,那美國會發生什麼呢?日本、印度、美國和韓國,如果沒有用以購買商品的美元,那中國會發生什麼呢?如果西方遊客停止旅遊,那靠西方人的享樂主義而養家糊口的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又將如何呢? CNN 記者法利德•紮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2009 年8 月1 日《新聞週刊》的一篇題為《走出去的錢包:世界需要美國人花錢》的文章裡,有力地說明了這種尷尬:「如果經濟之神告訴我,能得到一個有關全球經濟命運的問題的答案……我會問,『美國消費者什麼時候能又重新開始消費?』事實上,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我們的生存完全互相依存。」
然而,相互依存只是今天複雜現狀的一部分。就在我們已經越來越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變得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做為心理學家,吉恩•M•特溫吉(Jean M. Twenge)和凱斯•坎貝爾(Keith Campbell)形容它為「越來越自戀」。在他們頗有見地的書《自戀流行病:生活在權利的時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Living in the Age of Entitlement)中,特溫吉和坎貝爾稱之為「在我們的文化裡,自戀無情地上漲」,並闡述了它引起的問題。
他們解釋說,「美國正在飽受自戀疫情的痛苦。……自戀人格特質和肥胖上升得一樣快……」更糟糕的是,它們還在繼續,「自戀率的上升正在加快,和幾十年前相比,21 世紀之初更是如此。到2006 年,四分之一的大學生符合自戀特質的大多數衡量標準。今天,正如歌手利特爾•傑姬(Little Jackie)所說的那樣,許多人認為「就是這樣,全世界都應該圍繞著我運行」。在韋伯斯特(Webster)的辭典中,自戀被定義為「自我主義」,坦白地說,這意味著我們已經成為可怕的自私鬼。
因此,我們的問題是雙重的:一方面,我們相互依存;而另一方面,我們正變得越來越自戀和彼此疏遠。我們正在努力創造的生活方式是在兩個根本無法相交的方向上發展:相互依存和相互疏遠。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在網路社交網站花無數個小時和「虛擬朋友」聊天,但對自己家裡的親人卻冷若冰霜的原因。
如果我們只是相互依存,那我們可以團結起來,相互支援,以愉悅身心;如果我們只是自私,那我們會分裂開來,過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我們同時相互依存而又自私自利,那麼,無論哪種方法都解決不了問題。
而這在本質上正是危機的根源:我們的相互依存關係需要我們一起努力,但是我們的自我中心卻使我們疏遠、欺騙和利用對方。結果,我們如此努力建立的合作系統被瓦解,然後危機爆發了。
因此,這本書的目的是雙重的:(1)一方面,即闡明我們相互依存的起因,另一方面,也闡明我們的自我中心的根源是什麼;(2)提出了一個為了我們的自身利益而將這兩個看似相互衝突的特性結合在一起的可行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第一個目標,我將從我所學到的卡巴拉的智慧對自然的結構、創造和宇宙的演變歷史,特別是對人的本性做出解釋。
而為了實現第二個目標,我會將20 世紀偉大的卡巴拉學家耶胡達•阿斯拉格(Yehuda Ashlag)以及其他偉大的卡巴拉學家的觀點,和當代的科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學者的建議結合起來。
在卡巴拉的智慧中,我發現了一個我認為是解決目前的全球性問題的可行方法,同時我也為我有機會來展示這一方法而心存感激。它是我的希望,請允許我這樣說,透過卡巴拉的概念,我們可以拯救我們自己,也能拯救這個藍色的星球。
序
我想,所有孩子都會經歷一個喜歡問「深奧」問題的時期。我曾問過「我們從哪裡來的?」、「人死了會去哪裡?」等問題。其中,我還問過,「生命的目的是什麼?」或許是因為父母都是博士的原因,我總覺得自己天生喜歡探究科學上的答案。可能因為我一直喜歡探究科學的奧秘,自己找到的答案總是更加廣泛,更加自然。
我選擇的科學領域是控制論,確切地說,是醫學生物控制論,這曾是我的研究項目和研究工具。在那個時候,控制論是一門革新的新生科學,使得研究者可以探索複雜的系統,並找出控制它們的機理。我曾對於人體和它的控制系統感到特別的興趣。透過控制論,我曾致力於解讀人類自身存在的秘密:身體和寄居其中的靈魂(我認為是這樣的)。
但是我的願望受挫了。確實,科學教會了我很多有關生命的東西,更確切地說,告訴了我新生命的開始和它維持的方式。但是,它並沒有帶給我、驅動我的科學研究更重要和更根本的問題的答案:生命是什麼?生命又是為了什麼?
解讀生命的渴望使我孜孜不倦地去研究任何自己可以得到的資料和線索。我在科學、哲學,甚至是宗教方面繼續著自己的研究,直到自己得到大量多餘的新知識和對生命的理解為止。但是,就和我起初有關控制論的經歷一樣,所有的這些似乎都不足以解答我對於生命的意義和目的這個最深層的疑惑。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得到了自己長久以來探索的答案。我偶然碰到了它,後來發現這是一門叫做「卡巴拉」的科學。回顧以往,我發現自己所有的探究都並非多餘和可惜。在我探究「卡巴拉」的道路上,科學、哲學和宗教都是必要的「中途站」,儘管我從未真正停在其中的任何一個點上。在自己對於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存在的目的的理解上,它們都做出了自己那一部分的貢獻,而且它們每一個都恰到好處地構成了由卡巴拉幫助我建立起來的完整的世界觀的一個部分。
另外,我發現了人類存在的意義和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各種全球危機之間的聯繫。透過卡巴拉,我認知到了這些危機是無可避免的,也讓我認知到了它們在和平與繁榮中必然得以解決,認知到了在如何解決這些危機方面我們的自由選擇是什麼—透過協同合作;而更主要地則是透過對我們的團結一體和互相依賴性的意識的覺醒。而且更重要地是,我發現古老的卡巴拉有關人類關係的理念為建立一個促進這種友善關係的可行性社會提供了一個平臺。
現有的全球危機是事先註定的這一觀點並不是我自己獨有的。而且危機是一個通往一個所有人最狂野的夢想都不可能夢想到的現實的跳板,這個觀點也同樣不是我的發明。這兩個概念都存在了幾千年,只是最近才得以浮現出來,因為這是第一次一個必須的雙重條件得到滿足:人們已經足夠地絕望到了急切渴望得到一個答案的地步,並且能對之進行足夠清楚的解答的方式已經具備。至於我自己在昭示這些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我是一位呈獻者和促進者。但是,我對這些觀點絕對沒有所有權。
正如我希望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將要展現的那樣,當代科學和現代思維現在有可能滿足那個雙重條件,從而揭開這個在卡巴拉科學中的古老的秘密。如果不是量子物理敢於挑戰牛頓的對現實的認知世界觀,我們就不會認為類似「現實的統一性」等概念是值得考慮的。而且,如果不是哲學虔誠地培養了自由的思想觀念,我們也將無法分享思想和互相學習。
因此,雖然我將要介紹的是卡巴拉式的概念,我將同時表明,其中許多理念與現代科學並行。我希望,在多元主義的精神裡,人們將會用一種開放的思想和心態來迎接它們。而且,如果我能喚起哪怕只是一個同齡人的沉思,就像他們在我之內一樣,我也覺得自己的這些努力完全得到回報了。
麥可•萊特曼
緒論
在這些文字被寫就時,世界才剛剛開始擺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的經濟衰退。世界各地的千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健康保險、他們的家園,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
我們的健康似乎並不比我們的財富對我們更有利。現代醫學,西方文明的驕傲,正在掙扎著應付以前認為已經滅絕的疾病。聯合國全球健康理事會(the Global Health Council)發表的一份報告稱,「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的疾病,已重新做為主要的全球性威脅而出現。抗藥性的細菌、病毒和其他寄生蟲菌株的出現,讓人類在控制傳染病方面面臨著...
目錄
第一章 人類對於一的追求
1. 那個隱藏著的無所不在的力量
2. 來自巴比倫的先驅
第二章 核心願望
3. 起源(創世記)
4. 四個階段和創造的起源
5. 階段0 和階段1
6. 階段2
7. 階段3
8. 階段4
9. 對創造的思想的探求
第三章 人類共同的起源
10. 願望是如何變為世界的
11. 平行的名字—我們的這個世界
12. 亞當的誕生與墮落
第四章 宇宙和地球上的生命
13. 大爆炸(The Big Bang)
14. 物質的四個進化發展階段
15. 靜止無生命層面
16. 植物層面
17. 動物層面
第五章 人類
18. 自我的開始
19. 人類:唯一的例外
20. 身體VS. 頭腦
第六章 走在相反的方向上
21. 金字塔內的金字塔
22. 分裂
23. 自由選擇
24. 在不斷進化的願望面前:團結3
25. 其他道路
第七章 偉大的融合
26. 猶太人的流放
27. 中世紀—隱藏的時代
28. 自由大憲章
第八章 文藝復興
29. 人類精神的偉大覺醒
30. 揭開神祕面紗,努力走向公開的開始
31. 卡巴拉的繼續發展
32. 連接與溝通
第九章 同一個世界
33. 無形的連接
34. 指數倍增效應
35. 全球性的網路
第十章 自由選擇的時代
36. 人性的強制性自由選擇
37.《光輝之書》的登場
38. 瞭解系統的需要
第十一章 一種全新的做法
39. 互相合作與自我實現
40. 二者擇一
41. 將自然的法則做為指引
42. 將變化應用到生活中
43. 培養相互責任
44. 培育合作性的環境
附錄
有關卡巴拉的基礎知識
其他卡巴拉著作
有關Bnei Baruch 國際卡巴拉教育和研究中心
如何聯繫我們
第一章 人類對於一的追求
1. 那個隱藏著的無所不在的力量
2. 來自巴比倫的先驅
第二章 核心願望
3. 起源(創世記)
4. 四個階段和創造的起源
5. 階段0 和階段1
6. 階段2
7. 階段3
8. 階段4
9. 對創造的思想的探求
第三章 人類共同的起源
10. 願望是如何變為世界的
11. 平行的名字—我們的這個世界
12. 亞當的誕生與墮落
第四章 宇宙和地球上的生命
13. 大爆炸(The Big Bang)
14. 物質的四個進化發展階段
15. 靜止無生命層面
16. 植物層面
17. 動物層面
第五章 人類
18. 自我的開始
19. 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