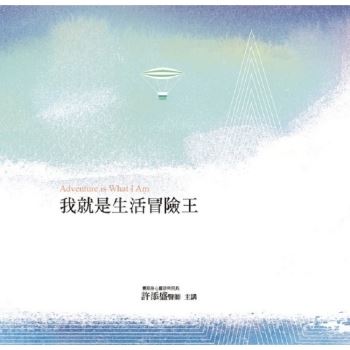11 春泥
春天的降臨趕走寒冷短暫的冬季,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田野間工作,藉由戶外勞動讓自己恢復幹勁,身體所有的感官似乎也跟隨氣候的改變而甦醒。我和冬季時默默待在角落而被遺忘已久的老朋友們再次相見︱鏟子、長耙、平鏟、修枝剪;我為自己將它們棄置在一旁找的藉口,是因為我相信就像植物一樣,他們也需要冬眠,養精蓄銳地等待嚴冬過去,因為在冬季之後,春天也將來臨。
我的手拂過這些老舊農具的把手,擦去上頭積聚的灰塵,然後整把抓起抖了抖,準備開工。我在修枝剪上滴了一滴潤滑油,仔細擦拭螺絲軸,接著用力握緊剪柄、然後鬆開,替彼此都暖暖身。鏟子和鋤頭的準備方式又不一樣,它們的金屬部分受到冬季氣候潮濕的影響,蒙上了一層棕褐色的繡斑;不過只要在土裡結結實實鏟個幾下,就會再度恢復光亮。
我對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的情感似乎太過豐富,那是因為我對農作的確充滿了熱情,所以只要和務農有關的東西︱所有的東西,我都興致勃勃。特別是在春天來臨時。父親大概不會用這樣的方式看待他的農具,但是他對即將展開的春季一樣充滿興奮的期待。他將修枝剪的刀身磨利,慢慢地用銼刀一遍一遍來回磨拭,然後停下來仔細檢查後,又重新磨一遍。如果父親慣用的鏟柄斷了,他會再找一根適合身高的新木柄裝上去(我和父親都不高,只有一百六十八公分)。
春天喚醒了整個山谷,花朵和小動物們為大地帶來生氣。臉頰上溫暖的陽光,讓人忘了其他地方還有雪,也忘了晚春寒霜對青嫩小苗的威脅。我們非常幸運,縱谷的春天比別的地方來得早。
農夫和園丁對春天的氣息異常敏感,我們都渴望走出戶外,呼吸清冽的空氣,撫觸甦醒的大地,感受指間微濕的春泥;我們的雙手在泥土裡翻攪,捏碎在冬天結塊的泥土,釋放這片土地被寒冬禁錮的靈魂。栽種似乎是一件自然的事,也是人類獨特的行為,源自於人們對開墾、成長與創造的渴求;農夫和園丁遵循自然循序的時間表耕作,學習跟上大地規律的步調,但是這些在現今講求經濟效益與利益的農業發展趨勢,早已被人們輕忽、遺忘。
我常認為學校應該規定所有的學生和老師們學習種植這門學問,好讓他們更能體會這中間所需要的耐心,還有生長的發展變化。每一個人都可以從種植中獲益,也能夠訓練等待花開之前的耐性。我有時候也會想像:也許哪一天所有的專業人士都需要具備園藝方面的知識,商人、律師、醫師以及政治人物必須通過園藝考試,當他們體驗過卑微的收穫後,必能培養出謙遜的處世態度。
隨著春天的召喚,所有的感覺也跟著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鄰居一位退休的日裔老農,靠著雙手和手指拂過針葉的觸覺,修剪他的松樹盆景;他能夠矇著眼睛,完全靠觸覺修剪多餘的莖葉。我問他如何知道該剪什麼地方,老農沒有回答,只是繼續他的修剪工作。我在一旁靜靜等著,更仔細的觀察。老農的雙手撫摸著針葉,不斷地拂過整株松樹,然後突然停下來開始修修剪剪,接著又繼續找下一個地方。他停下來的時間很短暫,好像有一股第六感引導他找到需要修剪的地方。老農修剪枝葉的手法就像一位技巧純熟的剪髮師傅,他們的力道輕柔,但動作迅速,而且能夠找出需要修整的地方,達到最令人滿意的結果;他們的工作目標都是創造自然流露的外觀,宛如工藝大師追求完美的極致。
隔鄰老農以身教代替言教,就像父親幾年來和我一起工作時一樣。春耕這門功課茲事體大,因為事關接下來這一整年的收成。我學會了用眼睛看、用耳朵聽、還有專注──這些都是春天教我們的事。
儘管如此,我還是在老農全神貫注地修剪盆景時,又問了一次:「你怎麼知道哪裡要修剪?」
這一次他同樣沒有開口回答,但卻抬起頭眨了眨眼,然後又全心回到他的松樹上。有那麼一刻我以為他正引導我進入「禪」的境界,要我專注於眼前的事物。
幾秒鐘後,老鄰居看著我,他問:「你說了什麼嗎?我的耳力沒以前好囉!」
他笑了笑,我沒說什麼,也對他報以微笑。
父親在春天這個再恰當不過的時間點回到了農場,所有的生命因他的出現與撫摸而甦醒。父親已經復原到可以勝任輕鬆的農作︱鋤草、監看灌溉水位、幫忙駕駛曳引機等等。
站在陽光下的父親享受著溫暖的春陽,微笑著慶幸自己能回到這裡。剷草,是父親這天的工作。雜草們也像父親一樣恣意吸收陽光的熱力,尋求生命的活力;它們和父親都在陽光下找到舒適與自在。雜草和父親就像兩個相互依靠的個體,雜草給了父親能夠繼續工作的機會;而兩者皆努力尋求屬於自己的歸屬,兩者也都是倖存的生還者,沒有哪一個願意從生命的旅程中離席。他們似乎彼此需要,也在每一年春天尋找對方。
經歷了天天穿厚夾克和兩雙襪子的寒冬之後,我也開始脫下身上一件件的衣服,讓皮膚感受季節的變化,找回身體和大自然的親密接觸。我想要盡情觸摸大地,更期待被暖陽擁抱。晚冬和早春的氣候有時令人捉摸不定,我盡量避免讓自己太冷或太熱︱我的身體則認為介於攝氏二○至二十二度之間的溫度最適合。如同許多住在現代城市的人們,我失去感受這個世界交迭變化的能力;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和這片土地的關係則讓我重新找回原本的感受力,或許比其他也在戶外工作的人更早記憶起這個季節的美好。
即使如此,我卻也經常忽略能讓所有感官感覺的機會,遺忘了感受的意義,彷彿被控制般對周遭漠不關心。舉例來說:在現今速食盛行的飲食文化中,餐具已然從餐桌上消失,我們經常用手抓食物吃,但是大部分的人不會記得手指碰觸芝麻餐包或是薯條的感覺。假如我們對食物絲毫沒有任何的感受,我們還會關心那些辛苦耕種、為我們帶來這些食物的人嗎?透過感覺,我們關心、留意;當我們關心、留意時,就會在腦海裡留下記憶。我們的腦細胞儲存了生命中的經驗與生活,但是人們卻常常對這些感受不知不覺,只因為我們未曾好好去感覺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依循每年與春天第一次接觸的慣例,我試圖喚醒身體所有的感覺。我的眼睛讓我看見氣候的變化︱陽光普照、霧變少了、白天變長了;當我的手觸摸溫潤的泥土時,我也感覺到了春天來臨的腳步。湊近一點,我聞到土壤裡的滋養,幾乎就像巧克力濃郁的味道。這片土地蘊藏了甜美的來源。
我停下腳步、仔細聆聽。一開始只聽見自己的呼吸聲,接著完全沉浸在期待的思緒裡,我彷彿看見了滿園花繁葉茂、結實累累的景象,蔬菜、水果、葡萄︱大豐收!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只不過我和父親一樣,也看見田野間冒出綠芽的野草,它們提醒我必須先付出努力及汗水,才能有豐收的甜美。我決定繼續享受眼前的嫩綠和這一刻,因為它們現在還不能算是雜草,只是生長在錯誤地方的植物。象徵春天的綠色環繞在我的四周,宣告冬天已經結束。
「輪到我大展身手的季節來囉!」我摩拳擦掌,等不及想快點揭開春天的序幕。
12 完美的破銅爛鐵
就像每一位優秀的農人,我們也有一堆破銅爛鐵,這些都是農場主人們代代相傳累積而來的,裡頭林林總總、雜七雜八,有各種奇奇怪怪的零件、老舊機具,以及被拋棄的過去。這堆廢棄物一直都在那裡,就像農場的一部分,隨著歲月日積月累地越堆越高。沒有人事先計畫,這堆被淘汰的東西就這麼隨著農人和他們的農作歷史逐年增加。
有些人可能看不慣這堆亂七八糟的廢棄物,他們會說:「該清理乾淨吧!」、「看起來糟透了!」、「簡直一團亂!」但是父親從來不隨意丟掉任何一根螺絲釘或其他機具的零件,每一次需要修理東西的時候,他總是能從這堆破銅爛鐵裡面找出適合的零件。父親讓我看見被丟棄的東西也有它的價值。
回到農場之後,我對這堆廢棄零件的主要貢獻,就是將大部分的零件重新堆到一個移動式的棧板上,這樣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再自欺欺人地假裝自己已經將這堆破銅爛鐵整理乾淨。
如同現代考古學家利用科學儀器搜索歷史的蛛絲馬跡,這些破銅爛鐵是我用來蒐集新靈感和新啟發,以及用來修理舊東西時的工具。一位雕塑家朋友陪我一起在破銅爛鐵堆裡「尋寶」,裡頭各種不同形狀造型的玩意兒讓他覺得有趣極了!我們拖出一個像大叉子的亮橘色耙刀,應該是從某輛收割機殘存下來的,我們把它立起來、又側放在地上,繞著它仔細欣賞。後來那位雕塑家朋友決定把這根大叉子埋進土裡,搖身一變成了所謂的現代藝術。我把它留在原地,有空的時候走過去仔細瞧瞧這座藝術之作,直到好幾個月後需要整地時,才把它挖出來丟回原來的廢物堆裡,這下它成了「後現代藝術」!
破銅爛鐵堆裡隱藏著許多寶物。從損壞機具拆下來的舊零件,告訴我農場裡的許多故事。時間的軌跡被留在這些層層疊疊的殘骸中,它們不像化石或者紀念物品,只能供人瞻仰、憑弔,而是能留給以後的農人們挖寶、使用(至少我是跟瑪西這麼說的)。
我在一場於威斯康辛州舉辦的研討會上提到這件事時,一位身穿吊帶褲的老農走過來跟我聊天,他說:「在我們那裡不叫『破銅爛鐵堆』!」我以為他會用「殘骸」這類在加州地區比較少聽到的字眼。
「我們叫它⋯⋯」老農好似揭露祕密般靠近我的耳邊:「存貨。」
我們的農場每一年都需要做一些改變,因為我們每一年都會面臨像是機具損壞、氣候變遷等等的新考驗。老舊機具對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來說就是一項挑戰,我們買不起新的、更不能丟掉舊的,所以只能咬著牙靠毅力堅持下去。我們學習在陳舊的設備下生活,但不讓自己成為過時的人。
父親的曳引機雖然老舊,不過仍然保養得不錯,我們每年都會為這些機器做一次健康檢查,也會不定時做一些小維修,所以農場裡的機器通常要超過十年以上,才會出現損壞或是無法再繼續修理的狀況。
拒絕相信,是農人面對困難或挫折時的另類應變之道。當我們無法負擔修理機具的龐大費用時,只能選擇不去煩惱隱隱迫近的災難,想辦法讓自己把心思放在別的事情上,這樣能讓情勢看起來好像沒那麼糟。盲目的樂觀以及努力的工作,確實有其優勢,它們支撐著你,給你繼續下去的力量,讓你度過這一季︱或是中風的危機。
面對日益艱難的困境,我學會利用僅有的器具度過難關,藉由熟悉每一項機具的操作技巧,讓我們再度過另一個收穫季。例如農場有一輛曳引機的變速器有時候會卡住,讓我沒辦法換檔,有一次我還真的就這樣整天都倒著開︱而我也只能放慢速度,耐著性子趁機學習用另一個角度看世界;雖然一開始不免感到沮喪和憤怒,但是我依然必須接受現實,然後開始用新的方式查看我的果樹和葡萄藤。當隔壁農場的工人對我揮手微笑時,我也忍不住笑了。經過幾次的經驗之後,我發現可以用鐵撬把排檔撬開,再不行的話就用長一點的螺絲起子將變速器的齒輪轉鬆。所以針對這輛曳引機,我的解決方法就是隨時放一把螺絲起子在工具箱裡,以防萬一。
大型農場和資金雄厚的集團根本不使用老舊的機具,然而舊機具在我們的農場裡被視為珍寶,原因正是因為它的老舊。這些舊工具在我們眼裡已經變成了「古董」,是值得珍藏的物品。或許是因為生活步調越來越緩慢的緣故,許多老農人對他們的舊機具懷有一份特別的感情──以及憐惜之情。我們也經常在回收利用這些舊物時,重新發現它們的價值。
老舊機具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它們經歷了失敗比成功多的年代,在那些年代裡當事情不如預料中順利時,你的選擇就是試試其它方法。現代農業追求的是立即效果──噴灑控制害蟲的農藥,或是施用快速增長的肥料,然後指望隔天就有效。而我和這些舊機具比較像藝術家,令人難以理解地想要追求完美的表現。這也是為什麼我得持續不斷求進步的原因。
當父親漸漸恢復的同時,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剷草而已。他重新學習許多農作的技巧,也找到一些受傷的右手能夠應付得來的工作,他的修剪技術也慢慢回到中風之前的水準。他駕駛那些容易爬上駕駛座的曳引機,記下農場裡比較不必用到太多駕駛技術的小徑。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水蜜桃的滋味:第二代農場主人的生命之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8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水蜜桃的滋味:第二代農場主人的生命之歌
★★亞馬遜讀者評價五顆星好書★★
韓良露、買買氏、劉力學、倪葆真 真情推薦
一種美味、一段記憶、一個堅持,一份傳承、一點感動、一個發生在自家果園的生命故事……
深深敲動我們的心,看這本書的同時,這個故事也同時在台灣發生……
有時候我會夢見所有美國農民全部列隊,依照年齡排成一行,年紀最大的排在前面,最年輕的排在後面。然後排在隊伍裡的我回頭一看,發現排在我後面的竟然沒幾個。
有幾個人繼續入列,但是他們都往前頭去,我突然懷疑自己是不是站錯位置,後頭的人這麼的少……
作者簡介:
大衛‧增本是得獎著作《桃樹輓歌》以及多本書籍的作者、專欄作家、有機農作發言人、以及家樂氏基金會(W.K. Kellogg Foundation)成員。他是第三代農家子弟,目前和家人在加州佔地八十英畝的農田上種植有機認證的水蜜桃、李子和葡萄。大衛.增本是日裔美籍第三代果農、自由寫作者、農民運動者、加州人權協會會員
譯者簡介:
何佳芬
美國南加大教育心理碩士。翻譯與創作的童書曾多次獲得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譯作包括《0-8歲育兒智慧王》、《孩子,錢不是從樹上掉下來》、《客廳裡的大象》、《告別亨利──一個自閉男孩與狗的真愛奇蹟》等書。
章節試閱
11 春泥
春天的降臨趕走寒冷短暫的冬季,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田野間工作,藉由戶外勞動讓自己恢復幹勁,身體所有的感官似乎也跟隨氣候的改變而甦醒。我和冬季時默默待在角落而被遺忘已久的老朋友們再次相見︱鏟子、長耙、平鏟、修枝剪;我為自己將它們棄置在一旁找的藉口,是因為我相信就像植物一樣,他們也需要冬眠,養精蓄銳地等待嚴冬過去,因為在冬季之後,春天也將來臨。
我的手拂過這些老舊農具的把手,擦去上頭積聚的灰塵,然後整把抓起抖了抖,準備開工。我在修枝剪上滴了一滴潤滑油,仔細擦拭螺絲軸,接著用力握緊剪柄...
春天的降臨趕走寒冷短暫的冬季,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田野間工作,藉由戶外勞動讓自己恢復幹勁,身體所有的感官似乎也跟隨氣候的改變而甦醒。我和冬季時默默待在角落而被遺忘已久的老朋友們再次相見︱鏟子、長耙、平鏟、修枝剪;我為自己將它們棄置在一旁找的藉口,是因為我相信就像植物一樣,他們也需要冬眠,養精蓄銳地等待嚴冬過去,因為在冬季之後,春天也將來臨。
我的手拂過這些老舊農具的把手,擦去上頭積聚的灰塵,然後整把抓起抖了抖,準備開工。我在修枝剪上滴了一滴潤滑油,仔細擦拭螺絲軸,接著用力握緊剪柄...
»看全部
目錄
原書名:最後一位農場主人的生命智慧
推薦序 每個難忘的味道,都有它獨特的意義
謝辭
第1部 我的選擇
第2部 人生的意外
第3部 農場裡的大小事
第4部 深值的回憶
第5部 世代交替
推薦序 每個難忘的味道,都有它獨特的意義
謝辭
第1部 我的選擇
第2部 人生的意外
第3部 農場裡的大小事
第4部 深值的回憶
第5部 世代交替
商品資料
- 作者: 大衛‧增本 譯者: 何佳芬
- 出版社: 樂果文化 出版日期:2012-05-07 ISBN/ISSN:97898659831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9頁
- 類別: 中文書> 生活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