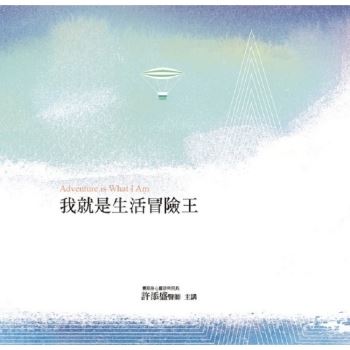繁體版搶先登場!
瀟湘冬兒 最新力作
原該安心待嫁的官宦千金,被迫入宮
原該前程似錦的秀女,卻被棄於亂葬崗
高牆深宮,諜影重重,難測的人性,詭譎的陰謀,她們卻無從退避……
什麼是報復?
不是殺了你,而是奪走你在意的一切,金錢、權利、地位與愛人,
然後──
讓你一無所有的跪在我的面前,豬狗不如的活著。
一場詭異難測的陰謀,一次乾淨俐落的殺戮,
一位慘遭橫死的宮妃,一座繁華巍峨的宮廷。
原本該安心待嫁的官宦千金虞錦,與原本內定為太子妃的秀女姜陵,
就此,開始了她們錯位的人生。
當禍從天降,美夢破碎,往昔美好盡皆化為泡影,
當慘遭橫禍,家破人亡,滿腔熱血盡皆凝成寒冰,
她們又該何去何從?
鳳凰泣血、宮闈博奕,萬千胭脂粉袖下,卻是掩不住的血雨腥風……
作者簡介
瀟湘冬兒
六年級後段班女生,生長於白山黑水之間。
瀟湘書院當家花旦,新生代網路寫手。
她用自己的靈魂書寫著一個又一個感人心肺的故事。
愛旅行的她將所見沉澱於心底,又將思緒飛馭其上;她將時間寫進文字,將現實融入夢想;她在人生旅途中跋涉感知,編撰獻於他人的寫意人生。
代表作品:《11處特工皇妃》、《暴君,我來自軍情9處》、《宮諜》、《軍火皇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