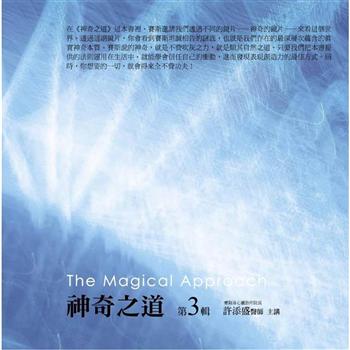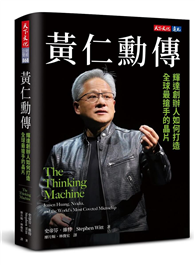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守墓人!守墓人!」
冰雪初融的早春,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素衣少女手提羅裙一路輕跑,長至膝蓋處的黑髮隨著她的跑動輕輕飄蕩。
「守墓人!」
少女站定,看著那靜坐夕陽下,正獨自吹塤的背影,心裡覺得莫名的悲傷。
塤聲悲壯低沉,沉浮纏綿於夕陽下,如泣如訴,那是一曲無人能懂的悲歌!
那人回首,早春殘紅的暮色透露著妖冶的光韻,將那深褐色的面具塗抹上一層令人望而卻步的猙獰!
面具的背後閃爍著兩道璀璨奪目的眸光,那是他身上唯一的亮點,曾筱冉想,她只要迎視著那雙星眸,便覺得他殘陋的容貌身體之下有著鮮活生動的生命和感情!
她叫他守墓人!
那是在兩年前她暈倒在太子陵內被范家人帶出墓陵後的某日,她在聽到吹塤之聲後再次看到了戴著面具的范家三公子范奇。
她小心地問他:「我以後要怎麼稱呼你?」
「守墓人!」
他起身後頭也不回丟下她一人獨自立於寒風呼嘯的皇陵一隅。
她曾為自己在初見他時表露出來直接傷人的驚恐感到萬分內疚,她一次次的靠近他,他一次次的迴避她……
皇陵深處,他們無聲無息地玩著躲貓貓的遊戲,但是,人性便是如此,對越是禁忌的東西便越是嚮往,對越是逃避的人便越是好奇。
兩年裡,曾筱冉無數次地纏著范奇教她吹塤,范奇均是無情冷漠地拒絕,在碰到他心情不好的時候,甚至會對她發火怒吼。
「妳離我遠一點!別想靠近我!別想試圖走近我!」
他的母親林氏在這個時候總會在她身後安慰,「顏兒,妳莫要怪他,他孤僻的性情不是與生俱來的,只是那一場大火燒毀的不僅僅是他的容貌,也燒毀了他的自信和驕傲!」
「嬸娘,我懂的,他和我皆是被命運捉弄和遺忘了的人,同樣的不幸!」
「好了,忘了過去,別盡想這些讓人傷心的事兒!」
林氏愛憐她,生有三個兒子卻沒有一個貼心的女兒一直是她的遺憾,兩年前救了曾筱冉,也算是她和范家的緣分。
再來也是為了保護她,對這憑空多出來的范家人總要有一個說法,於是范進於兩年前便給她改了名──范顏兒!
他日若有人問起,便說是范家的堂親留下的女兒,因為雙親雙亡,便來投奔堂叔。
兩年來平靜的生活讓她褪去了過往的青澀,其實兩年前在陵墓中的初見,便知她日後定能長成傾國傾城的美貌,只是不曾想,兩年說長不長的時光會造就她如此嫋娜卓絕的風姿!
猶如此刻,夕陽下的少女不過十四有餘,晚風輕拂,盈盈而笑,一身粗衣素裙,但是她與生俱來的馥蘭氣質無法被掩蓋、被埋藏。
范奇想,她終歸不會屬於這裡的,她只是一隻潛伏於此的彩鳳,只等時機成熟便要一飛沖天!
「守墓人,嬸娘讓我來叫你吃飯!」
范奇輕嗯了一聲,將手中的塤交給顏兒,道:「吹來聽聽,妳新學的那一首曲子!」
顏兒眉眼彎起,開心而笑,將塤湊在唇上。
她的習慣,每每吹塤之時便會閉上雙眸,一如此刻,晚來風急,吹得她衣裙獵獵,青絲嫋嫋,夕陽如畫,照得她眉目生輝。
輕柔的塤聲綿延起伏,范奇知她自幼精通音律,但凡鐘磬塤鼓,琴瑟簫管一點就通,為了跟自己學塤更是沒少受自己的氣。
一曲畢,她睜眼側首,倩語笑言,「吹得如何?」
「很好,吹得很好!這個塤就送給妳了!」
「真的?」
「當然是真的!」
范奇別過視線,不敢正視她如春花綻放時的笑靨,他一直告訴自己,她是自己不可觸碰的禁忌,是自己此生無法擁有的美麗神話,所以他的心不能為她淪陷……
「回去吃飯!」
「嗯!」
范奇佝僂的身子依靠拐杖支撐,顏兒跟隨在他的身側,與他緩緩前行。
抬頭望向天際的最後一抹餘暉,只見不遠外黃沙滾滾,群馬齊奔,直驅皇陵!
顏兒下意識地退後,將自己的身子隱在范奇之後,一手緊攥著他的衣袖道:「這些人定是來自京城的,會不會……」
「莫怕!」范奇低聲安撫,「像沒事人一樣走過去,不要忘了,妳如今是范顏兒!」
前方五六匹高頭大馬果真於皇陵入口處停下,顏兒和范奇站在不遠處細看那些人的裝扮,一身勁裝俱是出自宮廷禁軍。
他們拴好馬匹之後便快速湧入皇陵,身形如風,范進應該也是在他們進入皇陵之前就看到了這一行策馬狂奔而來的人!
「各位是……」
「范進,八皇子有令,皇上病危怕是大限已至,命爾等速速整頓皇陵,明日便有工匠來此對皇陵進行修繕,爾等務必全力配合!」
瑞帝要死了?
范進的心「咯答」一下,身上不由得冷汗直冒。
「小的明白,小的定會按八皇子的命令行事!」
領頭的侍衛冷冷掃過范進,雙手抱拳過後道:「話已傳到,我等就告辭了!」
「是,將軍慢走!」
那些人轉身,迎面碰上了正徐徐行來的顏兒和范奇,對這一如天仙一如鬼剎的二人忍不住產生了好奇,又回頭問道:「范進,這二人是?」
范進努力不讓自己的表情看上去僵硬,笑道:「是幼子范奇和姪女范顏兒!」
那領頭侍衛以鄙夷的目光看了一眼全身裹著黑布,戴著面具的范奇,爾後又將眼光緊緊盯著顏兒,臉上浮現頗具深意的笑,顏兒受驚,急忙低首斂眉。
「范侯爺……」那人不自覺地對范進轉換了稱呼,「你范家說不定能時來運轉了!」將話丟下之後一行人便匆匆離去。
當晚,顏兒心緒不寧,輾轉難眠,外頭一輪明月掛於疏桐之後,夜寒露重,想起白日裡那皇宮侍衛的話,不由得更添了幾分愁。
她披衣起身,燃上蠟燭,信手拿起炕上矮几上的書籍閱讀,卻不知為何始終無法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書的內容上。
如果瑞帝駕崩,那麼繼承大統的會是何人?
生死不明的太子假使真的還活著,是否要於此時現身了?
如果太子果真死了,那麼最有希望登上寶座的將是八皇子。
那麼自己的父親呢?他將會在這一場政治爭鬥中扮演什麼角色?
兩年前他一手扶持的太子亡故,想必對他造成的打擊不小,他如今是仕途受阻從此偃旗息鼓了呢?還是背水一戰不甘服命呢?
早年在相府裡,她便時常聽說瑞帝最為疼愛的並不是太子,而是已故的三皇子。三皇子死後他又將所有的寵愛給了八皇子!餘下雖還有不少皇子,但大都是泛泛之輩,恐難成大器,瑞帝當然不會將皇甫家數百年的江山輕率相傳的!
奈何,這皇陵和京城之間沒有任何資訊來往,這兩年她跟著范家人在此生活,想讓自己心如止水。可是每當夜深人靜之時,那些前塵往事便會洶湧而來,宛若挫骨噬心的痛,讓她一次又一次地清醒!
她撚了撚燭芯,聞得一聲「哇啊」之聲之後不禁輕笑出聲,想來是范初和妻子柳氏五個月大的孩子啼哭了。
支起窗,一陣寒風侵入,讓她忍不住打起哆嗦。
果見對面處,范初的房內傳出明滅的燭光,她又看了一眼他們隔壁的房間,那是范奇的房間,卻是一片漆黑。
「守墓人,我知道你將永遠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你不會靠近我,也不會讓我走近你!猶如此刻,黑夜隔著你和我,這咫尺的距離,竟似千山萬水一般無法跨越!」
那邊范初的房間熄了火,恢復了夜的寧靜,顏兒也放下窗,滅了燭火,窗外的月光折射而進映得一地潔白明亮。還是無法入眠,便雙手托腮,凝望著屋外的月光。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何時有了睡意,昏昏沉沉地趴在桌上,直到屋外的野貓在半夜時分拉長著嗓子,發出令人不勝其煩的叫聲才將她驚醒。
她揉著睡眼惺忪的眼睛起身,怕身子著了涼想回炕上歇息,卻又忍不住將臉貼在糊著紙的窗格看了一眼屋外靜悄悄的夜色。這一看之後卻讓她整個人清醒,為了更為清晰地看到外面的情景,她的食指沾上口水,將窗紙戳破!
用柴荊圍起的小院落閃過兩道矯健的身影,由外及內,直奔范奇的房間!
顏兒在雙手緊捂著嘴巴之前差點就驚呼出聲!
有人想要謀害守墓人!
當這個想法如一記電光閃過自己腦海的時候,讓她整個人都失去了理智,容不得她多想,拉開房門,不管自己衣衫單薄,外頭寒意四起,她直接衝向范奇的房間。
想到范家一門武功俱是不弱,自己卻是手無縛雞之力,便忍不住放聲而叫,「來人啊!有人──」
話音不曾落下,後腦杓一陣劇痛,卻已不省人事了。
倒下之前仍是不忘道:「守墓人,不要有事……」
顏兒醒來已是午時,林氏端著熱騰騰的白粥和煎餅笑意盈盈地推門而入,身後卻是跟著戴著面具的范奇!這讓顏兒立刻想起昨晚情景,急忙低頭查看自己是否有被人侵犯!
「沒事沒事,昨晚是有人想要入皇陵盜取財物,好在被妳發現了,妳那一叫家裡人便都醒了,那些人也沒得逞,把妳敲暈之後便直接逃跑了!」
林氏坐在顏兒的床側,顏兒也不顧自己的頭還隱隱作痛,急忙問范奇:「守墓人,你沒事吧?我看到他們進了你的房間了!」
「我沒事,妳不要擔心我!」
因為面具遮擋著他的臉,所以永遠看不清面具背後的臉有著怎樣的表情,唯有一雙星眸閃爍其後,再加之低沉沙啞的嗓音響起才讓顏兒覺得他是安然的,終於放下心來。
兩個人無聲地對望之後各自別過視線,林氏也已察覺其中微妙的氣氛,她笑著伸手撫摸顏兒的額頭道:「還好沒有發燒,起來把這粥給喝了,應該餓壞了吧!」
顏兒依言起床,范奇默默地出了門,林氏在房間裡半舊的斗櫃裡為顏兒尋找衣服,顏兒洗漱過後坐在一旁喝著粥。
林氏有一句沒一句地和她話著家常,「顏兒,這幾日宮裡怕是會有不少人來往於此,妳的模樣出挑,我和妳叔叔擔心妳早晚會被人認出,所以想讓奇兒帶妳去皇陵西北角的茅草小屋居住一段日子,那邊離皇上墓陵較遠,再加上偏僻,想來應該不會有人注意到妳的。」
顏兒覺得林氏說得在理便答應了,吃完飯之後,她簡單的收拾了幾件衣物和貼身物品便和范奇前往西北角的小茅屋。
皇陵西北角地勢偏高,能俯視整個皇陵,加之種有各種四季常青之樹,終年枝繁葉茂,倒不失為一個藏身的好去處。
她和范奇相安無事的在這裡居住了數日,每每吃飯之時林氏便會讓李氏或是柳氏將飯送來給他們,他們也時常居高臨下觀看皇陵近日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真如林氏所言,皇陵不時有京城派來的人進出,更甚者,有時會有馬車進出,自京城運來很多東西,顏兒甚為好奇。
「守墓人,是不是皇上駕崩了?」
她總是時不時地尋找話題想和范奇親近,范奇還是一貫的冷漠,拒她於千里之外。
「你說若不是皇上駕崩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奉命來這裡辦事?」
范奇還是不回應她,他只是坐在屋內最為幽暗的角落用小刀雕刻著木頭娃娃,神情專注,彷彿世事一切俱與他無關。
「守墓人,你說如果皇上駕崩,會是由誰登基呢?」
「……」
「守墓人,會是八皇子還是那明明已經死了,卻不見了屍體的太子?」
「妳懷疑太子沒死?」這一次范奇終於開口。
「我也不確定,也許他是真死了,當年皇上出於某種原因將他屍體葬於別處了!當然,也有可能,他是真的沒死,如果沒死,他這是為什麼裝死?又或者是他被人挾持了?可是,不管是哪一種原因,這背後一定是有著陰謀的,你說對不對?」
「我不知道!」范奇回了她一句,便逕自低頭雕刻。
正巧此時柳氏前來給他們送飯,柳氏等他們吃完飯便收拾碗箸,提著籃子出門回去了。
她行在坡間,迎面春風拂來,卻聽得身後顏兒在喚她,「二嫂,等等我!」
「顏兒有事?」
「嗯,顏兒想問問二嫂,皇陵這幾日如此繁忙……」將話說出之後,又謹慎地看了看四周,才繼續問道:「是不是皇上他……駕崩了?」
柳氏點頭道:「前日我們就接到京城裡的傳話,說皇上的確在早一天駕崩了,如今宮裡正忙著新皇登基之事呢!宮裡頭的事整頓妥當後,估計就等欽天監陰陽司擇日出殯了。」
「那如今新皇是誰?是八皇子嗎?」
「誰知道是誰當了新皇帝,皇上有那麼多兒子、兄弟,這江山反正都是他們皇甫家的!咱們這裡要不是一年裡頭死幾回皇家的人,倒也算是與世隔絕了!誰當皇帝都一樣,也沒有人會和咱們這些落水鳳凰說這事,咱們也學會不聞不問,如此日子方可長久!」
聽說武敬侯的兩房兒媳俱是出身名門,相處下來發覺柳、李妯娌二人處事也是極為穩妥之人,柳氏這一段話雖說處處顯示出她對皇家的敵意,卻也不無道理。
「顏兒,妳也得學會裝聾作啞,如此才可永保平安!」柳氏說完之後拍拍顏兒的臉,「我走了!」
顏兒嘆息,走在石子小路,道旁小野花隨風輕曳,她蹲下身子信手摘了一朵,顰眉自語,「我也知道自己應該遠離是非,我是一個已經死過一次的人,如今又不能恢復身份,如此這般糾結於過去又有什麼意思呢?知道了答案又能怎樣?」
那晚她被自己的親生父親灌下毒酒,她怒睜著雙眸死死地盯著父親,他雙手如鉗,不留一點情面,絕決果斷地將毒酒盡數倒進她的嘴裡,不給她一絲活命的機會。
她不願相信,但又不得不承認,父親是真的要自己死的!
她吸了一口氣緩解胸口的疼痛,不讓自己的眼淚掉下來,她已無數次告訴自己,既然老天已經給了自己第二次生命,她便要堅強地活下去,不會輕易的讓自己再次淪為生命的奴隸。
她要自己把握自己的未來!
思及此,不由得面露微笑,她看著幾步之遙的小小茅屋,不由得加快步子。
「守墓人,我會一直守在你的身邊的!」
天龍朝,瑞昭二十三年春,瑞帝駕崩葬於皇陵。
皇帝大殯舉國哀悼,滿朝文武皆著素縞,顏兒站在茅屋前方舉目眺望,只見整個皇陵一片白漫漫人來人往。
悲音哀樂不絕於耳,僧道行香誦經,皇親扶柩哭靈,一派紛擾喧鬧之景。
顏兒撇開范奇偷偷沿著陡坡行至帝陵附近,雖然她一直說服自己不再理會舊事,可是,她著實好奇難耐。她知道新皇的儀仗隊即將進入皇陵,她只需看一眼就好,還有……她內心深處終究還是想要看一眼自己的父親是否會出現在送殯隊伍之中。
一陣和音奏樂之後,聽得太監獨有的公雞腔調蓋過樂聲,「皇上駕到!」
顏兒躲在帝陵一角的一棵松柏之後,屏息斂氣,凝視著前方沿著甬道徐徐行來的轎輦。
鳳翣龍旌,雉羽宮扇,垂以藍色流蘇的金黃傘蓋,繡以藍鱗金龍騰雲駕霧的龍輦以帷幕虛掩。
顏兒睜大眼睛努力地想要看清轎輦裡所坐之人,只是隱約可見轎中人龍袍加身,皇冠束頂,卻不見其貌如何!
轎輦一直行至帝陵腳下,兩旁搭著高棚,四十九級白玉階上士兵林立,白旗翻飛。
顏兒終於看到新皇下輦,遠遠而觀,還是看不清其相貌如何,只待他轉身!
還是這般熟悉的景象!
她在茫茫人海中一眼便將他望進眼底!
俗世紅塵,凡音俗語頓覺消弭,她定定地望著高貴如神的少年皇帝。
他烏黑如緞的長髮及腰,頂著金光閃爍的金龍冠,一手負後,一手擱於胸前,步履從容,沿著白玉階梯而行!
太子,果然是你!
一直害怕看到轉過身來的那個人是你,可是,當你真的轉身而過的時候,我彷彿早就預料到了會是你!一定是你!
好一個皇甫靳!
好一場令人匪夷所思,無從思想的陰謀!
只是你贏了!
她已知,這一次他的目光不會再穿越層層人海與她對視!
她已知,那般的怦然心動此生唯有一次!
她在茫茫人海中不見父親的身影……父親,你可還是安好?
她倏然轉身離去,裙裾掃過翠綠無情的樹枝,雙手緊握成拳,眼淚已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了!她一聲聲地問自己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所有人都回歸正位,得到了自己應該得到了,唯有自己,雖然活著卻成前朝太子的冥妃?
不,她不能就這樣木然地過完這一生!
她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她不是別人手中的帶線木偶!
她也不能永遠藏身在這皇陵中,為皇甫家的先祖們守墓守陵!
「我要答案!我要一個當年為什麼非得要我死的答案!我要一個已故太子如何死而復生再登上皇位的答案!」
她回首,那邊梵音不斷,她的清眸淌下晶瑩的淚珠,那美絕人寰的小臉純真不再,一抹決然冷豔的笑猶如勾魂的媚蠱浮現在嘴角,「皇甫靳,你等著我!」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夙締良緣(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95 |
社會人文 |
$ 198 |
古代小說 |
$ 198 |
羅曼史 |
$ 198 |
古代羅曼史 |
$ 198 |
言情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225 |
文學作品 |
$ 594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夙締良緣(1)
古言+懸疑經典 兒女情長中最獨特的驚心動魄
一杯鴆酒,一具空棺,一場前所未有,轟動朝野的冥婚……
機智的相府千金,皇陵重生,陪葬謎案,疑點重重
且看她如何抽絲剝繭,揭開真相,成就一段夙締良緣
十二歲的曾筱冉,天龍朝相府裡最為尊貴的四小姐,
說其最為尊貴,緣由她未來的夫婿可是當朝的太子──皇甫靳!
一心一意等著及笄之年就舉行大婚,成為太子妃,甚至是母儀天下的皇后。
然而,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卻打碎了她一直懷抱的美夢,
太子靳猝死於景明宮!
更令她想不到的是,她最敬愛的父親,竟逼她喝下鴆酒,嫁於猝死的太子,成為冥妃!
在暗無天日的皇陵中,她意外重生,卻發現,
太子棺木中只有價值連城的古董玉器,獨獨沒有皇甫靳的屍身!
而且兩年後,明明猝死的太子卻繼承大統,登上帝位,成為新的國主!
為什麼?這是為什麼?
他高居太子之位,當年何苦大張旗鼓的舉辦冥婚,為自己掩蓋偽死真相?
太子猝死的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陰謀?
為何父親非要她喝下毒酒,與他合演一場陰婚鬧劇?
自己明明也是局中人,為何不知局中事?
她要知道答案,答案是什麼呢?
作者簡介:
十一顏
宅女一枚,擅長寫古典言情、穿越言情小說。
平生無大志,最愛江南煙雨,回首斑駁時光,編織舊時回憶,靜默對待生命,願與時間平行。
章節試閱
「守墓人!守墓人!」
冰雪初融的早春,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素衣少女手提羅裙一路輕跑,長至膝蓋處的黑髮隨著她的跑動輕輕飄蕩。
「守墓人!」
少女站定,看著那靜坐夕陽下,正獨自吹塤的背影,心裡覺得莫名的悲傷。
塤聲悲壯低沉,沉浮纏綿於夕陽下,如泣如訴,那是一曲無人能懂的悲歌!
那人回首,早春殘紅的暮色透露著妖冶的光韻,將那深褐色的面具塗抹上一層令人望而卻步的猙獰!
面具的背後閃爍著兩道璀璨奪目的眸光,那是他身上唯一的亮點,曾筱冉想,她只要迎視著那雙星眸,便覺得他殘陋的容貌身體之下有著鮮活生動的生...
冰雪初融的早春,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素衣少女手提羅裙一路輕跑,長至膝蓋處的黑髮隨著她的跑動輕輕飄蕩。
「守墓人!」
少女站定,看著那靜坐夕陽下,正獨自吹塤的背影,心裡覺得莫名的悲傷。
塤聲悲壯低沉,沉浮纏綿於夕陽下,如泣如訴,那是一曲無人能懂的悲歌!
那人回首,早春殘紅的暮色透露著妖冶的光韻,將那深褐色的面具塗抹上一層令人望而卻步的猙獰!
面具的背後閃爍著兩道璀璨奪目的眸光,那是他身上唯一的亮點,曾筱冉想,她只要迎視著那雙星眸,便覺得他殘陋的容貌身體之下有著鮮活生動的生...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古墓重生
第二章 迷霧層層
第三章 改名換姓
第四章 不如相忘
第五章 進宮揭密
第六章 你是誰?
第七章 四美爭鋒
第八章 妃上無后
第九章 謎團紛呈
第十章 步步為營
第十一章 他人夫君
第十二章 鋒芒畢露
第十三章 詐死背後
第十四章 一去難還
第十五章 只道珍重
第十六章 進行驗身
第十七章 竟是石女
第十八章 一等侍婢
第十九章 使出難題
第二十章 真正謀士
第二十一章 神祕紅衣
第二十二章 出使齊夏
第二十三章 曖昧不明
第二十四章 一觸即發
第二章 迷霧層層
第三章 改名換姓
第四章 不如相忘
第五章 進宮揭密
第六章 你是誰?
第七章 四美爭鋒
第八章 妃上無后
第九章 謎團紛呈
第十章 步步為營
第十一章 他人夫君
第十二章 鋒芒畢露
第十三章 詐死背後
第十四章 一去難還
第十五章 只道珍重
第十六章 進行驗身
第十七章 竟是石女
第十八章 一等侍婢
第十九章 使出難題
第二十章 真正謀士
第二十一章 神祕紅衣
第二十二章 出使齊夏
第二十三章 曖昧不明
第二十四章 一觸即發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十一顏
- 出版社: 東佑文化 出版日期:2014-12-24 ISBN/ISSN:978986600471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