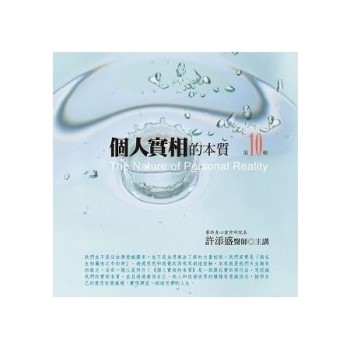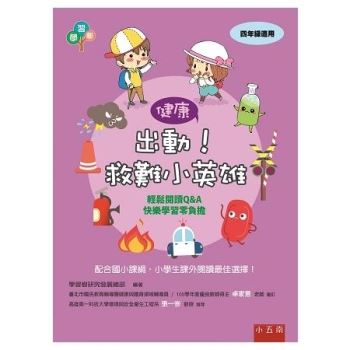斜坡上孤獨的立著三間捲棚頂小屋,和隱院的金碧輝煌,極盡奢華不同,這小屋極為質樸,好似一座遠離塵世的桃源。
喧囂的國公府裡竟有這樣幽靜的地方,這是哪裡?
太太帶她來這兒做什麼?
滿腹狐疑地隨太太過了拱橋,沿著木製的階梯來到小屋前,雲初這才發現,小屋簷上懸著一塊朱紅蝙蝠紋牌匾,上書三個碩大的篆字,想是這小屋的名字了,可惜除了中間的那個「女」字,其他的一概不識。
太太一擺手,把眾人都留在門口,只帶雲初進了屋,迎面一張香案,擺著牌位供品,香案後面的牆上掛滿了一幅幅女子畫像,或小巧玲瓏,或端莊典雅,畫得唯妙唯肖,栩栩如生,雲初恍然明白,這應該是董家的家廟了。
看著正中央一幅端莊嫻靜的女子畫像,雲初心中一動,不對,既是家廟,怎麼不供男人?這古代女子可是沒地位的,不是嫡妻又沒兒子的,都上不了族譜,再看這屋裡,連正位上都供著女子,彷彿回到了母系氏族。
國公府什麼時候這麼尊重、推崇女人了?她怎麼沒感覺。
可這不是家廟,又是哪裡?
心下狐疑,臉上卻不帶出來,見太太跪拜完起身看她,雲初就有樣學樣地點了三炷香,恭恭敬敬地插到獸鼎上,然後虔誠地跪在蒲團上磕了三個頭,起身立在太太身後。
無聲地注視著供案上的牌位,良久,太太低聲嘆道:「我們董家的女子,如能在這裡留下一個牌位,也是無上的榮耀。」
怎麼,這裡供的不是董家所有主母?
那這都是些什麼人,做了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才有資格供在這兒,被譽為「無上的榮耀」。
「姨媽,這裡……」
「妳小時候我曾帶妳來過,不想妳失憶後,竟都忘了!思前想後,還是再帶妳來拜拜,和妳說說,也免得妳做出……」聲音戛然而止,太太回身看著雲初,良久,才又嘆息一聲,「按說,萬歲允許女子出入集會,妳又是名聲顯赫,我不該約束妳的……」
「姨媽……」
「我們家族與別處不同,董氏自立族以來,已歷百年,到妳公公這一代,分了二十支,已經出了九十八個節烈,可謂世間少有,萬歲親口承諾,如果董氏能出一百個節婦,便可以造一個五孔麒麟牌坊,贈送御筆親提金匾,主母世襲誥命,並著史官修書立傳……」說著,太太眼裡閃出兩束異樣的光芒,昏暗中,有如毒蛇青幽幽的烈芒,陰森恐怖。
「雲初,妳和闌兒如能守得住……」呼吸突然變得急促,太太一把抓住雲初,「妳便是我們董家第一百個節婦!」
第一百面牌坊?
這便是太太嘴裡那無上的榮耀!
臉色一陣慘白,雲初身子歪了歪,不是太太抓著,就倒了下去。強穩住心神,雲初猛然抬頭,目光犀利地掃向牆上的畫像……
一生孤眠獨宿,青燈煢煢,冷夜寒風,只為死後能掙回那面陰森森、冷冰冰的牌坊,值得嗎?
董家這無上的榮耀,與她何關?
「她們……」雲初顫抖的手指向牆上諸女,「她們都是……」
拽下她的手,太太眼底閃過一絲不悅,「她們就是董家歷代的節婦、烈婦,董族的二十支中,我們是第十八支,一共出了十八個節烈,是族裡最多的,這也是我們這支的榮耀,比起她們,妳和瀾兒還能去各院轉轉,已是幸運了,祖輩上,女子守節,規矩是極嚴的,連內室都不准出……」說著,太太來到東牆角一張黃梨木八寶紋小櫃前,躬身打開櫃門,取出一本絲絹冊子,如珍寶般拿在手上,看了又看。
「姨媽,這是什麼?」
「是我們祖傳的《母訓》,裡面除了董家第一代主母留下的《婦言》、《婦行》、《婦德》三篇訓戒外,還記載了董家歷代節烈女子的生平和她們的戒語心得。按理,這應該傳給妳大嫂,但妳是我親外甥女,又是才女,我思量了很久,還是傳給妳更好,妳名聲顯赫,將來能在這上面留下隻言片語,也是後世人的榮耀。」
「姨媽,這……」
這個還是傳給大嫂更好!
見太太雙手遞過來,雲初一陣遲疑。
想起什麼,太太又縮回手,珍寶般攥得緊緊的,異常嚴肅地看著雲初,「按說我應該向祖輩一樣,等離世時再傳給妳,可自打妳……就性情大變,怕妳把持不住,才現在傳給妳,妳多學學祖輩的事蹟,事事慎之,時時戒之,也免得一時衝動,做下不可挽回的事情,只別讓妳大嫂知道了,又要攀比。」
見太太如此鄭重,已冷靜下來的雲初,不得不恭恭敬敬的雙手接過,佯裝認真的翻開,看了兩頁,清一色的蠅頭小篆,看得雲初眼冒金星,很想一把火燒了乾淨。
傳家寶似的把《母訓》偷偷地傳給她,太太可真找錯人了。
如果傳給姚瀾,興許這個事事謹慎,好出風頭的大少奶奶真能傳家寶似的供著,虔誠地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可惜,太太一己之私,竟傳給了她這個現代人,還想讓她這個大字不識的「才女」在上面留兩個字,光宗耀祖!
做夢!
她早晚一把火燒了這勞什子。
看著太太眼中煜煜的光彩,雲初恨恨地想著。
「雲初,這些回去再看不遲……」見她看得認真,太太心情大好,「來,我給妳講講畫像上的這些人。」太太說著,拉著雲初越過供案,來到畫像前,指著正中央的那幅三十左右,端莊典雅的女子畫像,道:「她就是我剛說的,我們董家第一代主母董薛氏,論起來,她是妳太祖奶奶的曾祖奶,也是我們董家的第一個節婦,不僅這貞女祠,族裡的烈女祠也供著她。」
原來這裡是貞女祠!
「這裡……」雲初想確認一下,話到嘴邊又改了口,「是後來建的?」
「嗯,其實也不算是……」太太點點頭,又搖搖頭,「這原是第一代主母守節的舊址,原本是三間茅草屋,妳太祖爺爺發跡後又重新翻蓋了,後來又經過了幾次修整,卻一直保持著原貌。」
「難怪這裡與府裡其他宅子不一樣。」雲初恍然大悟。
「這宅子現在看著古樸,在當時卻也算是奢華了,那時還沒有現在這種歇山、廡殿頂式的宅子。」
雲初點點頭,不再言語,只看著畫像。
太太就娓娓地講了起來。
「妳太祖爺爺的曾祖父在這董薛氏十七歲時便撒手人寰,留下兩個吃奶的孩子和幾畝薄田,日子太窮又雇不起人,她只得起早貪黑地勞作,有一日回去晚了,失足落到水裡,被路過的一位男子拉了一把,救了一條命,董薛氏自覺失節,回去後本想自裁,但因兒子太小,怕死了以後無人照看,讓董家斷了後,便是不孝,於是她生生地砍掉了那隻被拉過的手……」
不會吧!這麼殘忍的事,還拿出來廣告似的宣傳!?
雲初激靈靈打了個冷顫,下意識地看看自己的手,還好,小董和才五歲,不算男人。
「雲初……」正失神間,太太已踱到另一幅畫前,招手叫她。
「她是誰?」瞧見畫上之人竟梳著雙丫髻,雲初心下疑惑,「好像還沒出閣。」
「她的確沒出閣……」太太點點頭,「她就是妳的太姑奶奶,閨名叫董萍,打小訂了娃娃親,沒過門丈夫就死了,便在娘家守節。有一天,她隨妳太祖奶奶出門,遇到幾個無賴,見她長得漂亮,就當街調戲起來,說她那雙眼睛能勾魂。回去後,妳太姑奶奶覺得沒臉見人,硬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戳瞎了,傳到了萬歲那兒,妳太姑奶奶不僅被封了誥命,還特旨免除了我們這支的勞役,妳太祖爺爺也因此發了跡……」
頓了頓,太太又補充道:「為夫守節,妳太姑奶奶雖然沒有出嫁,卻也是盤了頭的,這畫像是她過世後,妳曾祖父為向世人彰顯她未嫁而節的事蹟,特意讓人將她畫成這個模樣的。」
沒出嫁也守節,守節也就罷了,還戳瞎雙眼,這哪是烈女,簡直是無極腦殘女!
難怪那曠世才女明明不喜歡董愛,明明知道他不久於人世,還傻呼呼地嫁進來,原來早被洗了腦。
不用再聽,董族這九十八個節婦烈婦中,大概有一半是瘋子!
看著太太的嘴一張一翕,雲初兩眼陣陣發暈。
「咦……」目光落在左邊的一幅七女圖上,雲初疑惑道:「這幅畫像怎麼這麼多人?」
太太順著她的手指望去,的確,不同於其他畫像,這幅畫正中央一把櫸木扶手椅上,端坐著一個酷似董萍的四十歲左右體態豐盈的婦人,身後恭順地站著六個妖嬈女子。
端詳了半晌,太太指著那個端坐的女子,道:「這就是妳太祖奶奶,她身後的六人是妳太祖爺爺的六個伺妾。」
「六……六個……伺妾?」雲初有些口吃了。
這也太多了吧!一娶就是六七個,就這樣,還要求女人節烈,真是變態的道德標準。
「難道,這七人……都……」
「是的。」太太點點頭,「她們一起做了烈女。」
「做烈……烈女!」
所謂烈,就是為節而死。
一個人殉節,那是情深意重,七人同時殉節,那是天方夜譚。
不會是董家為了湊數,逼著她們自殺殉節吧?
詫異地睜大了眼,雲初不可置信地看著太太。
「她們的確是同時做了烈女,我當初聽了這事,比妳還吃驚。」
「同……同時?」
太太肯定地點點頭,「因妳太姑奶奶的事蹟,妳太祖爺爺一路扶搖,到了南帝元年,已做了樊驤府同知,正趕上那年先皇駕崩,南帝年僅八歲,欺新君年幼,黎、赤兩國趁機大舉進犯,掠奪我國的鹽田,見天下離亂,刀兵四起,妳太祖爺爺毅然棄官從軍,仗著一身武功,很快就升到了宣慰使,一次奉命接送將士家眷,途遇強敵,妳太祖爺爺身負重傷,勉強保護大將軍之子逃脫。怕被賊兵掠去毀了清白,使妳太祖爺爺蒙羞,見他逃脫,她們七人便紛紛自裁。」
天啊!難怪董氏一族能出九十八個節烈,原來是這麼來的。
這都什麼世道,離亂中無力保護妻女,便請她們做烈女,自己逃命,事後表彰幾句,畫個圖像供在這兒,便是女人們嚮往的「無上的榮耀」了,他再別討女人,可也是「皆大歡喜」。
看著七女圖,雲初哂笑,她想起了前世的三國演義,諸葛亮火燒新野,劉備攜民渡江,遭遇曹操追兵,那糜夫人身負重傷,為救阿斗和保護自家的清白,縱身投入枯井,做了烈女,沒見劉備如何悼念,反是諸葛亮留錦囊,劉備甘露寺相親,智娶孫尚香被傳為佳話。
什麼節烈!
一群自私自利的男人,夫死女子必須守節,男人卻可繼續逍遙風流的制度,創造出一套如此變態畸形的倫理道德,被世人拿來表彰,偏偏又是這一群受害的女子拿來膜拜稱頌,做了節婦烈女,得了旌表,被寫入志書,便要教習他人模仿。
有如太太這樣,那煜煜生輝的眸光中,赤裸裸地寫著:丈夫死了,就不能再嫁,決不能再嫁!
看著太太的嘴一張一翕,語氣中滿是崇拜和思慕,雲初很想問問,她雖有這麼崇高的志向,立志要做節婦烈女,但不幸董國公長壽,竟活過了她,致使她雖然一生對董國公忠貞不渝,卻依然進不了這貞女祠,得不到那無上的榮耀,她會不會恨董國公的壽命太長了,竟沒像董愛一樣夭壽?
反過來想想,也難怪太太會如此,董家的節烈有如此驚人的數目,即便有像她一樣,不想節烈的女人,怕是也要被這畸形的倫理道德,驚人的數目禁錮致死。
面對這滿牆的烈女節婦,雲初心裡泛起陣陣寒意,在這節烈滿門的國公府,她要改嫁,怕是真的要等到滄海變成桑田了。
這條路,早已荊棘密佈,她要如何走下去?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誥命逆媳(1)的圖書 |
 |
誥命逆媳(一)【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雨久花 出版社: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2-1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320頁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8 |
古代小說 |
$ 198 |
羅曼史 |
$ 198 |
言情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225 |
文學作品 |
$ 31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誥命逆媳(1)
雨久花 繼《調香》《祖訓》後,再次為幸福而奮鬥
追加 繁體獨家番外
記住,妳是寡婦,要逆來順受,要忍辱偷生,要為董家掙回第一百面貞節牌坊……
啥咪!要她當個為牌坊而活的可憐小媳婦!
門都沒有!她不僅要為自己找到幸福,
還要打破傳統,「逆」爭上游,立下不朽傳奇
丈夫屍骨未寒,她就在靈堂上考慮改嫁的問題!
不知她是不是古往今來的第一人?
可是,不考慮這些,她又能如何呢?
穿越成了沖喜新嫁娘,老公已經掛點了,
這倒還好,既然是沖喜嘛,失去靠山也在合理範圍內,
她只能對那位無緣的老公,說聲「一路好走」。
不過,當她發現──
送嫁的母親還沒走,婆婆就偷偷命人毒啞她,
小姑尖酸刻薄,妯娌個個陰陽怪氣,
還有一個色咪咪的三伯對她虎視眈眈!
最可怕的是──她竟然肩負幫家族掙回第一百面貞節牌坊的重責大任!
從此,她不許四處遊蕩,不許穿彩色衣服,不許吃大魚大肉,
不許對男人笑,不許想男人,就連走路遇到男人,都要躲得遠遠的!
天啊!她可是來自標榜自由民主,人權至上的現代啊!
不行!她不能就這樣乖乖認命,
即使身陷等級森嚴的大宅門,即使已經誥命加身,
她也要為自己爭取幸福,她絕對拒絕做個逆來順受的乖媳婦……
作者簡介:
雨久花
女,東北人,喜歡看書,作白日夢,因工作性質特殊,常年漂泊在外,開始寫文純粹是因為一個人在外空閒太多,到如今忙碌了之後,動筆寫點什麼,已經成了一種寄託。
曾出版《調香》、《祖訓》等。
章節試閱
斜坡上孤獨的立著三間捲棚頂小屋,和隱院的金碧輝煌,極盡奢華不同,這小屋極為質樸,好似一座遠離塵世的桃源。
喧囂的國公府裡竟有這樣幽靜的地方,這是哪裡?
太太帶她來這兒做什麼?
滿腹狐疑地隨太太過了拱橋,沿著木製的階梯來到小屋前,雲初這才發現,小屋簷上懸著一塊朱紅蝙蝠紋牌匾,上書三個碩大的篆字,想是這小屋的名字了,可惜除了中間的那個「女」字,其他的一概不識。
太太一擺手,把眾人都留在門口,只帶雲初進了屋,迎面一張香案,擺著牌位供品,香案後面的牆上掛滿了一幅幅女子畫像,或小巧玲瓏,或端莊典雅,畫得唯...
喧囂的國公府裡竟有這樣幽靜的地方,這是哪裡?
太太帶她來這兒做什麼?
滿腹狐疑地隨太太過了拱橋,沿著木製的階梯來到小屋前,雲初這才發現,小屋簷上懸著一塊朱紅蝙蝠紋牌匾,上書三個碩大的篆字,想是這小屋的名字了,可惜除了中間的那個「女」字,其他的一概不識。
太太一擺手,把眾人都留在門口,只帶雲初進了屋,迎面一張香案,擺著牌位供品,香案後面的牆上掛滿了一幅幅女子畫像,或小巧玲瓏,或端莊典雅,畫得唯...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新寡
第二章 哭靈
第三章 籌謀
第四章 露院
第五章 牌坊
第六章 暴歿
第七章 妯娌
第八章 閨密
第九章 面試
第十章 急智
第十一章 簽約
第十二章 子嗣
第十三章 嫁妝
第十四章 虐奴
第十五章 衝突
第十六章 罰跪
第十七章 復得
第二章 哭靈
第三章 籌謀
第四章 露院
第五章 牌坊
第六章 暴歿
第七章 妯娌
第八章 閨密
第九章 面試
第十章 急智
第十一章 簽約
第十二章 子嗣
第十三章 嫁妝
第十四章 虐奴
第十五章 衝突
第十六章 罰跪
第十七章 復得
商品資料
- 作者: 雨久花
- 出版社: 東佑文化 出版日期:2015-02-17 ISBN/ISSN:978986600475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