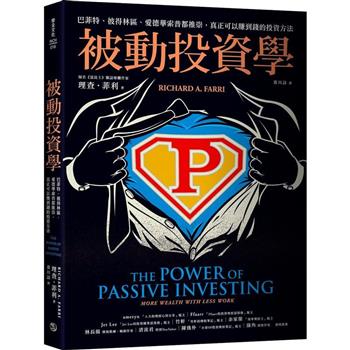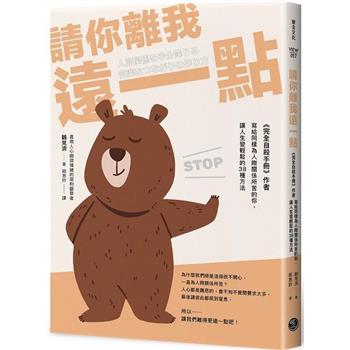窺視他人的生活,將導致自身的毀滅。你,有自信抵抗好奇心的蠱惑嗎?
當代德國文學新典範!優美、精準、卻又冷冽得令人不寒而慄
融合幻想寓言、驚悚小說、黑色幽默、哲學思辯的嶄新文體
帽子啪答一聲戴上頭頂時,頭頂上的東西好像全被消滅了,也許是頭髮,也許是思想,總之是他腦海的一部分。他感到有些東西沿著一條路徑鑽進他的體內。他聽見有東西在他的身體裡啪啪作響,同時內部隱蔽的東西流向身體外部,外部的東西流進了內裡。
西蒙.布洛赫,一個普通上班族。他曾想成為電影作曲家,但這個人生夢想已早早被埋葬。他認命於生活的常軌,直到那天,一位「老友」意外地重新闖入他的世界,攪動他刻意塵封的過往回憶,打開他生命中禁忌的一章……也給了他一個神奇的機會。一頂帽子。他將帽子戴上,於是親眼目睹自己的消失。他,隱形了。
西蒙從乾枯陷落的人生中解脫了。他可以改變自己的人生,甚至是別人的。他充分利用帽子賦予他的能力,盡情徜徉於不可思議的自由之中。但不久後各式問題接踵而至──這頂帽子究竟是怎麼來的?老友和帽子是什麼關係?隱形帽的極限何在?而愈形劇烈、難以繼續忽視的疼痛又是怎麼回事?為了弄明白這些疑惑,西蒙.布洛赫得做些他從沒想過的事情……
他,踰越了那道界限。
如果沒有人看得見你,那麼最終你還會是你自己嗎?人,為何是人?自我又是什麼?德國備受矚目的中生代小說家馬庫士.歐思,以細緻而節制的筆觸,精準切入人性與文明最脆弱的疑點。
作者簡介
馬庫士.歐思
1969年生於德國費爾森(Viersen),現居卡爾斯魯爾(Karlsruhe)。他的小說已譯為十四種語言,並獲得許多獎項,其中包括2000年開放麥克風(open mike)獎、2002年諾因史法茵州文學獎、2003年馬堡文學獎、2003年林布文學獎、2006年亨利.海涅文學獎、華特.史考特獎、羅畢爾最佳歷史小說金獎等;以及近年獎項如2008年巴登符騰堡州文學獎金、克拉格福特(Klagenfurt)奧地利電信文學獎、北萊茵州文學獎等。為當今德國文壇備受矚目的小說家。
目前已出版著作有:《在棺材後面,誰去了哪裡?》(2001)、《身體》(2002)、《教師休息室》(2003)、《卡塔莉娜》(2006)、《逃亡練習》(2006)、《房間女侍》(2008)、與《紡紗腦》(2009)。
譯者簡介
彤雅立
1978年生於臺灣臺中,以鑽研德國電影與德語文學翻譯為業。著有詩集《邊地微光》(女書)、《月照無眠》(南方家園),譯有艾芙烈.葉利尼克《美妙時光》(商周)、法蘭茲.卡夫卡《給米蓮娜的信──卡夫卡的愛情書簡》(書林,合譯)等書,主編並翻譯《月照無眠詩聲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