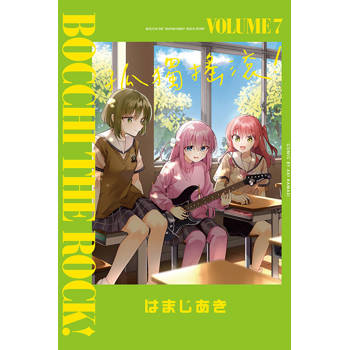她(紅瓦兒)是良臣遺孤,純真善良,燦笑如同月下精靈。
青梅竹馬、此情可待,
她的心願,就是長大成為他的王妃。
他(銀冀)是一國之君,尊貴淡雅,卻擔負著最深沉的責任,
朝政干戈,詛咒之禍,
他該如何讓她笑坐國妃之位?
他(銀翟)是王族棄子,冷漠殘酷,幾度淪落終返王宮。
危機四伏,陰謀重重,
她成為他奪回王權、展開報復的最好棋子,新仇舊恨如何解?
他們與她,一次次情緣交錯,
她的眸光堅定而執著,
拋卻所有恨仇,將用什麼來守護最後的愛?
作者簡介
冰冰七月
80後,獅子座,中文系畢業,定居深圳。作品風格多樣,人物性格突出,情節曲折感人,曾接受過網路廣播電臺一小時人物專訪,中國報告文學網人物專訪,瀟湘書院、紅袖添香等多家知名文學網訪談。
已著作品:《南詔王妃》全四部、《冤家系列》三部曲、《名門千金》上、下部
《明愛暗戀補習社》、《第一格格》、《帝國絕戀》、《七年之暖》、
《總裁爹地酷媽咪》、《邀君寵.美人憐》《漫步雲深處》《臨時媽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