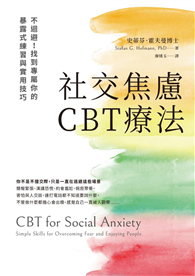第一章 初夜權
清晨的街道籠罩在白茫茫的霧中。
街道兩旁林立著數百家商鋪,其中只有一間客棧殘門半開,裡面黑漆漆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其餘則是戶戶閉門。
萬籟俱寂,整座宛如死城。
就在這時候,突然從遠處吱吱呀呀地駛來一輛車。拖著車的兩頭瘦騾子低著頭緩緩地往前走著;大風呼呼地吹著車頭的紙幡。紙幡吹開,後面坐著一名表情僵直的車夫,乍看就像僵屍一般。
這是一輛運屍出城的靈車。破舊的木板車上橫七豎八地堆滿了十幾具面目猙獰的屍體,所有屍體的脖子部位都有明顯的勒痕。
「快走!」從濃霧深處傳來了幾聲粗暴的喝令。
穿過迷亂的霧靄,街道的盡頭是一座剛搭起的絞刑台,四周站著幾十名劊子手,更遠一點的地方坐著一名監刑官,護衛分列兩旁。
台上站著幾排衣衫襤褸的犯人,其中最為顯眼的是一名年輕美麗的女子,她大概二十幾歲的年紀,黑髮披散,一張臉蒼白如槁,從身上破舊的麻布短衫下,露出戴著腳鐐的雪白雙足,皮膚都被磨破了。
她就像一個沒有靈魂的木偶般,僵直地站在絞刑台上。
「抬起頭來。」劊子手喝令了一聲。
女子順從地將頭顱緩緩昂起,木然地看了一眼打好結的絞繩,隨後對著劊子手,嘴角彎了彎,邪魅的一笑。
大驚失色的劊子手頓時一頭栽倒在地,口吐白沫昏死了過去,兩旁的侍衛立刻迅速上前將昏死的人抬走,另一名劊子手馬上遞補過去,他的眼裡佈滿了血絲,額頭一片晶亮細密的汗珠,俐落地將繩索套在女子細嫩的脖頸上。
霧越來越大,能見度不足三丈,監刑官不耐煩地敲著手裡的格殺令。就在距離他不到一丈遠的地方,一輛裝運著屍體的靈車正經過,旁邊還有兩輛正在整車待發。
這時台上的女子張開乾裂的嘴唇,唱起了小曲,一連串的吟唱從嗓子裡飄了出來,如哀鴻夜啼,在靜謐的廣場上空迴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
她在唱什麼?
監刑官一驚,手裡的茶水潑灑出來;就連台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們也禁不住打起了寒顫。
而麻木的犯人們彷彿受到了歌聲的召喚,都將目光投向了她,絕望的眼中漸漸升起希望的光芒,而她更是高高昂起頭顱,淒冷的目光彷彿洞穿了低沉的霧氣,所有的犯人都開始跟著她一起歌唱,歌聲漸漸由低沉變得高亢,每個人都懷著必死的決心,異口同聲地唱著: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
監刑官顯然是心虛了,急命行刑。
隨著格殺令落地,「唰-」地一聲女子的雙腳拉得懸空,糾纏在脖間的繩索如蛇一般地越箍越緊,將她的臉勒成了紫色,然而淒哀的呼喚聲卻從喉嚨深處清晰地傳了出來:「川兒-龍兒-龍兒︱」
對死亡的恐懼和受刑的痛苦,絞刑架上的人垂死地掙扎著。
霧氣更濃,絞刑架被一片濃霧所包圍。
突然,從大霧裡伸出一隻青筋暴露的手,像是身子已經被死亡拖去了另一個空間般,只留下一隻手極力想要抓住什麼……
就在那隻手即將觸摸到一張驚愕的面頰時,夜空中傳來了一聲讓人驚心動魄的尖叫。
深夜。
三更剛過。
在一望無際的敕勒川旁,安置著三、四十個錯落的帳篷,裡面住著兩個月前遊牧來此的羲和族人,剛才那聲驚叫就是從這裡的一個帳篷裡發出來的。
驚叫聲過後,帳篷外立刻響起了一陣凌亂的腳步聲,一名乳母模樣的婦人,披著衣服急急忙忙衝了進來,一邊跑一邊喃喃地說著:「一定是那個夢境又出現了,一定又是那個夢境又出現了。」
啪的一聲火光亮起,照著床塌上冷汗涔涔的少女。
「乳母,」少女一頭撲進乳母的懷裡,眼淚漣漣,聲音哽咽說:「乳母,我又夢見她了,我又夢見她了……」
「我知道了,孩子。」乳母憐惜地抱著她,手輕輕地撫著她的背,下顎抵在她的頭上,輕聲地安慰著:「妳又做惡夢了,別怕,有乳母在呢……別怕……」
「乳母……她死的好痛苦……」少女抬起淚眼,無助地描述著夢裡的所見,「她每次看我的眼神都那麼痛苦……她一直叫我的名字,她知道我叫龍兒……她一定很不想死,她一定很想活下去……乳母,她不想死……」說到這裡,少女已經泣不成聲了。
「乖,這只是個夢而已……你不要多想,也不要害怕,妳只是做了噩夢而已。」乳母溫和地拍著少女的肩膀,好聲地安慰著,眉頭不自覺的皺在一起。
兵荒馬亂,朝不保夕,噩夢誰不曾有!只是現在……草原上一天比一天混亂。尤其是雲羅人強大了之後,比噩夢還要令人膽寒的日子越來越多了。羲和族是草原上的弱者,是一支居穹廬氈帳,逐水草畜牧的小部落,人口只有區區幾百人,而雲羅人……是等同於惡魔的種族。
惡魔!
想到這裡,孀居的婦人忍不住輕歎了一聲,她才三十出頭的年紀,常年的遷徙和艱辛的勞作,令她的鬢角過早地染上了白霜。
聽見乳母歎息,龍兒懂事地停止了哭泣,抬起頭抹了抹眼淚,安慰似地在乳母的額頭輕輕吻了一下,又躺回了床上,嗚嗚咽咽地抽泣了一會兒,在乳母的安撫下睡著了。
乳母幫她蓋好了被子,坐在燈下守著,嘴裡輕聲哼著歌謠,手輕輕地拍著她。
「可憐的龍兒。」半晌,婦人突然發出了一聲感慨。
她一直記得十四年前的那個傍晚,首領從一堆蓬草中間將龍兒撿回部落的場景,那時候孩子的身上只有一件羊皮小襖和半塊玉璧,小襖的口袋裡有一塊羅帕,上面潦草地寫著生辰八字和名字,那天她正在給馬添加草料,聽見身後的歡呼聲,一回頭看見那個小小的孩子躺在首領的懷裡,就像是一顆珍珠躺在蚌殼裡。
她的心就像被一隻小手輕輕的觸摸過,剎那間被打動了。
年復一年,北冥龍兒漸漸長大,並且越來越聰明美麗,彷彿草原上的洛桑花。
「龍兒……」乳母揉了揉發紅的眼睛,低下頭,吻著她的額頭。
天很快就要亮了,折騰了一大半夜,乳母蘿蘿又累又睏,打起了瞌睡。就在這時,忽然聽見門外有人邊哭邊喊:「不好了,不好了,白楚無雙自殺了。」
渾身一顫,猛然睜開眼,疾步跑了出去。
清晨,東方剛剛翻起魚肚皮,大風呼嘯而來吹的她幾乎站不穩,天上流雲急走、枯草卷天,大風卷起沙石抽的人臉頰生疼,她不由得閉上眼倒退了一步。而時空彷彿也瞬間斗轉星移,回到了昨天晚上……
孤月當空,明月包裹在朦朧的光暈中。
在白楚無雙和阿木合成親的婚禮上,姑娘們穿著最美麗的衣服,戴著動物骨頭做成的飾品,在篝火的熊熊火光中,載歌載舞,「乾杯!」不知道是誰喊了一句,將酒潑向天空。
人群頓時沸騰起來,身著獸皮的男人們紛紛起身,舉起酒杯,將馬奶酒潑向天空,空氣中響起了一陣爽朗的笑聲,他們拋下手中的杯子,拉起姑娘們的手,隨著胡琴聲,跳起了歡快的舞蹈。
就在這時候,惡魔悄悄地逼近了,黑夜深處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雲羅人的鐵騎幽靈般到了眼前。
琴聲嘎然而止,眾人停下了舞步。
火光照耀下,雲羅貴族首領得意洋洋地坐在馬背上,猥瑣的目光落在驚慌失措的白楚無雙身上,邪惡的笑意浮上了他的唇角:
「聽著,我是你們的新主人阿紮都大人,奉我王的命令,前來行駛權力:我雲羅貴族有權對羲和族等草原上八個部落行使初夜權,這是文書。」
說完啪地一聲將文書往地上一扔,一摸落腮鬍大笑起來:「聽明白沒有?就是說我雲羅貴族享有統治區內任何民女結婚,都擁有在她的新婚之夜與她過夜的權力。」
看著呆如木雞的白楚無雙又是一陣倡狂地大笑:「現在,我就要行使我的權力了。」說完一揮手,騎兵一擁而上抓住了白楚無雙。
阿都紮的話就一聲雷,嚇呆了所有在場的人,眼看妻子受辱,阿木合不顧一切的衝了上去,卻被身經百戰雲羅騎兵打倒在地,鋼刀架在脖子上。
絕望就像天上濃厚的烏雲劈頭砸了下來。
雲羅人是劊子手!是惡魔!是索命的閻王!
而羲和族人……是羊!
騎兵將白楚無雙拖進一個帳篷裡,可憐的白楚無雙早已嚇的癱倒在地,而阿紮都就像一頭饑餓的惡狼撲向了食物……
「不︱不要︱求你放過我吧……求你……」她身心俱顫地掙扎,卻引來阿紮都的放蕩大笑。
阿紮都輕鬆地控制住她的雙手,譏笑道:「妳只不過是我的妓女而已,妳們八個部落的女人都是雲羅人的妓女,妳們的新婚之夜屬於雲羅貴族,你們的身體將無窮無盡地為雲羅人生育後代,哈哈︱」
在雲羅貴族的大笑聲中,門外的眾人全都低著頭,眼前的嘲笑聲和獸行就像一把鈍鈍的匕首,狠狠地刺進每一個羲和族人的心上。
深夜,風冷冷的吹著,落下的眼淚沒有人會在意。
漸漸地,耳邊呼救聲變得孱弱了,哭泣變成了抽泣……直到無聲……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一夜傾城(1):爭寵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0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夜傾城(1):爭寵
她是草原上羲和族的公主,她曾潦倒於賊寇,寵冠於後宮,又曾執掌王權統帥三軍,還曾輾轉於幾個王侯將相的身側。一個女人能夠得到的世俗的權力和榮耀,都曾短暫的擁有過,只是愛情於她來說,卻是永遠的奢侈品。一場「初夜權」引起的亂世之爭。草原八部選出的第一美人,究竟是待宰羔羊?還是與命運抗爭?
騰訊點擊:130萬。
評論:
1.這是一個充斥著肉欲、殺戮與恐慌的戰亂年代,龍妃的純真宛如一滴清水,折射出了世界的虛偽與自私……寫作手法法大氣,故事神秘、跌宕起伏,愛情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草原戰爭。
2.架構嚴謹,行文流暢,很好看的書,第一次看到有關「初夜權」的故事,很精彩。不得不看的一本書。
作者簡介:
桑甜,處女座女子,畢業於蘇州大學。喜歡唱歌,愛在陽光下行走,喜歡聆聽鍵盤在手指下輕快跳躍的聲音,喜歡在浴缸裏閱讀,喜歡寂靜的午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初夜權
清晨的街道籠罩在白茫茫的霧中。
街道兩旁林立著數百家商鋪,其中只有一間客棧殘門半開,裡面黑漆漆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其餘則是戶戶閉門。
萬籟俱寂,整座宛如死城。
就在這時候,突然從遠處吱吱呀呀地駛來一輛車。拖著車的兩頭瘦騾子低著頭緩緩地往前走著;大風呼呼地吹著車頭的紙幡。紙幡吹開,後面坐著一名表情僵直的車夫,乍看就像僵屍一般。
這是一輛運屍出城的靈車。破舊的木板車上橫七豎八地堆滿了十幾具面目猙獰的屍體,所有屍體的脖子部位都有明顯的勒痕。
「快走!」從濃霧深處傳來了幾聲粗暴的喝令。
穿過...
清晨的街道籠罩在白茫茫的霧中。
街道兩旁林立著數百家商鋪,其中只有一間客棧殘門半開,裡面黑漆漆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其餘則是戶戶閉門。
萬籟俱寂,整座宛如死城。
就在這時候,突然從遠處吱吱呀呀地駛來一輛車。拖著車的兩頭瘦騾子低著頭緩緩地往前走著;大風呼呼地吹著車頭的紙幡。紙幡吹開,後面坐著一名表情僵直的車夫,乍看就像僵屍一般。
這是一輛運屍出城的靈車。破舊的木板車上橫七豎八地堆滿了十幾具面目猙獰的屍體,所有屍體的脖子部位都有明顯的勒痕。
「快走!」從濃霧深處傳來了幾聲粗暴的喝令。
穿過...
»看全部
目錄
楔子 009
第一章 初夜權 011
第二章 逼婚 021
第三章 囚禁 041
第四章 被俘 059
第五章 與君再見 081
第六章 一入宮門深似海 091
第七章 救人 132
第八章 最毒婦人心 156
第九章 爭寵 165
第十章 失身 189
第十一章 真相 207
第十二章 被逼做祭司 267
第十三章 鳳還巢 288
第一章 初夜權 011
第二章 逼婚 021
第三章 囚禁 041
第四章 被俘 059
第五章 與君再見 081
第六章 一入宮門深似海 091
第七章 救人 132
第八章 最毒婦人心 156
第九章 爭寵 165
第十章 失身 189
第十一章 真相 207
第十二章 被逼做祭司 267
第十三章 鳳還巢 288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桑甜
- 出版社: 樸實 出版日期:2012-02-29 ISBN/ISSN:978986602843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12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