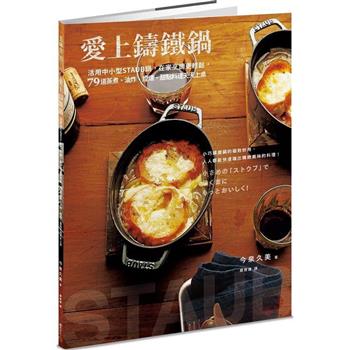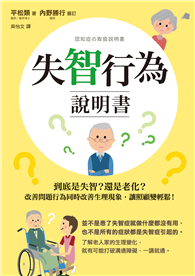宮部流時代小説新視界
通靈少女阿初的第二場華麗冒險!
天狗來啦,來擄走江戶最標致的姑娘!
血色朝霞下、櫻雨紛飛的林間,
狂風席捲如花似玉的待嫁閨女……
接二連三發生詭異的神隱,難不成真是天狗作亂?
能見人所不能見、聞人所不能聞的阿初,
這回要與會說話的虎斑貓阿鐵,一起追查匪夷所思案件背後的真相。
為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美麗足跡而寫──
隨宮部最溫柔的目光,最謙遜的筆觸,
在似遠又近的世間風景底層,走一遭。
【故事簡介】
世上真有極致的美嗎?
教人痴迷沉醉、教人嫉妒瘋狂,甚至自取滅亡……
通町一間小飯館「姊妹屋」的招牌姑娘阿初,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平日她忙著幫嫂嫂張羅生意,偶爾「臨危受命」,暗中探查江戶各角落的奇異之事。
這年春天,櫻花依舊燦爛盛放,然而,歡欣準備出嫁的木屐鋪獨生女、蔬果鋪引以為傲的長女,卻接連消失在清晨一陣突如其來的狂風裡。
無法冷眼旁觀的阿初,拉著精通算學的木訥少年右京之介四處奔波,希望尋得蛛絲馬跡。不料,途中竟多次撞見觀音菩薩的身影,還遇上一隻能言善道的虎斑貓,讓案情益發撲朔迷離……
阿初奮力對抗的敵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花季未了,無辜的少女們是否仍有一線生機?
【內文節錄】
「多美呀,那頭髮,那肌膚。」竊用神明寶相的魔物渴望地伸出手,流瀉的衣袖輕輕滑過,撫上阿初的臉頰。阿初打了個寒顫,那衣袖像冰一樣冷。
──摘自第二章〈消失的人們‧無盡之夜〉
作者簡介:
宮部美幸
Miyabe Miyuki
1960年出生於東京,1976年以《吾家鄰人的犯罪》出道,當年即獲得第26屆《ALL讀物》推理小說新人獎,1989年以《魔術的耳語》獲得第2屆日本推理懸疑小說大獎、1999年《理由》獲第120屆直木獎確立暢銷推理作家地位,2001年更是以《模仿犯》囊括包含司馬遼太郎獎等六項大獎,締造創作生涯第一高峰。
寫作橫跨推理、時代、奇幻等三大類型,自由穿梭古今,現實與想像交錯卻無違和感,以溫暖的關懷為底蘊、富含對社會的批判與反省、善於說故事的特點,成就雅俗共賞,不分男女老少皆能悅讀的作品,而有「國民作家」的美稱。近來對日本江戶時代的喜好與探究,寫作稍偏向時代小說,近期作品有《終日》、《孤宿之人》、《怪談》等。2007年,即出道20週年時推出《模仿犯》續作《樂園》,為近年少見的現代推理、自我挑戰鉅作。
譯者簡介:
林熊美
畢業於台大,現為專職翻譯。譯有《糊塗蟲》、《終日》、《顫動岩》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擄人案
朝霞怪象
江戶深川淨心寺後方的山本町,有個姑娘突然失去蹤影。這便是事情的開端。
失蹤的姑娘單名秋,芳齡十七,是木屐鋪的獨生女,再半個月就要嫁到淺草駒形堂附近的料理鋪。這椿親事男女雙方情投意合,待嫁的姑娘也衷心期盼著穿上嫁衣的那一天。
阿秋是在朝霞濃豔的春日早晨消失的。
那一日,木屐鋪的老闆,即阿秋的父親政吉,漫漫長夜竟做了一整晚惡夢,起身之際只覺比睡前還累。若不在天亮前到工坊,拜過神明、理過工具,政吉便吞不下早飯。因此,他忍著惡夢帶來的陣陣頭痛,緩緩下樓。
折磨政吉的惡夢威力不小,即使在夢醒後,仍讓他心有餘悸。好似繫上沒乾透的兜襠布,腰背整個不對勁。每踩一階樓梯,膝頭就不爭氣地顫一下。
政吉暗想,不行哪。都怪最近總過得戰戰兢兢,老大不自在。一定是這樣。
送獨生女阿秋出閣,政吉難免感到寂寞。打親事談定以來,女兒一天比一天明豔動人,望著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及粉頰上浮現的燦爛笑靨,政吉又是懊悔又是氣惱,彷彿心窩被狠勁戳了一下,滋味很不好受。
如今他雖已是獨當一面的工匠,好歹擁有一間小鋪子,但一路的艱辛困苦,委實一言難盡。一旦話起當年,縱然是這把年紀,仍不禁眼熱鼻酸。他之所以熬得過來,全是為了女兒阿秋。
阿秋將要遠走,要離開自己身邊,往後再也不能保護她、逗她歡喜。當然,那是阿秋的心上人,但在政吉眼中,不過是個小毛頭。他的思緒波濤洶湧,不止一次想著:「要我把心肝寶貝交給這種人,萬萬辦不到!」
然而,政吉小心翼翼,不在表情與態度上洩漏一絲半點。每當壓抑的情感就快決堤,他總咬牙強自按捺。大概是忍過頭,才會做那種怪夢。
在夢裡,政吉想殺阿秋。
(天底下哪有做父親的會想殺女兒?)
走在擋雨窗緊閉的暗廊下,政吉不住搖頭。
昨晚的夢境裡,政吉身處一座陌生大宅,孤伶伶站在似無邊際的房間正中央。一切肇端於此。
不知為何,政吉急迫地追著某人。對方就在宅邸中,於是政吉大步向前,幾乎是奔跑著打開奢華的拉門。
拉門發出清脆的聲響,左右退開,眼前出現和身後房間一樣寬廣的榻榻米汪洋。政吉飛快穿越,打開下一道拉門,不料仍是個大房間。
政吉跑過一個又一個房間,推開一道又一道拉門,漸漸有些氣喘吁吁。不久,頭頂上傳來大群人的笑鬧聲,抬眼一看,他才曉得那源自刻在拉門上方鑲格窗的嬌豔觀音菩薩。
每間房都有尊以透籠手法精心雕琢的觀音菩薩,姿態不同、嗓音不同、笑容不同,但全在嘲笑政吉。
(瞧瞧他。)
從一扇鑲格窗到下一扇鑲格窗之間,觀音菩薩的竊竊細語不絕於耳。
(多可笑,找成那副德性。)
(有得他找了。)
(找得到嗎?)
(怎麼可能。)
政吉心想,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不會如此低俗訕笑。那一定是妖魔,是妖魔假冒觀音菩薩矇騙我……
政吉流著汗、喘著氣,繼續奔跑,邊開門闖進下一間房,邊發瘋似地告訴自己。他在夢中不停狂奔,拚命說服自己這是夢、是夢、肯定是夢。
只是,房間卻連綿不絕。拉門開了又開,像是沒有盡頭。鑲格窗上的觀音菩薩喧鬧聲益發高亢,恍若青樓的賣春婦。優雅的衣裳裡露出雪白手臂,召喚政吉似地不斷笑著。
啊啊,那肌膚是多麼美麗,那眼睛是多麼迷人。
簡直……簡直……就和阿秋一樣。
霎時,政吉驚覺手中握著一把鑿子。
我怎會帶著這種東西?政吉不禁大吼。
於是,陸續經過頭頂的觀音菩薩異口同聲回答:
「為了殺你女兒呀。」
「殺阿秋?我要殺阿秋?」
「是啊,是啊。」
「我怎麼可能殺阿秋?阿秋是我心愛的女兒。」
政吉不由得回嘴。他想駐足與觀音菩薩正面對峙、嚴詞反駁,一雙腿卻停不下來。明明喘不過氣,喉嚨咻咻有聲,仍不得不繼續奔馳。
此時,觀音菩薩的話聲灌頂:
「你會殺害阿秋。」
「不管你再疼愛女兒都會下手。」
「你一定會殺死阿秋。」
「不可能不殺她。」
「不、不、不!」政吉大叫。「阿秋是我女兒!」
然而,觀音菩薩卻歌唱般綿綿低吟:
「是女兒也會殺。」
「因為阿秋要拋棄你。」
「忘記父親的養育之恩。」
「到心愛的男人身邊。」
「以後就算你生病……」
「阿秋也不會回頭瞧你一眼。」
「一腳把你踢開……」
「阿秋內心肯定在竊笑。」
「就算你墳上長滿青苔……」
「阿秋也懶得管。」
「就算你曝屍荒野……」
「阿秋也不會難過。」
「所以你會殺死阿秋。」
「你會殺死她。」
「你豈能不殺她。」
政吉根本發不出聲,冷汗滾滾而下。他髮髻散亂,灰白相間的髮絲迎風亂舞,邊跑邊哭。「不、不,我才不會殺阿秋!」
乾澀的喉間擠出這句話時,觀音菩薩的面孔驟然變樣。
原本美得難以逼視的容貌,突然口裂至耳,變成青面獠牙的鬼臉。下一間房,下一扇鑲格窗,所有觀音菩薩將衣袖撩到肩上,一齊飛身撲向政吉。
「既然你沒辦法下手,我只好收拾你的性命。」
政吉大聲哀嚎。由於恐懼太甚,他不禁叫道:
「好,我殺阿秋就是!」
政吉渾身哆嗦,一回神,已站在通往工坊的樓梯口。看樣子,他是不意想起睡醒後本應拋開的夢,迷迷糊糊地發呆。
(真不吉利。)
政吉雙手抹臉,大大吐口氣,邁出腳步。
唉,做這什麼怪夢,今兒個最好小心點。那多半是在警告我會受傷,暫且別碰刀吧。
如今政吉身為老闆,這倒不是難事。從旁監督弟子及僱工幹活也是一天。
破曉前,穿過尚未打開遮雨窗的家中,獨自下到工坊。女兒阿秋和老婆阿信老取笑政吉這個習慣,說爹爹活像神氣的檢校官 。
確實,在熟悉的屋內,縱使不點燈,政吉也和夜能視物的貓一樣來去自如。但趁一日之初前往漆黑的工坊,於他不單是種習慣。
夜裡人人沉睡之際,神明會駕臨,在工坊走動、碰觸工具,留下「氣」。
當政吉還是小工匠時,即對此深信不疑。這並非無稽之談。
好比趕夜工沒收拾乾淨就歇息,隔天鐵定會出事。不是某工匠割到手,便是該運來的木材沒送抵。狀況或大或小,卻都無可避免。
政吉認為,這是偷懶貪睡,沒整理妥當便就寢,惹怒夜半降臨的神明,導致神明不肯留下「氣」的關係。
所以,一日之始,先單獨至工坊確認「氣」的存在與否,並向神明致上謝意,對他而言是項重要的儀式。且必須在天光進屋前完成,否則「氣」很快會散逸。
政吉振作精神,伸手推開工坊的門,隨即發現裡頭有人。
「爹?」
是阿秋。
只見她已換好衣服,髮髻也梳得整整齊齊,似乎早早就待在那兒。
阿秋雙膝並攏,端坐在收集木屑的木箱旁,腳邊一根蠟燭悄然綻放微光。多半是她從房裡拿來的吧。
這樣的事還是頭一遭。
「妳在這裡做什麼?」
政吉不覺語帶責備,阿秋微微一笑:
「別一早就板著臉嘛。」
「板著臉……」
剛才那場惡夢去而復返,掠過政吉的腦海。
「我的臉色這麼難看嗎?」
阿秋明亮的雙眸望著父親,嗔道:「直到最後,爹爹都不喜歡我進出工坊。」
木屐師傅的工作絕非粗活,卻也是一門需動刀的生意。所以,自阿秋出生後,政吉始終嚴禁她踏入工坊。
若有個萬一,讓孩子受傷可不得了。尤其是女孩,即便僅是不慎傷到手背,難保不會耽誤她的將來。
持同樣想法的匠人不在少數。石鋪是如此,磨刀鋪亦是如此。然而,無論多小心,總有防不勝防的時候。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政吉一向不允許孩子靠近工坊。
「我就要出嫁,」阿秋垂眼幽幽開口,「不再是家裡的女兒。在那之前,我想看看爹每日做木屐、繫木屐帶,辛苦賺錢拉拔我長大的工坊。」
政吉僵立門口,腋下不斷滲出汗水。
「像這樣……」阿秋拿起握柄裹著布的鑿子,「摸摸沾染爹汗水的工具。」她仰望政吉,「讓我留下一點回憶,您不會不准吧。」
然而,政吉無法回答。
「昨晚,我做了個詭異的夢。」或許是瞧不清政吉僵硬的表情,阿秋笑著繼續說:「我獨自待在一幢大宅,可是,有人在追我。」
政吉扶著拉門,心臟怦怦狂跳。阿秋做了和我一樣的夢?和我同一個夢?
「好恐怖。」阿秋聳起肩,把弄著鑿子。「我拚命跑,沿途打開一扇又一扇拉門,房間卻一個連著一個,沒有盡頭。」
喉嚨乾澀的政吉嚥下唾沫,問道:「妳在逃命?」
「嗯,是呀。」阿秋點頭,「我邊哭邊逃,因為我曉得,要是被抓到就會沒命。」說到這裡,她刻意笑出聲,「真是場怪夢。醒來後,我不禁思索,一定是我其實很害怕出嫁,不由得直掉淚。坦白講,我也不想嫁人,情願一輩子陪伴爹娘。」
一直站在門旁的政吉,腦中赫然響起粗暴的吼聲。
(說謊!)
政吉渾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竟會這麼想。
「爹,我呀,是木屐鋪的女兒。」阿秋繼續道,「做鞋人家的女兒嫁到料理鋪,那邊的親戚背地裡頗有微詞,說是雖然常言媳婦要從下面討,但也不必討到那種低得踩在地上的人家去。」
原來別人這麼講妳啊,可憐的孩子。若是平常清醒的政吉,必會如此安慰阿秋,但當下他只緊閉著嘴。
反倒是心底那粗暴的聲音止不住咆哮。
(是嘛,這就是妳的真心話?壓根不顧含辛茹苦把妳養大的親恩,只因爹幹的是低三下四的營生,害妳在未來婆家面前抬不起頭,現下便抱怨連連?)
我到底是怎麼啦?政吉連額頭也冷汗涔涔,拚命思索。我怎會硬要挑阿秋毛病?
阿秋手裡那把鋒利的鑿子發出冷光。
「爹,遭別人嫌棄是木屐鋪女兒,我好傷心。」
阿秋抬眼望著政吉繼續道。
「可是,我一點也不覺得丟臉。這有什麼丟臉的,爹一直是我的驕傲。從小就常聽客人稱讚,只要穿過爹做的木屐,便不會再穿別家的,上西天都要穿著去。」
阿秋輕輕一笑,凝視著政吉。
(那張賤嘴就會扯謊!)
腦海裡的聲音嗡嗡作響。
(不要用妳那髒手碰我的工具!不要用妳那雙不知感恩的腳踏進我的工坊!)
啊啊,我怎會這樣想?
「爹,您怎麼啦?」
阿秋的語氣帶著一絲顧慮。
「怎麼都不說話呢?」
她拿著鑿子起身,走向政吉。政吉僵了似地直挺挺站著,喉嚨深處大喊:「阿秋,別過來。別過來!」
別拿著那把鑿子靠近我!
然而,望著阿秋的眼尾、嘴角,望著她的神情,完全占據政吉身心的粗暴聲音,益發高聲嘶吼。
(擺出那副得意的姿態,是要我稱讚妳嗎?明明瞧不起父母,嘴上偏要賣乖討好是嘛!)
「這是爹的重要工具。」
阿秋細聲說著,將鑿子遞給政吉。
別接!政吉喝止自己,卻沒能成聲。右手逕行接過,然後緊握鑿柄。
「我不會忘記握住那把鑿子的感覺,不會忘記爹的辛勞。為了銘刻在心,哪怕只有一次,我也想進工坊一趟。」
阿秋的雙眸隱隱泛淚。
「對不起,沒聽您的吩咐。我來打開遮雨窗吧!日頭出來了。」
阿秋翩然轉身,背對政吉,走向工坊的門戶。要遲個半步,阿秋恐怕早已沒命。
政吉緊跟在阿秋身後,揚起手臂。此時,朝陽從阿秋開啟的窗縫灑落。
四周一片鮮紅。
好一抹異樣的朝霞。
豔紅的光從狹小的窗縫傾洩而入,隨即充滿整間工坊,染紅一切。
紅光炫目,政吉踉蹌撞上拉門,右手揮舞著勉強維持重心,不由得垂下鑿子。
「多麼奇特的朝霞!」
阿秋驚呼。她踏出工坊,愕然張開嘴。
「從沒見過這樣的景象。」
趁阿秋還沒回頭,政吉趕緊縮起身子,呻吟著背向她。想遠離阿秋時,痛得渾身骨頭都快散架。
非放下這把鑿子不可。
政吉試著張開右手,汗水從額前滴落。手指一根根像被膠黏住,牢牢固定在鑿子上。左手使勁去扳,也不動如山。
「您怎麼啦?」
身後的阿秋問。
「爹?」
阿秋,別靠近我!政吉內心不住吶喊。神明、佛祖啊,救救阿秋!再這樣下去,我會殺死阿秋!
政吉閉上眼,弓身縮背地靠著拉門,打算滾進走廊。
困苦掙扎之際,突然聽到轟地一聲。
憑空而來的聲響,來自政吉身後的大門彼端,由右至左,由東至西,震耳欲聾。
那是風聲。風就要襲來!
對,是風。比二百一十日 的風更強,比秋末冬初的風更冷。這陣風以幾乎要將政吉吹走的勢頭,轉眼掃進工坊。
政吉腳邊木箱裡的碎木屑漫天飛舞,幾樣工具也被捲到半空中。一箱箱木屐帶應聲倒地。
政吉連忙雙手護住頭,鑿子從右手鬆脫。只見鑿子滾落地面,在風勢中彈跳兩、三下,最後插進大門門板,發出刺耳的聲響。
霎時,狂風止息。
政吉回頭一看,滿地碎木屑,工具凌亂。朝陽一如往常地照耀著工坊。
詭異的朝霞消散無痕。
「阿秋?」政吉顫聲呼喚。
然而,沒人回應。阿秋也消失無蹤。
御番所 情景
享和三年(一八○三)春櫻正盛的某個午後,正當位於日本橋通町的小飯館姊妹屋終於能喘口氣、歇一會兒時,古澤右京之介翩然來訪。
「哎呀,古澤大人。」
剛要卸下門前線簾的阿好眼尖,看到他靠近,便出聲招呼。聽嫂嫂這麼一喊,阿初趕緊解下圍裙,飛奔至門口。
「真是好久不見。」
阿初朗聲迎接右京之介,一面斜瞅著他。
這年春天,阿初滿十七。每多一歲,兄嫂便期盼她會多一分女孩家的秀氣,但總事與願違。阿初依然好勝要強,伶牙俐齒。
「若是一般姑娘,到這年紀也該有人來提親了。」
阿初老將哥哥六藏的話當耳邊風,忙著照顧姊妹屋的生意。她那略略下垂的眼尾和圓潤的雙頰十分惹人憐愛,是姊妹屋的活招牌。
「阿初姑娘還是這麼有精神。」
右京之介笑容可掬地回答。
依舊高高瘦瘦的身材,白皙的臉上掛著一副圓圓的眼鏡,倒挺符合他勉力鑽研算學的年輕學者身分。但其實這位右京之介,可是南町奉行所人見人怕的能幹吟味方與力 古澤武左衛門的長男。他本應循舊例繼承父業,那麼便有第二名鬼見愁在江戶城發威了。
然而,不曉得哪裡出錯,抑或壓根沒錯,是走向正道也未可知。總之,去年夏天,右京之介得到父親的諒解,卸下奉行所的公役職務,步上夢寐以求的算學之道。
那年夏天,右京之介與阿初歷經一件大事。在這件令人同感恐懼與悲傷的大事中,右京之介重新思考自身的未來,終於選擇現今的道路。阿初則得到右京之介這個難能可貴的朋友。
只是,兩人鎮日為大小事繁忙,正月裡碰過面後,右京之介還未曾造訪姊妹屋。
他似乎早料到劈頭便會遭阿初埋怨。只見他從懷裡取出手巾,擦著額上冒出的春日薄汗,往姊妹屋的醬油桶一坐,開口道:
「別這麼生氣,今天我是來邀阿初姑娘的。」
「邀我?」阿初雙眼睜得好圓。「要帶我去哪?」
「賞夜櫻。」右京之介回答。接著,對端來一大杯他喜愛的熱焙茶的阿好解釋:
「阿好嫂,雖說是賞夜櫻,但不必太擔心,御前大人也會同行。」
與力家出身的右京之介口中的「御前」,指的是南町奉行所的奉行,根岸肥前守鎮衛。
阿初與這位時年六十七的老奉行之間的緣分,講起來相當有趣。
打她遇見御前大人,並為大人效力,今年是第三個年頭。原本御前大人便對平民百姓的生活情狀──尤其是觸動人心的奇聞異事與傳說極感興趣,於是,聽說阿初的「靈異體驗」後,力促與阿初見面,一老一小總算結緣。
阿初擁有神奇的力量,能見人所不能見、聞人所不能聞。有時甚至可看穿人心、預見生死與事物的發展去向。
幾年前,阿初才發覺體內沉睡著異能。當身體逐漸成熟、出現身為女人的徵兆時,這份力量突然變得明確起來。然而,代替早逝的雙親,將阿初撫養長大的兄長六藏與嫂嫂阿好,很久以前便曉得她彷彿藏著第三隻眼或第三隻耳,有些不同常人之處。
六藏是效力公家的岡引 ,今年三十七,在看重經驗的這一行還算嫩得很,但他矯健的身手、迅速的行動、一遇上絕不放手的纏功,及最厭惡不平不義的剛正不阿,絲毫不遜於其他岡引。因此,他能堅守日本橋通町這塊大店家聚集的地盤,令御番所的大爺們刮目相看。
以往,阿初的奇妙靈異能力,不時也對六藏辦案有所幫助。為了阿初著想,六藏與阿好認為應盡量將此事保密。
只是,紙畢竟包不住火。漸漸地,內情由六藏效命的南町同心 石部正四郎口中傳開,最終引起奉行大人的關注。
「御前大人約我們賞夜櫻,這回又是什麼事?」
阿初偏著頭納悶地問。先前御前大人找阿初,若不是發生匪夷所思的情況,便是聽到諸如此類的風聲。
「阿初,妳覺得呢?」
「阿初,妳願不願意去查查究竟?」
──御前大人總是這麼問阿初。
「這就不曉得了。」
右京之介微笑著回望阿初。不是故意賣關子,他是真的不知情。
「關於那方面,我也不清楚。只不過,夜櫻這東西,原本便帶著幾分妖氣。」
「是啊。」阿初附和。
說實話,阿初不怎麼喜歡櫻花,總覺得那是種不知就裡的花。
「很久沒見到阿初姑娘,御前大人頗期待這次會面。」右京之介繼續道,「但若阿初姑娘不願意,御前大人想必也不會勉強。如何?」
「我這陣子沒機會上御番所,正覺得無聊。我很願意赴約。」
右京之介圓眼鏡後的雙眸彷彿安心許多。
「那就好。那麼,傍晚時分,我會前來迎接。其實,賞夜櫻的處所、屆時將在場的人物,我都一無所悉。御前大人似乎想給我們一個驚喜。」
而後,右京之介吃著櫻餅、喝著焙茶,閒談半晌算學道場發生的趣事與近日的生活。這無非是擅長傾聽的阿好,巧妙引導不問便不說的右京之介,於他已是雄辯滔滔。
或許是話匣子已開,臨走之際,鑽出暖簾時,右京之介抬頭望見頂上的招牌,便脫口道:
「這招牌也該重畫了。」
姊妹屋的招牌是小飯館常見的鬼與姑娘,取自滷菜的諧音。只不過,通常是一個鬼一個姑娘,姊妹屋卻有兩個姑娘。嫂嫂與小姑攜手掌店,理所當然是兩個姑娘。而這裡還真有惡鬼般的六藏頭子,因此鬼臉是照著六藏繪的。
現下右京之介倒提議重畫。
「為什麼?」阿初噘起嘴問。
右京之介碰碰眼鏡帶,突然手足無措起來。
「幾日不見,阿初姑娘就變得像個大姑娘。我只是覺得,招牌上的臉蛋稚氣了點。」
語畢,右京之介便舉手作別,快步離去。阿初微微一愣,不禁噗哧一笑。
「右京之介大人才是,又長高了。」
第一章 擄人案朝霞怪象江戶深川淨心寺後方的山本町,有個姑娘突然失去蹤影。這便是事情的開端。失蹤的姑娘單名秋,芳齡十七,是木屐鋪的獨生女,再半個月就要嫁到淺草駒形堂附近的料理鋪。這椿親事男女雙方情投意合,待嫁的姑娘也衷心期盼著穿上嫁衣的那一天。阿秋是在朝霞濃豔的春日早晨消失的。那一日,木屐鋪的老闆,即阿秋的父親政吉,漫漫長夜竟做了一整晚惡夢,起身之際只覺比睡前還累。若不在天亮前到工坊,拜過神明、理過工具,政吉便吞不下早飯。因此,他忍著惡夢帶來的陣陣頭痛,緩緩下樓。折磨政吉的惡夢威力不小,即使在夢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