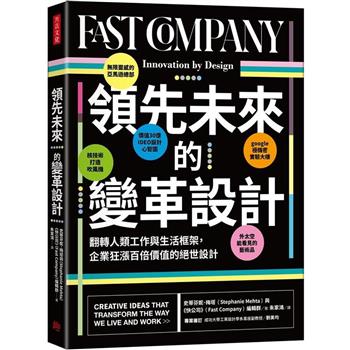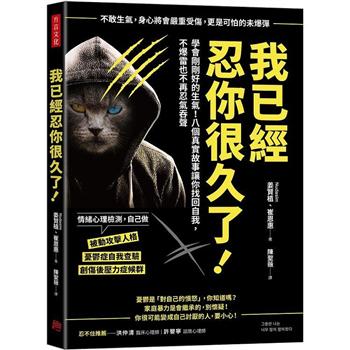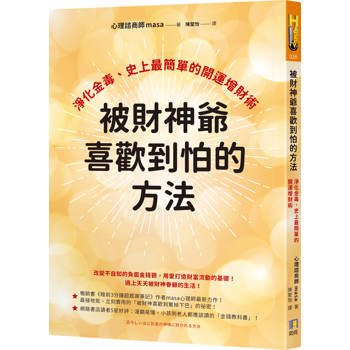「我們一出生就註定要死亡,有什麼比這更殘忍?」
伊(土反)幸太郎是天才,他將會改變日本文學的面貌!- 宮部美幸
以《死神的精確度》風靡文壇影壇
愛與和平好青年──伊坂幸太郎
2004年直木賞候選作品
幽默、寫實、懸疑、奇想天外
殺手業界菁英盡出,演奏一首灰色的末日交響曲!
這個世界瘋狂、絕望、悲慘、惡人氾濫……
人們汲汲營營,掙扎求生;尋求平靜,只是徒勞。
每個人,其實都渴望死亡。
如果上帝的食譜早已決定,端出來的又會是什麼料理?
【故事簡介】
我們的存在,只為了互相殘殺……
鯨;他,專為政治家滅口,專長是教唆自殺。
只要直視鯨的眼睛,便會看見絕望。隨身攜帶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是他心靈唯一的歸依。為了擺脫受害者亡靈,決定清算過去……
蟬;他,殺人易如反掌,擅長滅門血案。
不甘被「經紀人」指使,拒當「被操控的人偶」……
鈴木;他,不是殺手,對妻子的愛是唯一的武器。
為了替亡妻復仇,鈴木潛入詐騙集團,不料被人搶先,目睹仇人遭車輾斃。一路追蹤下,竟和殺手一家相處甚歡。萬萬不知就此點燃殺手們的戰火,黑暗業界譁然。
三個互不相識的人如何遇上彼此?這場相識又是幸與不幸?!
精妙的伏筆設計,不看到最後永遠不知道真相!
作者簡介: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1971年生於日本千葉縣。1995年東北大學法學部畢業。熱愛電影,深受柯恩兄弟(Coen Brothers)、尚‧賈克貝內(Jean-Jacques Beineix)、艾米爾.庫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等電影導演的影響。
1996年 以《礙眼的壞蛋們》獲得日本山多利推理大獎佳作。
2000年 以《奧杜邦的祈禱》榮獲第五屆新潮推理俱樂部獎,躋身文壇。
2002年 《LUSH LIFE》出版上市,各大報章雜誌爭相報導,廣受各界好評。
2003年 《重力小丑》、2004年《孩子們》、《蚱蜢》、2005年 《死神的精確度》、2006年《沙漠》五度入圍直木獎,為近年來得獎呼聲最高的文壇才子。
2008年 作品《GOLDEN SLUMBERS》榮獲2008年日本書店大獎、山本周五郎獎雙料大獎。
作者知識廣博,內容取材範圍涵蓋生物、藝術、歷史,可謂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文筆風格豪邁詼諧而具透明感,內容環環相扣,讀者閱畢不禁大呼過癮,是近年來日本文壇少見的文學新秀,備受矚目。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無法歸類的推理,推理從此進化,全方位娛樂小說誕生!
01|奧杜邦的祈禱 2000
02|LUSH LIFE 2002
03|重力小丑 2003
04|家鴨與野鴨的投幣式置物櫃 2004
05|孩子們 2004
06|蚱蜢 2004
07|死神的精確度 2005
08|沙漠 2005
09|魔王 2005
10|FISH STORY—龐克救地球 2007
11|GOLDEN SLUMBERS—宅配男與披頭四搖籃曲 2007
12|MODERN TIMES—摩登時代 2008
13|A KING—某王者 2009
14|SOS之猿 2009(即將出版)
15|OH! FATHER 2010
16|Bye Bye, Blackbird—再見,黑鳥 2010
17|MARIABEETLE—瓢蟲
譯者簡介:
王華懋
熱愛閱讀,嗜讀故事成癮,尤其喜愛推理小說與懸疑小說。現為兼職譯者,譯有《白色巨塔》(合譯)、《華麗的喪服》、《無止境的殺人》、《夏天.煙火.我的屍體》、《完美的藍》、《蚱蜢》、《沙漠》、《富豪刑事》等作品。
章節試閱
鯨
鯨站在椅子上的男人身後,望著窗外。他把才剛拉上的窗簾掀開五公分左右,從隙縫間俯視市街。真是無趣的景色———他想。飯店的二十五樓,還不足以將所有建築物置於眼下,而夜晚的鬧區也不顯得賞心悅目。只有在十字路口交錯的汽車車燈,大樓的燈飾閃爍著而已。緊鄰的建築物讓天空看起來像一塊狹窄的天花板。
鯨放下窗簾,回過頭來。這間單人房意外地寬敞,鏡台與床鋪的設計有一種肅穆的威嚴,打理得乾淨整潔;在都內的飯店當中,這裡稱得上高級。
「要看看外面嗎?」
他朝男人的背影出聲。五十來歲的男人面對書桌而坐,眼睛盯著牆壁,像是第一次坐在書桌前的小學生一樣,正襟危坐。
「不用了,謝謝。」男人只回過頭,也許是被鯨的聲音喚回神來,他像是嚇了一跳。
這個男人在鯨至今為止見過的政客祕書裡,算是令人比較有好感的。一絲不苟的旁分髮型,讓人感受到他的一板一眼;儘管穿著質料上好的進口西裝,卻不讓人覺得矯揉造作或不愉快,實在難得。即使面對年紀小了一輪的鯨,也不改彬彬有禮的語氣,這應該是出自男子的性格與知性吧。鯨的體格散發出不輸給格鬥家的壓迫感,但男子並沒有因此顯露卑躬屈膝的態度。
「不看就再也沒有機會了。」鯨明知無此必要,還是建議男子。
「咦?」男子的眼中已沒有昔日的霸氣。
你就要死了,這是最後一次看到外頭景色的機會了。鯨本想繼續說明,卻打消了念頭。反正他們永遠不會理解自己置身的狀況,沒必要為此多費唇舌。說起來,那也不是值得在臨終前特地看上一眼的景致。
男人依然面對書桌,目不轉睛地盯著信紙和信封。
「這、這種事,」男人背對他,開口問道。「常有嗎?」他彷彿為了自己說出口的話顫抖。
「常有?」
「像我、像這樣,」男人拚命尋找合適的詞彙,可能是太過混亂,精通的英文脫口而出,「suicide.」說完,他問道:「被迫自殺,是常有的事嗎?」
他的肩膀在顫抖,擱在桌上的拳頭緊握,壓抑著不讓情緒顯露出來。
總是這樣。他們一開始總是裝出毫不在乎的模樣。若要形容的話,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平靜、豁達。他們一副通達事理的樣子,說:「這樣就行了吧?」一會兒之後,又異樣地饒舌,錯以為若是不說話就得死。———儘管說了還是一樣得死。
鯨沒有回答。只是望向房間的天花板,看著綁在通風口上的塑膠繩,繩環已經綁好了。委託人並沒有指定要上吊,不指定的話,一般都採取上吊的方式。
「人死了就能被原諒,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男人說,他把椅子打斜,斜眼看鯨。「就算身為祕書的我自殺,情況也不會改變。社會大眾明明清楚得很,知道真正惡劣的另有其人,然而卻因為我自殺,讓整件事不了了之,這不是很沒道理嗎?」
和對方的對話拖長通常不會有好事,鯨從經驗上學到這一點。
「那不是憑我一個人能做出來的。這是當然的吧?那麼複雜的事,我怎麼可能一個人想得出來?」
男人是梶議員的祕書。這數十天來,梶因為遭媒體揭發他接受通訊公司的不當獻金,身陷醜聞風暴。目前情勢極度不利,正面臨窮途末路的窘狀。由於眾議院的選舉近在眼前,黨部捨棄他的可能性極高。
「只要我自殺,追究責任的聲浪就會減弱嗎?」
「膽小,動不動就大呼小叫,一害怕就出手傷人。獈不就是這樣一個人?」鯨想起獈的臉。老議員個子小,一張娃娃臉;為了營造根本不存在的威嚴,在嘴邊蓄了一圈鬍子,兩道粗眉無時無刻不高高揚起,但仍是毫無力道。鯨每次看到獈在電視上的言行舉止,就覺得這個男人根本不想從事政治,只是想耍無賴而已。
「獈總是委託你做這種工作嗎?」
「這是第一次。」這不是謊話,獈是認識的議員介紹的,三天前第一次和鯨聯絡。「我不喜歡他,不過工作歸工作,我接下了。」
「這次的事件若是能更冷靜地應對,根本不會演變成現在的局面。」男人眼球嚴重充血,滔滔不絕地說:「都是因為獈慌了手腳,胡亂發言,事情才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你怎麼不怨自己要擔任那種人的祕書呢?」
男人嗚咽似地大口喘氣,嚥下口水,叫嚷著:「這太沒道理了!」他一直是一個模範生,人生一帆風順,這或許是他第一次高聲叫罵。出聲的他反倒被自己的舉止嚇得睜圓了眼睛。
「追究的聲浪會轉弱。」鯨簡短地說。
「咦?」
「找個代罪羔羊,是有相應的效果的。」
「就算不會有人信服嗎?」男人露出遭到背叛的表情。
「這一行我已經幹了十五年。」
「逼人自殺的行業?」
「若是沒用,我早就失業了。」鯨在床上坐下。身高一百九十公分、體重九十公斤的巨大身軀把彈簧床壓得吱吱作響。他穿著有三顆釦子的深灰色西裝,從內袋取出文庫本(註一),無視於懇求地望著他的男人,看起書來。
「你、你在看什麼?」男人問。不是出於興趣或好奇,只是害怕自己被拋下。鯨無言地把書背轉向對方,書封已經拿下來了,紙張皺巴巴、髒兮兮的。
「那本書,我十幾歲的時候也讀過。」男人眼睛發亮,為了找到雙方的共同點而欣喜。甚至有種「怎麼,我們根本是同類嘛!」想要握手言歡的氣氛。「是經典名著呢。經典真不錯。」
「這世上所有的小說中,我只讀過這一本。」
男人張著嘴,不知所措。
「這不是誇張、吹噓,也不是自卑。」雖然提不起勁,鯨還是繼續說明:「這是我唯一讀過的小說。」
「你一直只讀這本書嗎?」
「等書破了不能讀,就買新的。這已經是第五本了。」
「那樣的話,背都背得出來了吧?」男人強顏歡笑地說:「書名倒著唸,就成了『涎與蜜』(註二)唷。」他聲音亢奮,像是身負傳達這件事的使命一般。
鯨緩緩抬頭,凝視文庫本的書名,原來如此。「我沒發現。」
忽地他想起十年前的事,當時他誤以為自己能和理解這本小說的人惺惺相惜,由於誤會太深,他犯下了錯誤,一個令他懊悔不已的失誤。看過同一本小說的人,在全世界不知幾凡,然而當中沒有一個人是自己的同志,當時的他還不懂這個道理,只能說是愚蠢至極。
男人的太陽穴抽動著,說:「我真的得自殺嗎?我現在做的只是垂死掙扎嗎?」
「不,大家都是這樣的。」鯨頭抬也不抬地說。事實上,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政客的祕書自殺,又能怎麼樣?」
「有人自殺,就麻煩了。有效果的。」
只要祕書表明「這件事的責任全在我」這種連小學生都不會扯的謊,上吊自殺,社會上對於政客的抨擊就會大幅轉弱。散佈公害而遭受輿論撻伐的大企業社長從大廈跳樓自殺,也有相同效果。儘管會招來「一死了之太卑鄙了!」、「這只是逃避罷了!」等等批評,不過社會大眾也會達成一種「可是人都死了,就算了吧」的共識。
「只要祭出犧牲,就算不合理,再追究下去也太麻煩了。」鯨接著說。
男人聽了發出呻吟,雙手摀住臉,趴伏在桌上。這也是常見的反應。鯨讀著文庫本,等待男人宣洩情緒。有時有些人還會在飯店房間大吵大鬧,和那些人比起來,眼前的男人算是比較好的。而男人止住嗚咽和顫抖後會說什麼,鯨想像得到。
男人果然如預期中說了:「總之,只要我死,我的家人就會平安無事吧?」
走到了這一步,作業的準備階段算是告一段落,就像礦車滑下山坡般,事態將加速進展。玻璃窗對面大樓招牌上的紅色燈飾正閃爍著,彷彿在為鯨的工作鼓譟加油。
「不會有問題的。」鯨在書裡夾上書籤,站起來。走到男人身邊,用指節敲敲桌上的信紙。「遺書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吧。」
男人像是變回了十來歲少年,露出像在觀察監護人臉色似的眼神。
自殺吧,那樣一來,就能保證家人的安全;反過來說,「若不自殺,家人就危險了」。
「有人拒絕過嗎?」男人問。他在問有沒有堅不自殺、反抗到底的勇者。
「有。」
「那些人後來怎麼了?」
「有人因為原因不明的火災,一家人全被燒死。」
再明顯不過的,一抹希望之光從男人臉上蒸發。
「也有人被酒後駕駛的卡車撞死,還有人的獨生女被飆車族凌辱。」鯨唸經似地一一列舉。這些都是他聽說的,不一定是事實,不過「聽起來像真的一樣」比什麼都重要。
男人支吾起來,嘴唇顫抖:「只要我照你說的做,我的家人就會平安無事吧?」
鯨姑且點頭,但並沒有根據。他從未去確認被害者家屬是否會獲得補償,對此也沒有興趣。不過,他推測應該是那樣。因為就算對象是死人,那些政客和有錢人也不願意欠下任何人情。
男人垮下肩膀,所有希望都落空了。
他抓起筆,翻開信紙。
讓對方寫遺書,也是工作的一環。有些人的遺書只寫給家人,也有人寫給政客或上司。讓對方自由發揮,事後再確認內容,如果有問題,就扔掉。
鯨再度坐回床上,回到文庫本的劇情。只要打開書頁,讀上一兩句,立即就能融入小說中的世界,回到殺害老婦人的俄國青年進退兩難的抑鬱心境;比起現實生活,鯨更熟悉書中的世界。
男人寫了三十分鐘左右,偶爾撕下信紙揉成一團,但沒有大吵大鬧或是氣憤拍桌。寫好之後,男人坐在椅子上,側身看著鯨。
鯨呼吸平順,翻頁無聲無息,或許男人以為鯨已經從室內消失了。「你在啊。」他看起來像是失望,又像鬆了一口氣。「那個,有、有沒有人手抖得沒辦法寫遺書?」
「有三分之一是這樣。」鯨從小說世界回過神來。
「那我算是比較好的吧。」
「是啊。」鯨翻過文庫本的書頁。
都到了這步田地,他們還在意自己的「位置」,實在教人啞口無言。儘管死期近在眼前,他們還是忍不住想確認自己高人一等。
鯨在文庫本中夾上書籤闔上,收進口袋。他站起來,對男人說明步驟:「移動椅子,把頭放進繩圈裡。事情一瞬間就結束了。」
「好的。」回答得鄭重其事的男人表情恍惚,若有所失。
「你有一種奇怪的能力。」以前有一個政治大老這麼說。他不說「特別的能力」,而用「奇怪」來形容。「那是種不具形體的恐怖,只要一面對你,人會不由自主地陷入絕望。這是千真萬確的。就連膽大如我之人,在你面前,也不禁有些沮喪。內心的罪惡感和無力感不斷滋生,讓人憂鬱不振,像是掉入萬丈深淵。那些自己犯下的微不足道的過錯不斷膨脹,不禁覺得活下去是種痛苦。」
竟然好意思說只是微不足道的過錯———對方的厚臉皮讓鯨目瞪口呆。那位政治大老繼續說了:
「你有強迫別人自殺的能力。」
「那你快去死吧。」鯨回答。
實際上,鯨並不清楚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有什麼感覺,不過他注意到了,面對面時,對方的表情就像瞪視著黑暗,逐漸失去生氣。
「爬上椅子。」他在男人耳邊呢喃。呼哈、呼哈,眼前的祕書像是忘了怎麼呼吸似的,吃力地喘著氣,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全身打顫。鯨覺得自己不像在威脅,反而像在開導對方。脫掉鞋子,站到椅子上,脖子伸進繩圈裡。明知若是聽從鯨的指示,遲早會死,對方仍是一一照辦。
看樣子沒必要動用手槍了———鯨想。有時也會碰到不肯正視鯨雙眼的人,他們不會被鯨的力量蠱惑,試圖逃走。遇到這種情況,就只能拿出手槍了。鯨會亮出槍,低聲威脅:「如果不死,我就開槍。」儘管這話解釋起來,成了「如果不想死,就自殺」這種歪理,還是有一定的說服力。他們因為不想立刻被槍殺,會選擇聽從鯨的指示。
因為人不到最後一刻,不相信自己會死。
男人握住繩子。此時,他忽地問道:「目前為止你逼死了多少人?」
鯨眉毛都不動一下。「三十二人。」
「你背起來了嗎?」
「我有記錄,你是第三十三個。問這個問題的,你是第八個。」
「做這種工作,你不覺得悲哀嗎?」男人的臉就像為了應付唐突造訪的死亡,皺紋激增,皮膚乾燥,彷彿一瞬間老去。「你不會受到罪惡感折磨嗎?」
鯨苦笑。「我會看見亡靈。」
「亡靈?」
「被我逼著自殺的那些人,最近開始出現在我面前。」
「一個接一個嗎?」
「三十二個人,輪流。」
「那算是一種罪惡感的表現吧?」
原來有這樣的解讀方法啊?鯨吃了一驚,但沒有回答。
男人的表情扭曲,看起來既像在憐憫瘋子,也像在享受拙劣的怪談。
「那麼,我遲早也會出現在你面前吧。」
「沒有人規定非那樣不可。」
「我在學生時代常聽爵士樂。」男人突然岔開話題,鯨明白這是他人生最後的脫序。「我很喜歡查理.帕克(註)唷。」
鯨不打算搭理他的脫序。
「他有一首有名的曲子,叫〈Now’s the Time〉,〈就是現在〉。這曲名很棒呢!」
的確,這個句子很不錯。鯨忍不住跟著複誦。
「就是現在。」
彷彿把鯨的話當成信號,男人回了句「就是啊」,踢開了椅子。椅子搖晃,男人的身體落下,在空中被繩子勾住,天花板吱吱作響。鯨像往常一樣,觀察過程。
黃色塑膠繩陷入男人脖頸,繩圈從下巴往耳後縮緊;口腔內,舌根頂住了氣管。 鼻子為了吸氣顫動著。咻咻地喘著。
他的雙腳前後踢動,椅子被踢倒。男人雙腳搖擺,像在進行游泳特訓似地,動作愈來愈快,沒多久逐漸趨緩。
唾液從嘴邊流下,白沫伴隨著喘息,從嘴角溢出。
男人的雙手伸向勒緊脖子的塑膠繩,試圖伸進皮膚與繩索間的縫隙,指甲撓抓著下顎的皮膚。
也許是因為血壓上升,臉部和眼球滲出紅潮,脖子一帶腫脹不少。全身開始痙攣,是因為氧氣減少,腦內的二氧化碳增加了吧。這時,男人的身體一瞬間放鬆,臉部失去顏色,轉眼間一片蒼白,有如沉浸在脫力感當中,肩膀頹軟,身體左右搖晃。
鯨眺望懸吊在半空中的祕書之後,進行室內確認,檢查有沒有留下垃圾或忘了擦拭的指紋。例行性的善後工作結束後,他探向桌上的遺書。如他所料,男人只留下了給家人的信。他寫下對妻子的鼓勵、對孩子的關愛、人生教訓等話語,最後以「我會永遠守護你們」的字句作結。並不是什麼特別稀奇的內容,字跡顫抖得不很嚴重,只是後半的字列稍稍傾斜,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忽然一陣眩暈襲來,自己站立的場所開始旋轉,感到一陣頭昏眼花。鯨忍住蹲下的衝動,奮力睜開眼睛。同時,背後傳來一個聲音:「還是老樣子,都是人呢。」
鯨回頭。窗邊,一名男子正從窗簾隙縫間窺看外面。鯨咋舌。那是兩年前上吊的參議院議員。當時爆出不法獻金收賄案,為了模糊焦點,他被迫自殺。
政客的問題總是與金錢糾纏不清,不是錢,就是為了自尊。至少也該有一兩件起因於國政方針或義憤填膺的委託案吧,然而至今為止,一件也沒出現。
那個應該已經死去的議員,用手比出手槍形狀,食指敲打著玻璃窗。正下方就是行人專用時相路口,等待號誌的人潮像群聚在一起的螞蟻。
剎那之後,鯨看見了意想不到的光景。
站在路口的人群當中,有個人影彈也似地跳出馬路。
那個人一出到馬路上,立刻被車子撞了,一切發展迅速得令人吃驚。就像投手投出去的球瞬間被打者打回場中央,迅雷不及掩耳。
「死了吧。」一旁的議員亡靈極具存在感,感嘆:「被撞了。有人撞車自殺呢。」
「不,不對。對方不像是主動跳出去的。」鯨在內心這麼回答。儘管沒有清楚目擊,但他如此確信。
由於突如其來的車禍,路口附近的人就像潰散的軍隊一般四分五裂,紛紛嚷嚷。有人聚集到受害者身邊,有人背過臉離開,有人把手機按在耳邊,有人聽到喧嚷察覺騷動跑了過來;這些情景彷彿就發生在他眼前。
在這當中,鯨看見一個人影浮出來似地散發出與周圍格格不入的空氣,往其他方向前進;一群螞蟻當中混雜了另一隻不同種類的螞蟻。
「推手」這個名詞浮現在鯨的腦中。
緊接著,理當被埋沒的記憶從腦中泉湧而出,記憶打開塵封的蓋子,有如泥水般流出;當時的自己,以及過錯、悔恨等等情緒,十年前的記憶瞬間浮現,全身彷彿被火焰燒灼。陳舊焦黑的情感,又再度被加熱,是焦躁與後悔,不愉快的悔恨。
鯨再一次把那可憎的心情塞回腦袋深處,將之壓潰似地封印起來。再次回神時,議員的亡靈已經消失了。
鯨瞥了一眼吊在半空中、已經停止呼吸的男人,離開了房間。上吊屍體發出的傾軋聲,也隨著門關上後,漸漸轉弱。
門上有標示提醒房客「外出時請記得攜帶鑰匙」。鯨沒有拿鑰匙,出了門。門被徹底關上了。
鯨
鯨站在椅子上的男人身後,望著窗外。他把才剛拉上的窗簾掀開五公分左右,從隙縫間俯視市街。真是無趣的景色———他想。飯店的二十五樓,還不足以將所有建築物置於眼下,而夜晚的鬧區也不顯得賞心悅目。只有在十字路口交錯的汽車車燈,大樓的燈飾閃爍著而已。緊鄰的建築物讓天空看起來像一塊狹窄的天花板。
鯨放下窗簾,回過頭來。這間單人房意外地寬敞,鏡台與床鋪的設計有一種肅穆的威嚴,打理得乾淨整潔;在都內的飯店當中,這裡稱得上高級。
「要看看外面嗎?」
他朝男人的背影出聲。五十來歲的男人面對書桌而坐,眼睛盯著牆壁...


 2015/12/30
2015/12/30 2015/12/21
201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