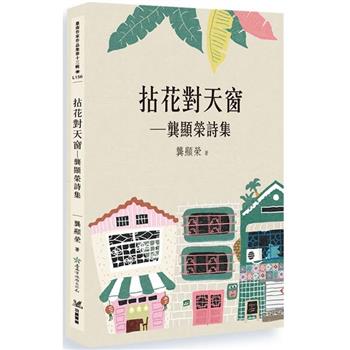承繼橫溝正史與江戶川亂步的創作之魂,
完美融合恐怖與推理真髓的混血作家──三津田信三
最毛骨悚然,也最令人神魂顛倒的「作家三部曲」系列
注意:故事的結束,才是恐怖的開始!
「它」,會去到想要知道「它」的人身邊。
所以,千萬別告訴旁人這個故事……
三十年前,父親替驟逝的祖母送終,
卻憑空消失在名為「百蛇堂」的密室裡。
如今,輪到我為後母舉行相同的儀式,
父親當年的經歷,即將在我身上重演……
五歲時,父親帶「我」回到老家──鄉下望族的百巳家。
私生子的我是家族之恥,彷彿只是空氣,默默過著備受冷遇的生活。
衰老的祖母逝世那天,親族們遵循代代相傳的詭異儀式舉行葬禮,
不料,父親竟在形同密室的「百蛇堂」中消失無蹤!
三十年過去,接獲後母惡耗的我重返睽違許久的百巳家。
這次,換成我與繼母的遺體一起被關進那座「百蛇堂」……
本書特色
1. 三津田信三作家同名系列,與最終曲《百蛇堂》彼此有承接關係,《蛇棺葬》是《百蛇堂》中的主角聽聞的一個故事。
2. 神祕大宅邸與大家族的書寫格局,具有橫溝正史作品的詭譎氛圍。
3. 詭譎的大宅、駭異的空間,恐怖更勝《忌館》。
作者簡介
三津田信三(Mitsuda Shinzo)
在經過多年編輯工作後,2001年以「三津田信三」系列第一作《忌館-恐怖小說家的棲息之處》出道。
因為熱愛恐怖小說和電影與江戶川亂步的作品,他的「三津田信三」系列總是融合大量的相關雜學,及現實虛構混合的後設作風,廣受喜愛這類作品的讀者喜愛。
主要作品尚有「三津田信三」系列的《蛇棺葬》、《百蛇堂-怪談作家說的故事》,「刀城言耶」系列的《如無頭作祟之物》、「死相學偵探」系列等,是目前最受矚目橫跨推理小說和恐怖小說的第一線作家。
2010年以《如水魑沉沒之物》獲得第十屆本格推理大獎。
譯者簡介
王華懋
熱愛閱讀,嗜讀故事成癮,尤其喜愛推理小說與懸疑小說。現為專職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