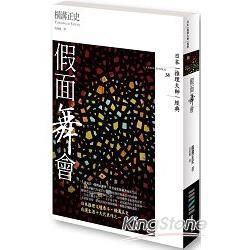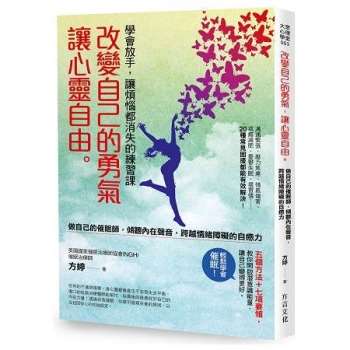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日本暢銷超過5,500萬冊!
推理史上不朽的名偵探「金田一耕助系列」
※本格推理宗師──橫溝正史
生涯十大代表作最後一彈
讀者千呼萬喚的夢幻經典全新重現!
推理史上不朽的名偵探「金田一耕助系列」
※本格推理宗師──橫溝正史
生涯十大代表作最後一彈
讀者千呼萬喚的夢幻經典全新重現!
「人世宛若一場假面舞會,男男女女都戴著面具生活……」
一個風華絕代的電影女星,歷經四段轟轟烈烈的婚姻。
即將覓得幸福的最終歸宿之際,一場怪颱帶來命運的清算。
三名前夫離奇死亡,一人下落不明,徒留詭異的火柴拼圖。
金田一耕助該如何抽絲剝繭,斬斷悲劇的連鎖?
一九六○年的夏天,在避暑勝地輕井澤,實業家飛鳥忠熙終於求婚成功,卻仍愁眉不展。心愛的女人──電影明星鳳千代子,曾有四次婚姻。一年前,她的第一任丈夫成為當地池塘的一具浮屍,第二任丈夫車禍喪命,都沒能找到肇事凶嫌。於是,忠熙委託金田一耕助前來調查,不巧遇上颱風侵襲。一夜過後,千代子的第三任丈夫竟陳屍自家畫室,身旁排列著二十一根火柴,有紅有綠,其中十一根折斷,像是某種奇異暗號……
處處停電斷路,涉案眾人又各懷鬼胎,彷彿個個戴著面具,有意無意促成一場詭譎的假面舞會。金田一耕助能否解開千絲萬縷的糾葛,找出真正的幕後黑手?
◎為廣大讀者創作到最後一刻的巨匠!
一九七六年,《犬神家一族》由名導市川崑改編電影獲得空前成功,被譽為「日本電影的金字塔」、「日本電影史上最極致的懸疑大作」,再度引發「橫溝正史熱潮」。為回應大眾的殷殷期待,七十二歲的大師重拾筆耕,竭盡心力完成十年前連載中斷的《假面舞會》,並陸續寫就長篇《醫院坡上吊之家》及《惡靈島》,直至七十九歲逝世都創作不輟。
◎永遠的名偵探金田一耕助!
身為日本推理小說史上的三大名偵探之一,跨越六十年歲月,至今仍受到眾多讀者的愛戴,影響深遠。著名漫畫《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便是設定主角為金田一耕助的孫子。
耕助的皮膚白皙,個子矮小,招牌打扮是皺巴巴的和服。特別的是,他擁有許多名偵探不該有的怪習慣,像是思考之際喜歡抓搔蓬亂的雞窩頭,搞得頭皮屑滿天飛,一興奮就會口吃,甚至還會抖腳。此外,當他發現關鍵線索時,便會愉快地吹起口哨。雖然外表窮酸,卻有雙睿智的雙眼,登場角色最後總會傾倒在他溫暖誠摯的微笑下。
★大師自選「金田一耕助系列」十大代表作
1. 獄門島
2.本陣殺人事件
3.犬神家一族
4.八墓村
5.惡魔的手毬歌
6.惡魔前來吹笛
7.假面舞會
8.女王蜂
9.三首塔
10.夜行
名人推薦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松本清張之社會派推理小說登場前夕,這段期間,日本推理文學的主流是解謎推理,其領導者就是橫溝正史。──文藝評論家 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