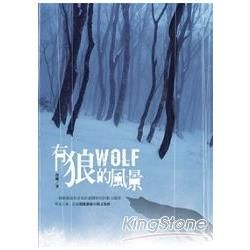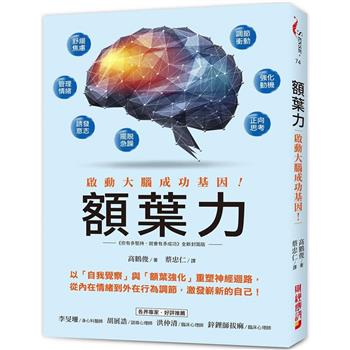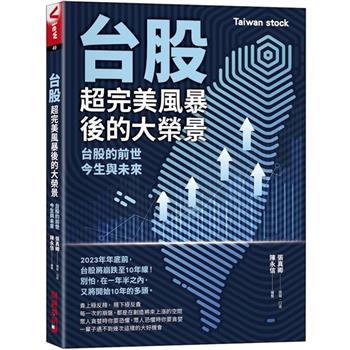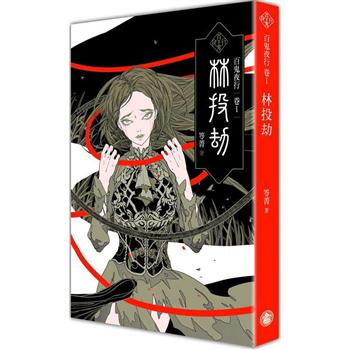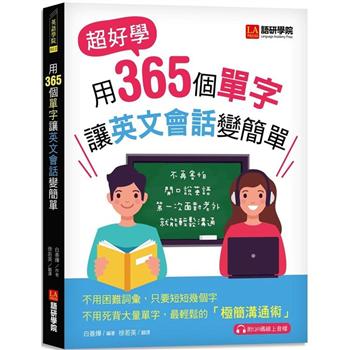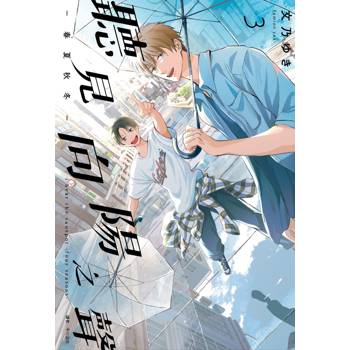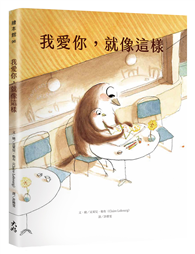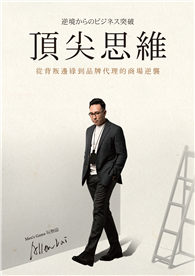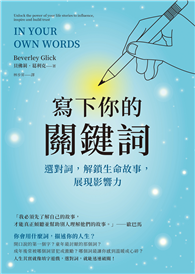本書意在思考當代藝術,以批評為主,兼涉研究,以中國藝術為主,兼涉西方藝術。本書所收文章分為三輯:第一輯《觀察與批評》討論西方藝術理論的翻譯問題,嘗試在西方的影響下進行藝術理論的寫作。第二輯《畫展與畫家》收錄了作者為海內外一些當代藝術家和藝術群體所寫的展覽前言和評論,作者力圖將艱深的理論化為平易的通俗語言,以便使這些藝術家及其作品能為更多人理解。第三輯《訪談與講座》既有作者對20多年來藝術理論研究的概括和總結,也有對新媒體新形式的探討,體現了作者對當代藝術的理解、判斷和態度。
作者簡介
段煉
執教於加拿大高校,研究藝術與文學,出版有《藝術與精神分析》、《世紀末的藝術反思》、《海外看風景》、《跨文化美術批評》、《觀念與形式》、《觸摸藝術》、《詩學的蘊意結構》、《視覺的愉悅與挑戰》等。